
最近,陈逸飞去世,陈丹青辞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职务,两陈事情,媒体闹得沸沸扬扬,一个是资本营运化的艺术家对社会造成的冲击,一个以艺术家的正义感来捅破一个人人都有同感、但是人人都不愿意说的教育制度上的痼疾。只有能够正视这两个问题,中国的艺术才能够真正走向产业化,走向世界,艺术教育制度才能够摆脱目前这种只出庸才、不出天才的混沌状态,给我们培养出一些好像两陈一样的真正的艺术家来。
我认识两陈都好多年了,都是在美国认识的。
陈逸飞和陈丹青好像是1983年前后去的美国,我则是到1986年底才去的。中国艺术家到了美国,有点原形毕露的感觉,好人特别好,能人特别能,坏人特别坏,在国内有个制度压着,除了政治运动这种特殊机会,基本看不到原来的面目,到了美国这种竞争激烈而公开的地方,本质就全部显露无遗了。这两陈都是好人,也都是很好的艺术家,他们都在纽约,那里有个相当庞大的中国艺术家圈子,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有人商业,有人纯粹,有人前卫,很丰富;我在加州,加利福尼亚虽然对美国人来说是很前卫的地方,但是却绝对不是中国艺术家可以追求自我的天堂,那里基本没有什么像样的国产艺术家,都商业得厉害,牛烘烘的,并且张狂得令人难以置信。我在大学中工作,与艺术家还隔着层,对这些同胞,基本能躲就躲。但是和两陈,则多有来往,因为他们都是好人,也都是很能的人。

1990年前后,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的博物馆在洛杉矶的威斯特伍德开幕,我去参加仪式。入门是一张陈逸飞画的哈默肖像,大约有四五米高,技法娴熟。哈默喜欢附庸风雅,找过许多画家给他画肖像,我也看过好些,这张应该是最传神的了。陈逸飞创作的作品好多都是哈默收购的,包括后来送给邓小平的那张周庄的小油画。他在美国打得开局面,因此好些大陆来的画家心生忌妒,八卦四起,说他投奔商业,艺术完蛋。我见到他,问他怎么看这些议论,他就是那样温和地笑笑,说:没事,没事。这个人对自己的艺术素质最了解,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从来没有投机去搞自己弄不来的前卫艺术,因此从不与他人在艺术上争辩,但是总在一步一步完成自己的梦想。
两陈的英文都讲得很流利,这在美国的大陆艺术家圈子中是不多见的。好多艺术家对外国的文化毫无兴趣,也不努力去学习,英文不通,还阿Q式地说“艺术家是不需要学外语的”。他们到博物馆就看合自己口味的那点东西。这两陈在纽约则是实实在在地看、学、想,并且对自己的艺术发展都有明确的方向。陈逸飞回国早,立即把艺术进行大规模的资本运作,成了一个真正把资本和艺术结合起来的艺术家。在这方面,可能在中国也就仅此一人了;陈丹青回国迟一些,在学院中滚了几年,终于明白和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再玩下去是一件奢侈之事,就超脱地退了出来,画自己的画,写自己的文章,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成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这两个人,我都是佩服的。

我和丹青的交情,是从1990、1991年前后在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帮他组织了两次画展开始的。他比我和陈逸飞小,刚来洛杉矶的时候,住作家阿城那里,他们一起听室内乐、谈琐事。阿城是个什么都能的人,写文章、修汽车、装音响设备,无师自通,丹青却是一个连汽车都不开的纯粹艺术家。虽然性格上有不同,但他们还算是一类的,特别是在文字上,你总可以看见互相的影响。我去阿城住的地方看丹青,看见阿城和他就拿不锈钢锅煮挂面吃,就好像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北京宿舍里一样。阿城抽烟斗,丹青抽那种很细的香烟,吃完西红柿鸡蛋挂面,两个人坐在那里听巴赫,全部入定,简直有种宗教的情绪。我是个喜欢肖斯塔科维奇、巴托克之类的俗人,经常是先告退,让他们去欣赏。去纽约,丹青迁到42街的一个画室中,带我去看了看,很小的一个画室,和另外一个外国画家共用。他画一些很小张的静物,毫无浮躁。从他的画室走到灰狗巴士总站,全部是红灯区,满大街性商店,他却能潜心画自己的静物,这真让我惊叹。
在纽约,陈逸飞是忙人。在纽约,不忙不行,哪里有我们国内学院、画院画家这种安逸哦!拿国家工资,卖自己的画,真是社会主义好啊!在美国,不找出路,怎么过日子?陈逸飞一旦看到机会,总不放过,因此早早就回国发展了。丹青却是个清静的人,看书,看画展。钢琴家霍洛维茨去世,他也去吊唁,与陈逸飞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有芥蒂,大约是性格两样导致的吧?但是回国之后,他们依然往来如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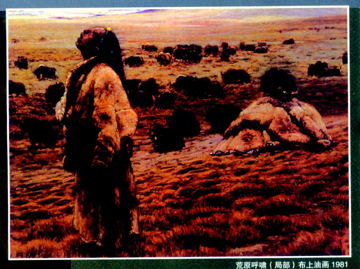
1996年前后,中央美术学院的靳尚宜院长带了戴士和老师和张宝玮老师来洛杉矶,找我探讨建立设计学院的事情,同时提到要去纽约请陈丹青回美院教书,不知怎么没有成。后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常沙娜院长和袁运甫老师带了好几个系主任来洛杉矶,他们也想请丹青,居然就请动了。陈丹青回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院已经并入清华大学,叫美术学院,增加了绘画和雕塑系,他自然是当了导师,本科和研究生都要带。他是个非常非常认真的人,一旦承诺了什么,非投入十二分精力不可。
丹青回国之后,我每次过北京都要打电话给他,他看来很忙,对教学非常认真,但是好像不愉快。我到清华讲课,与美术学院的领导谈起丹青,他们对他都很尊重,但是也都有难言之隐。来来往往时间久了,我就知道了是教育制度的问题。对于现行的艺术教育体制,我一向不以为然,英语和政治分数一点不让,哪里能够招到天才的艺术家啊?我属于那种惹不起躲得起的人,因此在国内若干院校就挂个客座虚名,还是在美国大学供职,但丹青有点身陷囹圄,责任心使他又不能自拔,因此很低潮很懊恼。对于这种状态,我太了解了,但是却帮不上什么忙。
两陈对我都有很大的启迪:逸飞告诉我怎么用市场的规范、资本的营运来做艺术,却又不失艺术水平;丹青告诉我如果与制度痼疾搞不来,是可以全身引退,重做一个自由人的。他们两个都生活在自己的自由王国里,因此,他们也是艺术圈中很自在的人。做艺术,如果能够达到自在的境界,有多好!
(专稿)
王受之,1946年出生于广州,设计理论和设计史专家,为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全职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