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年前——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死于北京中南海瀛台涵元殿。第二天,慈禧太后在北京故宫仪鸾殿病逝。正当壮年的38岁的皇帝与风烛残年74岁的太后竟在20小时之内相继死去,这巧合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光绪皇帝的死,发生得太突然。尽管光绪在去世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的确患了很严重的病,但不至于有生命危险,更不会突然死去。有人曾看到皇帝死前两天还在瀛台水边散步。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光绪死去的当天,慈禧太后于病榻上很快传下懿旨:立溥仪为嗣皇帝,命醇亲王载沣为监国。但有记载显示,溥仪是在光绪临死的前两天,即11月12日进宫的,载沣也是在同一天命为监国的。难道慈禧已经“知道”光绪要死了,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于是匆匆对后事作出安排?
光绪和慈禧巧合地相继离世引起人们的猜测。有人说,慈禧太后知道自己的病已经无法医治,又听说光绪帝听到自己病重的消息时面带喜色,因此下定决心:“我不能死在你前面。”于是密令亲信太监害死了光绪。但也有人说光绪的确是病死的。
这其中扑朔迷离,回顾光绪和慈禧两人生前的恩怨矛盾,也许可以从中窥见真相。
“飞来”的皇冠
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二十八日,一向恬静的醇亲王府突然活跃起来,王爷的嫡福晋(即夫人)生了贵子。 醇亲王十分高兴,给孩子起名叫载湉,希望儿子能像自家府邸旁的太平湖水那样平平静静地度过一生。然而命运却没有按名字所寓意的那样运转。
载湉具有十足的皇族血统,他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是道光帝旻宁的第七子,咸丰皇帝奕詝的亲兄弟。载湉的母亲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
慈禧太后是载湉的姨母,也是伯母,他们本不应该有矛盾。不幸的是,他的表哥、也是叔伯堂兄的同治皇帝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没有后继人,于是载湉成了离姨母最近、最容易控制的棋子。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同治帝载淳病逝。失去自己唯一的亲生儿子,慈禧顾不上悲痛,她不会忘记儿子身后的巨大空缺。同治帝卧病的几个月,慈禧一直在心中筹划“立嗣大计”。等到儿子咽气的时候,她已经确定了人选。她没有从载淳的下辈“溥”字辈中挑选人,因为这样她会由皇太后升格为太皇太后,不宜隔代垂帘,也就无从控制朝政。经过反复权衡,慈禧选择了亲妹妹的儿子——年仅 4 岁的载湉。 因为载湉年幼无知, 便于控制。
面对“飞来”的皇冠,载湉的父亲奕譞伤心不已。他好不容易盼到一个儿子,却要“贡献”出去当皇帝,从此父子不再是父子,只能是君臣,相隔不远却难以相见。所以,当慈禧宣布载湉为嗣皇帝时,奕譞失态地突然扑通一声跪下,连连叩头,并且嚎啕大哭,跌倒在地,昏迷不醒。
当晚,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领旨前往宣武门内的醇王府,执行慈禧的命令——接载湉进宫,继承皇位。醇王府第外挂满灯笼彩旗,一派喜庆气氛,而内室里,奕譞夫妇却为失去他们的爱子失声痛哭。太监们给熟睡的载湉穿上蟒袍补褂,抱上了暖舆,就这样,4岁的载湉在熟睡之中被抱进了皇宫,他一夜之间离开了爹娘,当上了大清国的第十一位皇帝——光绪皇帝。
母子君臣
光绪幼年时有一段时间和慈禧感情很好。光绪初入宫时,由于太小,处处需要人照顾。而他的长相或气质的某些方面带有叶赫那拉家族的特征,这激起了刚失去儿子的慈禧重新做母亲的念头,开始处处细心照顾光绪。
慈禧把光绪领入自己的卧室,亲自包揽了小皇帝吃饭、穿衣、洗澡、睡觉等琐事。光绪小的时候,得过一种怪病,时常无缘无故从肚脐眼里流出一种发黏的液体。为此,慈禧天天擦洗他的身子,衣服一日三换。光绪年幼时最怕雷声,每次听到电闪雷鸣,天公发怒,都吓得浑身发抖,啼哭不止。每遇雷雨天,慈禧就把光绪搂在怀里,一边轻轻拍打他的后背,一边哼唱着小曲。
光绪长至 5岁时,慈禧又开始抓他的启蒙教育。最初,将“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词句写在一张张小方纸片上,一遍遍教小皇帝识字,并“口授四书五经”,随后,慈禧经过反复挑选,最后确定以书法和学问闻名的常州人翁同龢作为光绪的老师。当翁同龢为5岁的小皇帝授课时,慈禧曾多次亲临视察。光绪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即是前往慈禧居住的储秀宫向慈禧背诵当日学过的功课。

每一个女人身上都有母性的本能。当慈禧抱着年幼弱小的光绪时,很难断言她内心没有涌动过温柔的波浪。但慈禧不是普通的女人,她不只是出于天性爱护光绪,更希望通过爱怜和辛勤指示,逐渐确立起一种特殊的人身依附关系,以便于今后对光绪长期控制。
为此,慈禧想了许多办法切断光绪同他的生身父母之间的感情纽带,通过潜移默化的办法,使光绪帝在他那小小的心灵中,逐渐地树立起他和慈禧太后的所谓“母子”关系。光绪称慈禧为“皇阿玛”,这是满语,汉语的意思是“亲爸爸”,并一直保留着这个称呼。
慈禧还把光绪关在森严的皇宫高墙内,多年不让他回家。思念儿子的醇亲王福晋——慈禧的亲妹妹曾多次带着光绪喜欢吃的零食,要求进宫探望,都被慈禧无情地挡了回去,气得她嚎啕大哭。直到多年以后,醇亲王福晋病危,光绪才获准重新迈进他出生的那个坐落在太平湖边的王府大门。
个性倔强、独断专行、经常与母亲唱反调的同治皇帝给了慈禧很多教训,为了使光绪帝从小就树立起对她的绝对服从的观念,她还特别注意对光绪进行“孝道”教育。不仅如此,慈禧还为光绪制定了一些不可违背的条规。每天早晨,光绪帝必须到慈禧的住处去问好请安。随着光绪年龄的增大,慈禧对光绪的要也更加苛刻。在光绪磕头请安的时候,没有慈禧的命令,他是不敢起来的。如果遇到慈禧不高兴,那么光绪只得长跪,还不敢表示什么不满。每逢慈禧乘舆外出,光绪必须亲自随从。年少的光绪皇帝没有一点人身自由,整日生活在慈禧的淫威之下,这给光绪幼小的心灵留下极大的阴影和创伤,致使他陷入无法言语的痛苦之中。正因这样,光绪十分害怕见到慈禧,每见到慈禧总像见到狮子、老虎一般,战战兢兢,生怕惹怒慈禧。
值得庆幸的是,他有爱护他的师傅们,翁同龢是其中之一。在翁同龢的耐心教育下,他勤奋好学,不仅衷心接受着礼制繁复的宫廷教育,而且极有耐心,对枯燥乏味的礼仪制度严格遵守。这让老师翁同龢甚至慈禧都惊叹不已,也让慈禧放下心来:生性懦弱的光绪的确与倔强的同治不同,他容易被权威、规制所塑造。
据记载,光绪入学后不久,一天,他指着书本上的“财”字对翁同龢说:“我不喜欢这个,喜欢‘俭’字。”6岁幼童说出这般老成话,说明他对翁同龢关于君主美德的理解是十分准确的。翁同龢听后非常激动:“皇上明白这个道理,真是天下百姓的福气啊!”光绪11岁那年,在翁同龢的指点下,开始阅读历史典籍。当读到唐朝衰亡时,他在书上批道:“唐朝之所以灭亡,在于宦官专权,懿宗之后更加没有法度,所以亡国了。”他还以“汉章帝”为题,写成一首“以史为鉴”的五言诗,被翁同龢誉之为“帝王御书中的第一篇上乘之作。”

光绪有心成为“中兴之主”,在他卧室的墙上,始终悬挂着康熙、乾隆先帝的画像,他们的业绩就是他的梦想。他因此十分勤奋。许多老臣也一致认为,光绪是自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以来最勤勉的皇帝。
但慈禧常常打破光绪的梦想。在上书房光绪雄心勃勃,充满自信,似乎看到了自己若干年后一展鸿图、意气风发的样子。可一到储秀宫请安,他只能是唯唯诺诺。慈禧不再像以前那样关心爱护光绪,为树立自己的威信,她经常训斥光绪,一次竟然对光绪动了刑具——鞭笞。据记载,到后来光绪不仅到慈禧住所跪安时浑身发抖,即使听到锣鼓声、吆喝声、物体碰撞发出的巨响也心惊肉跳,太监们暗地里叫他“小胆儿天子”。

光绪对慈禧的淫威不能有丝毫的直接对抗,于是小时候不自觉、长大了就自觉地采取消极的反抗来发泄满腔怨恨。小时天真而动,常往东太后住处而与慈禧较疏。慈安死后,他又与翁同龢情同父子。平日里,则像老鼠见猫一样躲避着慈禧。
在慈禧心情舒畅、兴高采烈的时候,光绪仍然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这让慈禧十分扫兴以至于恼怒。慈禧一生气,又是训斥和罚跪。惩罚一起,只会加剧光绪的对抗。经过这番折腾,慈禧的快乐心情荡然无存。就这样恶性循环,慈禧和光绪不再是温情的母子关系,而是谁也别想安宁,谁也别想愉快,彼此是对方噩梦的关系。
在训斥和冷眼中,光绪逐渐长大,成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l887年,光绪l7岁,按照朝廷的惯例,他已到了结婚的年龄。幼帝一旦成婚,就要亲理朝政。这对光绪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他似乎可以从慈禧的控制中摆脱出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但选择皇后的事证明了光绪依然是慈禧的一个摆设。
慈禧想牢牢控制住光绪,对后、妃人选密切关注,经过精心筹划和苦心安排,准备让自己的侄女——大都统桂祥的女儿做光绪的皇后。1888年11月8日(农历十月初五),慈禧以皇太后的名义颁布懿旨,宣告光绪的后、妃一并选定,并定于次年大婚。这些后、妃是如何选定的呢?高阳的《母子君臣》有很生动的描写:
五个候选人一字儿排定行礼;领头的叶赫那拉氏,二、三位是江西巡抚德馨的一双姊妹花,四、五位是礼部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
慈禧对光绪发话:“谁可以当皇后,你自己放出眼光来挑。合意了,就拿如意给她。”
光绪回答:“这是大事。当然请亲爸爸作主;儿子不敢擅专。”
慈禧说:“我知道你的孝心。你自己选,你选的一定合我的意。”
光绪拿起一柄如意,交给谁,实在是很明白的事。大殿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在皇帝身上。突然,只见光绪的手一伸,虽无声息,却如晴天霹雳,震得每一个人的心都悬了起来——那柄如意是递向第二个人,德馨的长女。
慈禧太后大喝一声:“皇帝!”
这是真正的一声雷。光绪一惊,差点儿将玉如意摔在地上。他下意识地回头一看,慈禧脸色发青,双唇紧闭,神态异常可怕;而且还向光绪努嘴示意。
于是光绪如斗败了的公鸡,垂下头来,看都不看,将如意递给了叶赫那拉氏。
叶赫那拉氏却能沉得住气,勉强一笑,跪下举手接受如意,同时说道:“奴才叶赫那拉氏谢恩。”
光绪没有答话,也没有说“伊里”——满洲话的“站起来”,只管自己走回原位,脸上一点儿笑容都没有。
慈禧在愤恨中仍能保持冷静,控制局面也依然有她的手腕。光绪喜欢谁意向已明,不能留下隐患。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喊:“大格格!拿这一对荷包,给长叙家的姊妹。”
光绪喜欢的江西巡抚的两位小姐被摈弃了。
贵为一国之君,却连选择自己嫔妃的权力都没有,对光绪来说,这是一次悲惨、羞辱的失败经历。有人说:“皇帝名为亲政,实则‘虽君亦臣’,‘母子实同君臣’。”此言极是。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1889年2月25日),光绪大婚典礼在太和殿正式举行。光绪帝的婚礼场面隆重宏大,花费也相当惊人,据清宫有关材料显示:光绪大婚共用黄金4100余两,白银482.4万余两。
然而这一切都引不起光绪帝的兴致。19岁的光绪看到比自己大两岁的皇后就心情恶劣,相貌平平是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太后逼迫他接受这门婚事。懦弱的光绪虽然不可能发泄,但他可以消极地抗拒,可以让温暖的洞房变成沉寂的冷宫。选立皇后你太后可以包办,册立嫔妃你太后同样可以包办,但你不能包办感情,你总不能强迫人去温存、去抚慰、去上床睡觉吧!于是,花烛之夜,光绪冷若冰霜,此后既不召幸皇后,也不令皇后侍寝。皇后只有饮泣长叹,在泪水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寂寞的长夜。
昙花一现的反叛
光绪亲政后,与慈禧之间的矛盾逐渐明显。慈禧表面上宣布“归政于”光绪,从此不过问政事,搬到颐和园“养老”去了,但精神仍然贯注紫禁城,实际上仍然把持着军权和官员的任免权;而没有这两项关键的权力,光绪就是一个傀儡。
尽管慈禧的心腹密切地监督着光绪的一举一动,但光绪有名分上的至尊,比以前自由多了。他试图通过维新变法改变自己无权的地位,实现自己“中兴之主”的梦想。一些不满太后擅权的“守正”之士、倾向变法图强的朝臣以及慈禧零星的反对者,迅速向光绪靠拢,形成与慈禧的后党相抗衡的帝党,这就犯了慈禧的大忌。
年轻、直率、稚嫩的光绪一直都是一个优秀的读书人,但没有政治经验。他的自身素质与自我期望之间的巨大落差,就预示着他不可能有好的结局。

光绪急于破旧立新的举动让后党的大臣们十分不安。1898年春,荣禄等大臣联名上奏,请慈禧再度垂帘。这已经在暗示光绪自己的地位不稳。光绪本来对样样事都要请示、汇报慈禧十分恼火,后党分子又兴风作浪,迫其退位,生性怯懦的他破天荒以攻为守,向慈禧伸手要权。一天,光绪召见后党骨干、主持清廷日常政务的庆亲王奕劻,让他转告太后:“我不做亡国之君,如果不给我权,我宁肯退位。”
奕劻把光绪的原话转告给慈禧,慈禧听了奕劻的传话暴跳如雷:“他不想坐这个位置,我早就不想让他坐了!”但她依然叫奕劻传话给光绪:“皇上想办事,我不阻拦。”在私下里,她对奕劻说:“让他去办吧,办不出来再说。”一副秋后算账的样子。
1898年6月1 1日,光绪在“帝党”的支持下,毅然决定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这就是著名的戊戌变法。
面对光绪的攻势,6月15日,慈禧瞅准目标,实施反击。她一天之内连发三道懿旨:
一是令光绪下谕旨,解除了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龢的一切职务。这无疑砍去了光绪的左膀右臂。这使光绪身边所剩的尽是地位不高、空有热情而不谙斗争方法的小人物了。
二是逼光绪下令,以后所有授任新的二品以上官员,均要到慈禧处跪叩谢恩。这等于慈禧明确而牢固地掌握了清廷的一切人事大权。
三是迫光绪下令任荣禄为直隶总督,由荣禄统辖北洋三军。这样,慈禧实际上已牢牢地将京津地区直接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也就牢牢地控制了光绪及“帝党”,使他们不致对自己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慈禧在完成上述部署后,再没有做什么,住在颐和园里依旧读书、写字、看戏,静观事态的发展。
光绪已无退路可走,只好硬着头皮顶下去,试图通过大力推进变法维新,造成某种既定事实,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光绪革去反对变法的一些慈禧派人物的官职,授予维新代表人物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杨深秀4人四品卿衔,为军机处章京,后人又称4人为“军机四卿”。
1898年8月,形式已经非常严峻。慈禧下令直隶总督荣禄频频调动军队。荣禄派一部分兵力在北京长辛店一带驻防,又派一部分兵力到天津,威胁北京。
但光绪不能坐以待毙,他于9月14日以一种传统的传谕方式——衣带诏,让杨锐等4位军机章京速谋大略,想以武力解决慈禧的“后党”。维新志士们手中无实权,他们把希望完全押在处于光绪与慈禧之间摇摆不定的袁世凯身上,结果袁世凯出卖了他们。
就在袁世凯告密后的第二天,即1898年9月21日,终日神不守舍的光绪一大早就赶往颐和园向太后请安。而这时的慈禧则亲率一队侍从由便道入西直门回到宫中,随即在便殿召集起一大群顽固守旧大臣,把匆匆赶回宫中的光绪召到面前,令光绪跪在案前,并置竹杖于座前,如同审讯一般。
慈禧质问:“我抚养你20多年,你竟听信小人之言,想谋害我?”
光绪战栗不发一言,过了好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我无此意。”

慈禧唾骂道:“混账东西,今天没有我,难道明天还有你吗?”
光绪不再争辩。
结果,大臣散后,光绪被押去中南海瀛台软禁起来。
瀛台是西苑的一个小岛,四面环水,岛上有几间房屋,原是清朝历代帝后夏季避暑的所在。光绪帝被囚瀛台后,慈禧就令人拆去了小岛与外界惟一联系的小桥。清晨,由小船将光绪帝送到对岸上早朝。实际上,光绪帝是个傀儡,在上朝时总是一言不发,凡事由慈禧决断。散朝后,小船又把光绪送回瀛台。
光绪几个月昙花一现的反叛之后,是十年多的囚禁生活,他成了皇宫里最尊贵的囚徒。
珍妃惨死
光绪被囚禁后不久,他的最大不幸是失去珍妃。
光绪的婚姻是一个悲剧,但他的不满不能向慈禧表现出来,只能把一肚子怨气发泄在妻子隆裕皇后身上。他不能用打骂来发泄,唯一的办法就是不理睬皇后,连看都不看一眼。换了聪明的女子,一定会体谅皇帝的心情,用柔情来感化皇帝,那样或许会好些。不幸的是隆裕一心想学太后的专横跋扈,不肯向光绪低头,弄得两人关系很紧张。
光绪有时想到隆裕当选为皇后也是一种不幸,不免对她产生一丝同情。婚后三四个月后的某一天,时逢一个节日,按例皇帝须和皇后在一起饮酒。他们两人木呆呆地坐在一起,客气地互相寒暄,光绪看到隆裕那毫无光彩的眼神,忽然心软了,于是对着她一笑,准备打破僵局讲几句什么,如果隆裕也报以真诚的微笑,事情也许会有转机。不料隆裕以为皇帝嬉皮笑脸,是对自己的不尊重,竟然拂袖而去。光绪没有想到皇后会当着众多的宫女太监的面,如此使自己难堪,感到极没面子,发誓不再和她多说一句话,并且尽量避免与她见面。
光绪每次到慈禧宫中请安或禀报,只要不遇到隆裕,就会赏赐那里的太监若干银子,善于察看主子脸色的太监很快明白光绪不愿见到隆裕。于是,当光绪去太后那里碰巧隆裕也在的话,就有太监在门前守候,见到皇帝便会委婉提示:“老佛爷现在正忙着,请万岁爷过一会儿再来吧。”
这是一种多么沉闷的感情生活!珍妃的出现恰如一道阳光,将光绪的生活变得明亮起来。
光绪皇帝选后、妃时,慈禧为了选她的侄女做皇后,将同时参选的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封了“嫔”的称号。长者封瑾嫔,次者为珍嫔,也就是后来的珍妃。
珍妃姐妹出生在官宦世家,祖父做过陕甘总督,父亲是礼部侍郎。姐妹俩虽然生长在一个家庭里,但她们的修养和素质大不一样。有人说:“珍妃是一个绝项聪明的人物,玲珑剔透,正和她姐姐愚蠢固执成了一个绝对的反比。”
珍妃小光绪5岁,美艳贞淑,性情开朗,兴趣广泛,写得一手好字,而且能够左右手同时写字,画也画得很好。这深深地吸引了光绪。
两人经常在一起攀谈品评宫中收藏书画,观赏御花园里的花木,光绪内向的性格逐渐为珍妃的开朗和广泛的志趣所感染。
光绪一直在慈禧的压抑之下而郁郁不乐,是珍妃给了他莫大的欢乐与鼓舞。他一刻离不开珍妃。依照宫里的规矩,只能皇帝诏后、妃入皇上的寝宫,可是光绪情不自禁,常常三四天工夫就要亲自到珍妃宫里走一次,甚至每天光绪到慈禧那请过早安以后,总是吩咐珍妃不要回到自己的宫里去。他放弃凉轿不坐,和珍妃一同步行,有说有笑地走回皇宫便宫。
光绪亲政后,需要批览的奏章越来越多,珍妃侍候慈禧时曾看见过慈禧批览奏章,对处理政务有所了解,因此成了光绪的得力助手。珍妃对朝政大事的见解常常与光绪不谋而和,“人生难得一知己”,对于十几年来孤寂地生活着的光绪来说,真是莫大的安慰和快乐。
1898年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囚于瀛台,珍妃亦受到牵连,被施以刑杖,随后囚禁予偏僻的北三所,并不允许见光绪。光绪帝通过小太监探听到珍妃的下落后,迫切地想见她。在几个太监的帮助下,两个“囚徒”相见了,其情景是何等的悲凉!每次两人都隔着栅栏四目相对,诉说情思,最后又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仓皇出逃,临行前夕,珍妃被慈禧下令溺死在宁寿宫外的井中,年仅25岁。慈禧回宫后,为了掩盖自己杀害珍妃的罪行,对外宣称珍妃是为了免遭洋人污辱投井自杀的,并追封珍妃为恪顺贵妃。
在光绪短暂的一生中,珍妃是惟一给他带来快乐的人。她是那么的青春活泼、开朗热情、善解人意,像一道阳光照进光绪黑暗的世界里;她是光绪的精神寄托。珍妃死后,光绪失去了他的灵魂,变得完全像个木头人。这种精神状态让自幼多病的光绪身体越来越差。

谁是凶手
1908年年初,皇帝得了感冒,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包括光绪本人在内,这一病竟至不起,直到11月l4日死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光绪才38岁,正值壮年,怎么会突然去世呢?更奇怪的是,在不到20小时之内光绪和慈禧——一对冤家先后病逝,这其间没有什么关联吗?
很多人猜测是慈禧害死了光绪,有的人反驳说慈禧没有必要害死光绪,因为慈禧在光绪死前并不知道自己将很快死去,不可能在自己死前动杀害光绪的念头。的确,从慈禧的医案来看,慈禧患的是慢性病,直到光绪死前都没有出现凶险症状。只是到l5日中午时,她突然晕过去,病情发生突变,很快死去。
而且从光绪的医案来看,光绪似乎是正常死亡。
光绪的身体,自幼就很虚弱。小的时候,经常得病。进入青少年时期,体质也极差。长年腰痛,夜间遗精,睡眠不稳,精力很容易疲惫。按照中医的说法,这是体虚肾亏,而且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
据l908年春季的医案记载,光绪因感冒而复发结核病,情况非常严重,已是病入膏肓,性命危在旦夕。
从医案来看,光绪的病情是逐渐加重的,没有中毒或其他伤害的迹象,似乎是正常病死。但光绪的整个治疗过程,全部都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中。请大夫,看病,开处方,全由慈禧最得力的亲信大臣奕劻主持。在这种情况下,要掩人耳目、伪造医案是很容易的。
有史料记载,光绪病重后,江苏巡抚送名医陈莲舫进京给光绪诊病。奇怪的是,陈医生不能直接向光绪询问病情,而是太后代述病状,皇帝只是时不时点头或说一二字,以证明太后说得对。
太后让陈诊脉,老迈的陈医生跪在地上给皇上诊脉。诊完,太后又接着讲病情,舌苔如何,生疮如何,不许医生亲眼看,只能听太后说。太后说完,陈就叩头谢恩退出,根据太后所说,记录医案,提出治病方法,然后交给军机处转送。开了几种药交上,也不知道皇帝用没用。
这种太后口述、医生胡乱记录的医案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因此不难推想,根据需要随意编造医案也不是不可能。
民间盛传慈禧害死了光绪是很有依据的。连光绪帝的嗣君溥仪在其自传《我的前半生》中也说:“西太后自知病将不起,她不甘心死在光绪前面,所以下了毒手,这也是可能的。”结合慈禧在戊戌政变之后的一系列废帝、虐帝活动,更证明了这个说法。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一直想把光绪废掉,这不仅是因为懦弱温顺的光绪背叛了自己,而是她从政变中觉察到光绪的存在会威胁自己的地位。列强们似乎更喜欢光绪当政,这也难怪,一个老人行将就木,还有几年掌权时间,何况比起光绪来她是那么守旧,不如把眼光放长远一点,把砝码压在年轻开明的光绪身上。
慈禧将光绪囚禁在瀛台,各国列强对光绪帝的处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心。英、日驻华公使再三要求觐见光绪帝。英国在华的舆论工具《字林西报》也多次发表文章,抨击慈禧,赞扬光绪。
这让慈禧非常紧张,她不敢明目张胆地废除光绪,于是采取“迂回”战术。慈禧生日时光绪去给她祝寿,她没让光绪进门,传旨说:“皇帝卧病在床,不必亲率百官行礼。”明明皇帝已可以行动,她为什么说他“卧病在床”呢?人们推测说,这是为了造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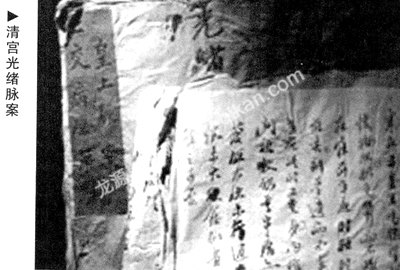
果然不久后,慈禧开始大张旗鼓地宣布光绪有病了,并下诏广布天下,遍求天下名医为光绪治病,把病历每日传送各官署,甚至送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慈禧想通过此举逐渐为废立制造借口。其实,这一时期光绪没什么大病,给光绪看过病的几乎所有医生后来回忆说,光绪得的不过是一些并不太重的慢性病而已。洋人没读懂慈禧这本经,信以为真,他们看到光绪病情严重,纷纷向总理衙门建议,派一名医术高的西医给光绪看病。这一下子弄巧成拙,把慈禧弄得很尴尬,立即派人回话谢绝。
这时候又有一件小事刺激了慈禧敏感的神经。一个潦倒的满洲贵族子弟与一个太监合伙行骗,窜入武昌。他们靠盗窃来的一枚御印和绣着金龙的被子等物冒充光绪。这种不甚高明的骗术居然骗了不少人,一些希图飞黄腾达、急于攀龙附凤的中下级官吏,误以为光绪潜逃到了武昌,纷纷送钱送物,虔诚进贡,希望有一天能平步青云。人们纷纷传言,光绪挣脱了慈禧的枷锁,到了武昌,可能会依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势力东山再起。这种传言传到张之洞那里,看惯官场风云的张之洞也将信将疑,一再密电慈禧,查询光绪下落。当他弄清了真正的光绪依然囚禁在瀛台之后,就毫不犹豫地把两个骗子抓起来砍了头。
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骗局,但是骗子装扮“逃逸”中的皇帝吸引了那么多官吏的事,不能不让慈禧心惊肉跳。这表明光绪虽然失去了权力和自由,但只要他是这个王朝的皇帝,他就有不可估量的号召力。慈禧不禁暗自发憷:如果真有这类事情发生,那她有可能会被人从御座上彻底掀下去。于是,她对光绪的监视、控制更加严格。她下令,光绪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必须向她奏报。有时,光绪心情郁闷,登楼远眺,看一看南海的水波,望一眼紫禁城的亭台楼阁,太监们都会向慈禧汇报。
光绪在瀛台孤苦伶仃,没有自由,饱受慈禧的生活和精神上的虐待。
据有关史料记载,光绪睡觉的榻上,只有一张破席子。严冬季节,岛上寒风凛冽。光绪的衣服除了上朝用的龙袍外,内衣都是旧的,又很单薄,根本不能抵挡风寒。大殿的窗户纸,经过一年的风吹雨淋,早已残破不堪,但没人来修。冷风直灌进屋,光绪只得搓手在殿内走来走去,借此取暖。光绪身边的太监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冒着危险找到工部侍郎立山,求他给皇上糊糊窗户。立山还有点同情心,就带人去把窗户糊上了。
消息马上传到了慈禧太后那里。一天,太后召见立山,冷冷地问:“立山,我看你最近红光满面,走了什么好运了?”
立山被问得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回答,太后又冷笑说:
“我看你越来越能干了!我明儿赏你个差使,专门管打扫瀛台!”
立山恍然大悟,吓得急忙举起双手,左右开弓轮番打自己耳光,边打边告饶:“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连打十几下,慈禧才喝道:“滚出去!”
立山机警,挺识趣地当真就势一躺,打了几滚,滚出殿去,逗得慈禧“扑哧”一下笑了。但慈禧对立山的仇算是坐下了,后来庚子年立山被杀,这大约也是一个原因吧。
光绪刚去瀛台时,太监们按慈禧的吩咐,每天给光绪备两席饭菜。一席是“例席”,也就是光绪分内的一席,另一席是慈禧所“赏赐”的。后来,慈禧下令撤去她所赐的一席。而所谓“例席”,除了食品干冷变质之外,太监们往往任意敷衍,有时干脆就不送去。倒是一些心肠好的小太监,常用自己的月例银买贴饼子、炒栗子、煮花生之类的小吃给光绪吃,但光绪还是有吃不饱的时候,实在是饿得不行,就摘槿花的花英来充饥。有时,慈禧却故意多给光绪食物,使处于饥饿状态的光绪大食一顿,以损坏他胃口。
有一次,光绪率百官去天坛祭天,他走得很慢,有个官员请他走快点儿,他说:“你们穿的是好靴,我穿的是破靴,你们走得快就前头先走吧。”可见他处境的窘困。
皇帝在众目睽睽之下受辱,到后来太监都欺负到他的头上。有一次慈禧召集外边的戏班进宫演戏,光绪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什么时光,还有这份心思去听什么戏!”他身旁的一个太监听到了,厉声责问他:“你说什么?”光绪连忙解释说:“我随便乱说,你千万别乱声张。”
光绪不甘心于这种屈辱境遇,他企图摆脱。l898年冬天,一夜之间,湖面结了一层冰。光绪想出去走走,小太监给皇上披上大褂。光绪一步步往前走着,听到身后喊:“请万岁爷留步!”小太监气喘吁吁追上来一把拽住光绪帝,原来光绪不知不觉已经上了岸。
光绪游兴未尽,还想去园子里看看,小太监们不忍拒绝,决定为光绪破个例。正当光绪游兴正浓时,被大太监崔玉贵看见了。崔玉贵以小太监挟持光绪帝出巡、欲行不测为由,将6个小太监全抓了起来。光绪帝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结果6个小太监当天就被杖毙。
在这之后,只要南海结冰,就有人不厌其烦地砸冰,连块大点儿的浮冰也不放过。光绪听着砸冰声,心如刀绞。
在这个孤岛上,光绪没有任何人可以接近。他所喜爱的珍妃早在政变时就被囚禁,庚子年又被推到井里淹死。瑾妃是不能去瀛台的。即使是皇后,来探望光绪也有定时,而且,事先必须得到慈禧的批准。但光绪对这位皇后是十分厌恶的,他也不愿与她相见。据说,一次皇后去看望光绪,正值光绪盛怒,竟将皇后头上的发簪打落在地摔碎。自此以后,皇后与光绪几乎不见面了。在这里,他孤独凄凉地度着时光,打发着难熬的岁月。
囚笼中的光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有一天,他信步走进一个太监的住室里,见桌上放着一本《
三国演义》,他顺手拿起来看了看,勉强看了几行,又把书扔到桌上,叹息说:“我连汉献帝都不如啊!”
长期的折磨、摧残,也使光绪的性格发生了畸变。原来他对太监从不打骂,很少同别人发脾气。但在他临死前几年,变得暴怒异常,烦恼时,常对太监喝斥、打骂,以发泄怨恨。他还时常用竹竿穿插在椅子下面,叫太监们抬着他在室外奔跑。他自己手持铜器,一边敲击,一边呼喊:“外国人如此闹下去,怎么得了!”一次,竹竿断了,他被重重地摔在地上,跌得鼻青脸肿。太监们吓得跪在地上,不敢起来。光绪却平静地说:“起来吧,与你们无关。”当时,宫中的人都认为他得了神经病。
慈禧明知光绪自幼体质差,却将他囚禁在瀛台,不让他吃饱穿暖,不给他自由,处死他心爱的珍妃,对他的精神百般折磨,这不是把光绪往死里整吗?
光绪恶劣的精神状态加重了病情。他从小患下的多种疾病一天天恶化,结核症波及肺、肾及其他器官,并患有严重的遗精症。各种疾病,使他的行动日益困难。据清宫医案记载:他腰胯左边疼痛严重,稍一转动就牵动整个腰部,疼痛难忍,晚上睡得越多,则血脉愈凝滞,筋骨愈不灵便,而且这些症状一天比一天严重。
这一次光绪如慈禧所愿真的得了重病,慈禧是不是又广招天下良医为光绪治病?她表面文章还是要做,但似乎敷衍了事。光绪对医生看病的态度产生怀疑,他埋怨御医“每次看脉,忽忽顷刻之间,岂能将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
1908年慈禧也生病了。前面就提过一种说法,说慈禧得的是慢性病,她在光绪死前并不知道自己将很快死去,不可能在自己死前动杀害光绪的念头。但想想看,一个70多岁的老人,本来时日不多,稍有风吹草动,怎么不会想到自己会因此而离世?慈禧生前与光绪矛盾重重,对光绪百般折磨,让光绪的一生过得那么压抑和暗淡,她难道不担心自己死在光绪前面会遭到光绪的报复?慈禧的拥护者众多,但“树倒猢狲散”,谁知死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慈禧不让光绪死在自己前面,她如何能安心离去!
何况光绪在病重之前,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盼望太后百年之后,自己重新亲掌朝柄。光绪身边的人曾说:“万岁爷心底上,始终确认那些新政的策划是绝对合理的,绝对可以推行的。但须等到老佛爷撒手西归的时候,万岁爷一定可以很顺利地干一番。”光绪每日早朝之际,对国家大事,甚至世界上主要国家发生的事情,都非常关注,了解形势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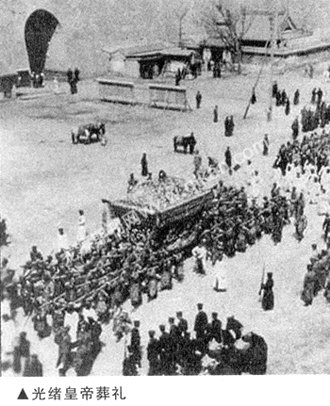
德龄在她的《清宫二年记》一文中这样写道:“每日早见皇帝,当余有暇时,光绪帝必问英文,所知甚多。余见皇帝,极有趣味。在太后面前,面容肃默,或有时如呆子。若离开时,全然又是一人。”
光绪不仅向德龄学习英文,还不断向她询问了解西方各国风土人情、政治制度、国家间相互关系等问题。民间传言光绪帝听到慈禧病重的消息面带喜色,即使是编造的也很符合光绪的立场。
光绪一副渴望东山再起的样子,怎能不让慈禧担心?据说,光绪临死前,有一天忽然想去慈禧面前请安,实际是想当着慈禧的面发泄他的愤懑之情,要亲口告诉她,被她压制折磨了一生的傀儡皇帝快死了,她该放心了。光绪对慈禧如此怨恨,疾病缠身的慈禧难道不会采取特殊措施?
容龄的《清宫琐记》中记述了周景濂所经历的光绪死亡的情景。周说,光绪死的那天早晨,他去见光绪,见光绪躺在床上,以手招他近前,只是张口而说不出话来。他还以为光绪想要吃的,遍屋寻找也没有找到。这时,只见光绪头一歪,口中喷出一股鲜血,他急忙奔至光绪身边,发现皇帝死了。中午时,醇亲王奉太后命来看光绪,见已死,即匆匆去报告慈禧。一会儿,慈禧太后率一群太监进来,屋里乱得很。而宣布光绪死亡的日期已是两天之后了。从记载中,人们认为这是中毒身死的症状。也有的史料说光绪死于11月14日傍晚时分,而第二天即15日慈禧来瀛台亲自验证后,中午时便发病,到下午就不行了。
清末名医屈桂庭在他写的《诊治光绪皇帝秘记》一书中披露:光绪在临死的前三天,曾在床上乱滚,他向我大叫肚子疼得不得了。而且他的面色发暗,舌头又黄又黑。
德龄在《瀛台泣血记》中肯定地说:这是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大太监李莲英干的。李见慈禧太后的寿命已经不长,靠山快倒了,暗自着急,与其待光绪掌了权和自己算账,不如先下手为强。是李莲英设计毒死了光绪。
关于光绪之死还有一种说法,凶手是袁世凯。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说:“我听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是袁世凯派人送去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原因。袁世凯靠出卖光绪发迹,光绪十分痛恨他。在瀛台时经常在纸上画一个乌龟,并在乌龟背上写上袁世凯的名字,粘在墙壁上,用小竹箭射击,过一会儿又取下来撕成碎片,可见恨袁世凯之深。袁世凯的靠山慈禧身体已一日坏似一日,不容袁世凯不另寻出路。不过光绪在涵元殿被慈禧监控得很严实,要想瞒过慈禧去害光绪是很不容易的。
详考清宫医案,用现代医学的语言来说,光绪是受肺结核、肝脏、心脏、风湿等慢性病长期折磨,致使身体的免疫力严重缺失,酿成了多系统的疾病,最终造成心肺功能衰竭,合并急性感染而死亡。但,正如前面所述,光绪看病、抓药,当然也包括清宫医案的所谓“实录”,这一切都在慈禧太后的掌控之中,谁能保证其中不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作伪作假呢?
1980年清西陵工作人员清理光绪的崇陵地宫时,检查了只是一堆骨骼和几缕头发的光绪遗体,并未发现有外伤的痕迹,颈椎与头发经化验,亦无中毒表现。但,前些年又有报道,北京有关部门对光绪遗体头发进行了高科技手段的化验,发现砷的含量高出正常值上百倍。地宫内没有污染的迹象,与光绪皇帝葬于一室的隆裕皇后(入葬时的身份已是太后了),其遗发砷的含量却很正常。而头发中砷含量的超常,正是慢性中毒的呈象。
笔者研究光绪猝亡有年,倾向认为光绪之死,应属正常亡故;早于慈禧一天,确属巧合。虽然光绪被慈禧害死的说法很可信,但推断只是一个,光绪还是属于病故。慈禧太后可定为间接凶手,是她使光绪悲惨地离开了人世。然而,面对“清宫医案”中极可能存在的独裁者、权谋者的上下其手,面对现代化高科技的检测化验结果,还能坦然自信地颇有把握地“倾向”么?
百年疑案,光绪猝亡;希望在下一个百年中,这个“天字号”的疑案能够破解,大白于天下。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