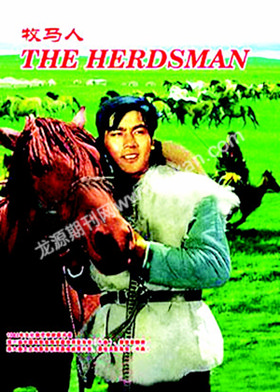
三十年影音变迁之电影篇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看大师碟买大师碟成了都市小资生活方式中的重要一环。2001年还在复旦读研究生的秦玉兰是个淘碟迷,她对记者说:“我得承认,相对于那些动不动就一麻袋一麻袋往家里搬影碟的发烧友们,我只能算个蹩脚的、不上档次的业余电影爱好者。多年以来,我对电影的热情时断时续、若即若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多少值得我看的影碟。在孙孟晋把他认为出色的DVD推荐给电波那头的听众以前,在《看电影》等专业杂志把碟评写得技术与艺术同等出色之前,我把选购影碟的筹码都压在伯格曼、费里尼和安哲罗普洛斯等少数几个导演身上,也就是说我一度考虑成为某个导演的收藏专业户,即使那位导演的作品在当时连影子都摸不着。但是2001年让我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当那些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杰作仿佛在一夜之间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时候,坦率地说,我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把钱花在杨德昌身上好呢,还是为戈达尔筋疲力尽。我也不肯定该不该感谢多如牛毛的盗版贩子,他们是一群真正懂得电影的人,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往往只有小学或中学的文凭,并且法制意识淡薄。”
这些淘碟一族在对西方电影大师顶礼膜拜的同时,也见证了中国电影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电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8年,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十年动乱流血的伤口、充满猩红的过去仍然在困扰着那些经历过艰难岁月的人。第三、第四代导演是一群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从《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戴手铐的旅客》、《天云山传奇》、《小街》、《牧马人》一直到后来的《芙蓉镇》,他们延续了老一代电影人的现实主义风格,那些沉重苦涩、人性被禁锢的岁月又重新在银幕上被呈现出来。特别是“第三代”的佼佼者谢晋,他的电影反思民族历史,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同步前行,开创了中国电影的谢晋时代。“泪飞顿作倾盆雨”—— 一种完全不同于周星驰影片的体验——对于当时观看这些电影的“伤痕一代”来说,这就是电影的全部意义。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高考毕业后的第一代年轻人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第五代导演是中国电影后50年的核心力量,正是他们,实现了中国电影在国际顶尖电影节上的“零的突破”。“我是在我们三林镇上的电影院里看的《红高粱》,也不是我要去看,年纪还小,不懂什么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我爸拉着我们全家去看的。我当时和大多数男孩子一样,迷的是《少林寺》这样的功夫片。”殷志江记忆中第一次看第五代导演的影片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多的印象,“《霸王别姬》去电影院看了两遍,但是依旧没有什么感觉。直到我后来买了张碟,重新看,才发觉陈凯歌确实拍得真不错。”
除了张艺谋和陈凯歌,殷志江印象很深的另一个导演是一直坚持艺术片理想的田壮壮。他早期的两部以西藏为背景的电影作品《盗马贼》和《猎场札撒》都让他热血沸腾。田壮壮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起当时拍《盗马贼》的初衷:“说心里话,我们这帮人是有‘文革’情结的。‘文革’情结中最核心的是对政治极权的反思,但那时候是不可能在电影中有话语权的,就想到在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会有个借题发挥的故事。再有一个坦白讲,是受电影大师的影响,对影像的追求让我选择这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的影像会更震撼你。正好这个时候北京办了一个国际电影交流会。这是毕业后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次影展,马丁·斯科塞斯和今村昌平等都来了。我就带着写《盗马贼》小说的这个甘肃作家去洗脑,让他耳濡目染,看这些美国、欧洲、日本的电影,然后跟大师们一起开座谈会,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特别有收获。就这么着我们拍了《盗马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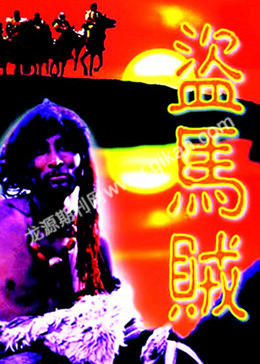
田壮壮还在坚持着自己的理想,更多的第五代却很快蜕变为娱乐市场的大鳄,他们努力要拍摄中国人自己的大片。大片的概念随着《真实的谎言》、《生死时速》、《泰坦尼克号》等好莱坞引进大片的票房神话而深入人心。在此之前,一些外国影片只能以“内参片”的形式在少数电影院(如上海的新光电影院)面对少数观众。儿童作家秦文君曾经向记者描述过当初如饥似渴观看内部电影的景象:“最疯狂的当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有一大批好片子在‘英国电影回顾展’为首的一系列外国电影周中亮相。记得有一次,我的早场电影是在新光看的,散场后小跑着奔向另一个剧场,随后又是另一家;就这么一个接一个赶着场子看片子。姿态比跑片员还心急火燎。其间还旁若无人,一手拎着水瓶,一手拎着小食,像是唯恐在颠沛流离中饥渴交迫,昏倒在去下一个电影院的途中。那天的夜场电影恰巧又是到新光看的。回家后回顾这一整天的行程,发现竟在上海地图上走出一个大大的圆。”
“内参片”不是电影院放映的主流,正规电影院里除了包场观看的主旋律影片,最能吸引观众的就是香港电影。从1977年开始,内地的电影院开始放映香港电影,一代人的恐怖电影记忆是从《画皮》开始的。1983年,电影《鼓手》在观众中引起轰动,这时候的张国荣还是如此阳光、如此灿烂。由李翰祥来故宫拍摄实景的清装宫闱片《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也大受欢迎,梁家辉因此得了影帝之后就失业,而刘晓庆也走上内地女星一姐的地位。1985年之后,内地开启了“录像厅”时代,有的录像厅有越俎代庖取代电影院的趋势。香港警匪片、武侠片和喜剧片是录像厅的常客,《英雄本色》系列、《赌神》系列、《倩女幽魂》系列、《逃学威龙》系列……还有台湾的“琼瑶片”也开始登场,周润发和周星驰,林青霞和秦汉,老片新片,纷至沓来,由不得细嚼慢咽。到了90年代初,国产电影很不景气,《黄飞鸿》、《东方不败》、《新龙门客栈》等港片,正式在内地电影院摧城拔寨,争夺票房。同时博得大众特别是小资们青睐的还有一个名叫王家卫的戴着墨镜的香港导演,他的小情小调最终成就了张曼玉和梁朝伟两大天皇巨星。不过,由于VCD的冲击,很多港片公开上映时的票房并不是很好,比如被引为经典的《大话西游》,1995年在大陆上映时票房低得可怜。

不仅是港片,上世纪90年代初,整个中国电影市场跌至低谷,观影人数骤减,票房暴跌,影院关门。1994年,为改变电影市场的萧条局面,时任中影公司总经理的吴孟辰向电影局提议以国际通行的票房分账形式(制片方35%,发行方17% ,放映方48%),进口最新的一流外国影片,以发行的收入扶持老、少、边、穷地区电影事业。当年年底,广电部电影局批准了这个建议,允许每年可以进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表现当代电影成就”的影片。于是有人将这10部影片称为“10部大片”。1994年11月12日,由哈里森·福特主演、华纳出品的《亡命天涯》作为首部进口分账大片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郑州、广州等六大城市率先公映,并以2500万人民币的票房佳绩在全国创造了大片的第一个消费奇迹。1995年大年初一上映的成龙电影《红番区》是大片放映的又一重要时刻,中影公司与成龙合作,使《红番区》在香港与中国内地同步首映,中国观众看超级大片终于实现了“零时差”。
随着中国加入WTO,2003年国家广电总局宣布进口分账大片从以前的10部增加至20部,进口影片的总数量也达到50部。面对好莱坞大片的凌厉攻势,国产大片也一直在寻求一条市场的出路。从张艺谋的《英雄》到吴宇森的《赤壁》,一场场快意恩仇的江湖厮杀呈现在观众的面前,热闹,眼花缭乱,但也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反正都是大制作、大投资、大明星,演员混个脸熟,群众看个热闹,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中国式大片墙内开花墙内香,票房大卖的同时,口碑却越来越差。

在第五代之后,第六代导演开始擎起艺术电影的大旗,依然小众,并且依旧孤独。自1990年张元独立制作低成本电影《妈妈》以来,中国独立电影制作领域已经历了坎坷的18年。这些严肃和深刻的作品,对观众形成了视觉冲击。但其中的很多影片,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还只能从盗版DVD中一窥它们的庐山真面目。当贾樟柯、王小帅、王全安、王超、张元、章明、娄烨、朱文、王光利等人的作品在国际上频频获奖时,其实普通观众并不是太了解他们和他们的电影。即使是拍摄一部小成本的电影,花费也常常让剧组不堪重负。朱文拍《海鲜》的花费是100万人民币,光转胶花的钱大概就有四五十万元。而王光利的《横竖横》筹资80万,可以说是将成本压低到了几乎不可能的程度,最后为了电影顺利完成,制片、导演、编剧都没有拿工钱。
《十七岁的单车》和《青红》的女主角高圆圆,对记者说了一个多少有些悲壮的故事,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第六代导演风光背后的窘境:“拍《青红》的时候,王小帅面临着经济上的巨大压力,有很长一段时间剧组其实根本就没有钱了。拍完一天之后我们心里都会打鼓,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开工,因为拍到一半就夭折了的片子我们碰到的太多了。王小帅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去讨钱。同时经常会有讨债的人跑上门来。车祸后打着石膏的制片主任就拍着保险箱,信誓旦旦地对他们说,这里面都是钱,还怕不还给你们?(其实里面只有几千元)这样才蒙混过关。有一天,王小帅自己发着烧,仍然跑遍了贵阳所有的取款机,给工作人员发了几百元钱。他在摄像机前的状态挺震撼我的,如果我在这样的压力下,我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安心演好戏,能投入到角色之中去。”对此,王小帅本人反而觉得经济方面的问题并不是太有所谓,他轻描淡写地说:“这是很正常的事。”
1989年,王小帅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早期酝酿的几部片子后来都没有继续下去。1990年,他到福建电影制片厂报到。结果,他先后写了5个剧本都没有通过,他发现再等待组织给他机会,他的电影就永远拍不成了。要像第五代导演那样用国家的资金拍片是一个非常渺茫的事情。早期的坎坷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王小帅们的电影总是那么阴冷。在《十七岁的单车》中,阿桂扛着被砸烂的自行车,迈着多少有些蹒跚的步伐走过北京街头的镜头,让许多西方影评人评价为“震撼人心,完美无瑕”。
在“第六代”电影人不同路数的叙事中,有一个关键词是不能被忽视的,那就是“城市”。面对城市的推土机,欠发达地区的居民开始心理失衡,一方面是麦当劳文化的诱惑所引发的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则是融入都市过程中的种种挫折导致了他们的失落和迷惘。贾樟柯的《小武》、《站台》和《三峡好人》等作品都深刻地反映了农村与小镇居民面对都市化浪潮时的价值失衡。小武被捕后在大街上抽烟时冷漠的表情,旁观者对于小武仿佛鲁迅笔下“看客”般的漠然,如此真实。
(摘自《新民周刊》2008年第37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