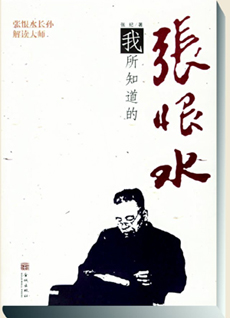
张恨水代表了一种由文化传统携载传统文化搏击于现代生存整体的力量……张恨水的传统文人人格境界及张氏作品中的那么热情与真诚具有着不可忽略的抵御当代文化之冷漠的功用……
——张毅
北京砖塔胡同43号:我见爷爷的最后一面
1967年的正月初七,那年我十岁。我的家在人民大学林园8号楼,4单元42室,这里有我全部的童年。砖塔胡同爷爷家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去,这一天我和仅比我大6岁的小叔张同正在嬉闹,我妈突然惊慌地进了家门说“爷爷走了”。因为是节日期间,我妈穿了一件新的素花罩衣,那年我妈应该是32岁,她很年轻,也很漂亮。
从全家人的表情中我知道“走了”的意思。文革时期,砖塔胡同43号院像一叶孤舟随风飘摇,那样的渺小,那样的不堪一击。造反者从43号院前匆匆而过,没有将它踏翻,没有将它捣碎,任由它在惊恐中飘摇。在砖塔胡同我家与邻里多年关系和睦,特别是居委会的几位大妈,她们知道张恨水是怎样的人,所以她们要保护我家,43号院这朴素得有些简陋的小院没有再遭受命运的最后一击。爷爷是静静地走的,跟随家里几十年的老佣人,正月初七早晨在给他穿鞋的时候,他往后一仰撒手人寰。
我的名字是爷爷起的,我的出生日和我爸我妈的结婚纪念日巧合,爷爷脱口而出就叫张纪,纪念的纪,没有用他满肚子的学文思考一下。以后我曾试图改过几次名字,我父亲叫张小水,我干脆按照大家伙儿的意思改成张济水也挺好,在名字中内涵志向。读了点书以后我放弃了改名,名字就是人的一个符号,和人能不能成气候没有关系。
爷爷走的这一天,家里没有哭天抢地地乱作一团,小院里静得出奇,女人们在默默地垂泪,仿佛生怕惊醒了爷爷。他的确是太疲劳了,他一生的睡眠比常人要少许多,他的形象在家人中永远是坐着的,永远是在写作。而这个时候已经用不着他再写作了,他要睡觉。家里的男人们在床边围着爷爷。除了家人,仅有一位从北京市文联赶过来的叔叔,穿着崭新的蓝制服,陪在爷爷的身边算是代表着组织和官方。他低着头默默地抽烟。我爸和伍叔也在抽烟,奶奶开始有节奏地号啕大哭。我没有哭,这时候我也想抽烟,像一个男人那样沉着。爷爷的屋里烟味很浓,这是我熟悉并且感到亲切的味道,香烟伴随爷爷的一生。爷爷的灵感终于停止了,停止在一片波澜壮阔的红色海洋中。这一年是文革最凶猛的一年,他走的这一天是“人日”。作为人,他应该很圆满;作为文人,他觉得应该这个时候走,作为文人在这个时期是绝望的。
1949年我爷爷的积蓄被私人银行拐骗到了台湾,加上政治上的惊吓,报馆里有人说他是国民党特务,他得了一场大病,脑中风,差点过去。家里只好卖掉了砖塔胡同口的一所大院子,支付医药费,住进了这所43号小院。从这样的院落里出来的人家可以是北京很普通的一户人家,这所院子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没有老北京的凉棚和鱼缸,我爷爷还是要把它收拾得好一些。院子里扎了一个花架子,种了牵牛花和丝瓜,西屋种了一棵榆叶梅和两盆盆栽石榴,在他的窗前北屋,栽了一棵柳树,一棵黑枣树。到了他的晚年,这些花木也渐渐凋零,黑枣树很少结枣。我问长辈为什么。大人说,树上虫子太多。于是我盼着有啄木鸟能来,这是童年的我所知道的唯一树木除虫方法,我盼着它结出丰硕的果实。小时候我很馋,只要能吃的,都要寻思。
周总理派人来看望我爷爷,邀请他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了解了他的病情之后,文化部艺术局长、他的老友马彦祥向周扬反映了我家的困窘生活。经研究,文化部决定聘请我爷爷担任文化部顾问,中央文史馆馆员,每月支给他一笔钱,北京市文化局又给了一份补贴,相当于正部级的月薪了。我爷爷看病也转为公费医疗,这下帮助我家渡过了难关。
我爷爷体会到了新社会的温暖,也感谢党的关怀,但他的信条是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如今拿着干薪不干事,违背了他的生活信念,他良心会感到不安。不待病好就决定继续写作。大病之后,他的记忆力不行了,过去文思泉涌语言词汇信笔即来,现在寻思良久还找不到适当的词汇。他深感写作能力不如以前,无法再写长篇巨著,便决定改编民间流传的爱情故事。他选中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中篇故事花费了我爷爷巨大的心血。他搜集了30多种有关的词曲等资料,费了一番考证的功夫,首先确定故事发生在晋代,然后考证晋代的民俗、服饰、用具,力求真实地再现这段历史,几万字的稿子竟然反复修改达十几次之多。爷爷的创作一般都是一挥而就,他同时能写四五部小说,还从来没有这样过。
《梁山伯与祝英台》在香港的《大公报》上打响了,海外华侨报纸转载的很多。后来在砖塔,他将中国的民间故事改编了一批。这时候他创作的《五子登科》、《八十一梦》、《魍魉世界》、《啼笑因缘》在1957年前后又出了一批单行本,他的作品被市民所熟悉和喜爱,这使他感到欣慰。这时候他又有了比较好的稿费收入,他给马彦祥写信,辞去了文化部的薪金收入。有人统计这是中国大陆解放后唯一靠自己稿费生活的老作家,他是一个真正的自由职业者,在砖塔他终止了一百余部长篇小说创作,《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张恨水这位通俗小说大师的绝响。在写这篇文章时,我的电脑放着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我抑止不住感情的波澜,录下小说最后的一段文字,以为纪念。

银心对四九道:“这两只大蝴蝶,就是梁山伯相公、祝英台小姐的化身呀。”
四九看去,那两只大蝴蝶又展了翅膀,一上一下,一左一右,缓缓地在树林丛中、双碑新冢之间,飞来飞去。四九留意看它,看向哪里飞去。只见两只蝴蝶此来彼往,越飞越高,飞进苍松横枝,忽然不见。
安徽天柱山下:我们家族不屈的武魂
我爷爷的爷爷张开甲公,自幼习武,是家乡有名的力士,14岁时能挥百斤巨石,如弄弹丸。开甲公15岁时,被迫抽丁,入湘军曾国藩部,从征十几年,出生入死战功卓著。据县志记载保过三品军功,爷爷也有过对他爷爷的回忆,应该是真实的。开甲公还有一绝活,不练武功的人以为是神话。夏天吃饭时一只苍蝇飞绕,只见他一双竹筷向空中一伸,居然夹住了苍蝇,苍蝇的翅膀折断身体完整。爷爷在《啼笑因缘》一书中,有这样的细节,关寿峰请樊家树吃饭时用筷子夹蝇,表现的绝技实际上是张家祖上的绝技。我的曾祖父字耕圃,讳钰,也是一身好武功在身,和土匪打过不少恶仗。由于打得一手好算盘,他当上了一个小税官,他为人正直办事认真,深得乡里爱戴。乡下的宗族械斗也由他来摆平。他摆平的方法很简单,摆开场子长矛短剑一通狂舞,舞罢他带来的税警随从鸣枪示警,双方被我曾祖的超群武艺和诚恳言辞所折服,我的曾祖父张钰凭着他的武功和为官清廉成为德高望重的人。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武侠小说盛行,有人统计有170多人在写武侠小说,总数超过千部,字数超过3亿,应该是盛行了,而爷爷的武侠小说在内容上是对当时武侠风的一种改良。
在我爷爷的早期作品中,写有武侠小说《剑胆琴心》,书中在描写人物的武功时,力求做到的是现实生活可能发生的事情。他鄙弃当时武侠小说中 “口吐白光飞剑斩人头”的描写,这是从祖上对他心灵的渲染,在武功的描写上他有着先天的影响和优势。《啼笑因缘》是一本言情加武侠的小说,通过关寿峰和关秀姑父女俩的侠肝义胆大大满足了上海小市民要看噱头的愿望。我爷爷1934年做了一次西北旅行,路经河南时亲眼看到河南的红枪会、民团等地方民众武装力量,他想通过他的文字教育他们爱国,灌输民族意识,教以大忠大义,来取代他们身上的小仁小义,江湖义气。鉴于当时的形势不能直接宣传抗日,他便取清末河南绿林首领王天纵响应武昌起义,聚众起义之事,宣传保国保种的爱国思想,写就了新派武侠小说《中原豪侠传》。
安徽省为桂系军阀所控,他们与中央军矛盾重重,三爷四爷他们途径岳西县时经人介绍认识了国民党驻皖部队徐源泉将军,徐将军不但批准了潜山游击队,还提供了一批弹药枪支。这支坎坷的游击队,后来被认为是非法武装,强令解散,但是三爷爷还是从了戎。爷爷根据他亲弟弟的经历写下了我国抗战文学的先锋作品《冲锋》(又名《巷战之夜》)。
苏州盛宣怀家祠:开始偷偷写小说
我爷爷从小当然有过大学梦,甚至想出国留洋,学习科学报效国家。爷爷17岁时曾祖不幸因病去世,临终前把赡养母亲和三个弟弟两个妹妹的家庭重担托付给了我爷爷。家里断了经济来源,祖奶奶带着六个孩子只好回到老家潜山,那里还有几亩薄田和几间老屋。
18岁我爷爷考上孙中山先生在苏州所办的蒙藏垦殖学校,依靠上海的亲戚交了不多的学费和食宿杂费,于是来到了苏州。这是他断断续续上过的学堂中一个重要的学校,也是他在履历上唯一可以体面地填写的学校。
蒙藏垦殖学校的环境很好,空气中都有阳光和植物的气味。校址设在闾门外盛宣怀家祠里,就在留园隔壁。盛宣怀是清末巨富,房子又大又好,宿舍窗外,就是花木扶疏的花园。尤其是理化讲堂,是一幢小洋楼,楼下是花圃,五颜六色,送来阵阵花香。窗外是留园,竹幕掩映,假山婷立。
学校环境虽好,无奈经费不足,原来校长由上海都督陈其美兼任,他是一位著名的革命党人,这时辞职了,换了一个姓仇的代理。仇代理人在北京,校务无人负责,学校常常停课,学生对校方不满,又常常闹学潮。我爷爷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在这里上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深感学业的渺茫,他怀念自己的亡父,忧虑在潜山家人的生活,深感自己作为长子而未能挑起养家的重担,更不知白己何日才能干出一番事业。彷徨、郁闷,比起在乡下时反倒更厉害了,遣愁的诗词也作得更多。因为穷,爷爷开始找出路,他那时每月总要节省两角钱买一期《小说月报》看,在背页,《小说月报》有征稿启事,并定每千字3元,爷爷偷偷地作起应征的小说来。
“为什么偷着写呢?就由于怕人家笑我不自量力,这理化讲堂,是一幢小洋楼,楼下是花圃,楼外是苏州名胜留园,风景很好,我一个人坐在玻璃窗下,低头猛写。偶然抬头,看到窗外竹林依依,远远送来一阵花香,好像象征了我的前途乐观,我就更兴奋地写。”爷爷已经成为著名作家后,是这样回忆他的第一篇作品的。在3天的工夫里他写了两个短篇,一篇是《旧新娘》,是文言的,大约3000字,一篇是《桃花劫》,是白话的,约4000字。稿子写好了,寄出去了,但并没有抱太大幻想,因为他对《小说月报》的作者一律认为是大文豪,而自己实在太渺小了。事情也有意外,几天后,一个来自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信封,放在我爷爷寝室的桌上。他以为是退稿,悄悄地拆开,里面没有稿子,是编者恽铁樵先生的回信,信上说,“稿子很好,意思尤可钦佩,容缓选载。”我爷爷欣喜若狂,将这一喜讯告诉了要好的同学,同学都认为垦殖学校前途暗淡,既然文学底子很好,不如就在文学上找点出路。
我爷爷还和恽先生通过两封信,文学的大门在这时好像已经打开,可那两篇稿子,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只等恽先生交出《小说月报》给沈雁冰,总共等了十个年头也没有露脸。当然十年以后我爷爷已经大名鼎鼎,不再需要靠这两篇东西闯牌子了,但为什么他如此耿耿于怀?大概就是常常会想起自己的处女作吧,他会回忆他的起点,起点是《小说月报》没有采用的投稿。
还是说当年的现实问题,我爷爷在学校怎么混?又穷得叮当响。我爷爷是长子,出来读书又不放心家里,可实在找不到什么良图,只有伤感而已。这种伤感渐渐在他的性格中积淀下来,成为他独具的气质,后来渗透在他的创作里,形成他独特的风格,在二三十年代,它倾倒了无数市民。二次革命爆发了,垦殖学校是孙中山办的,也挂起讨袁旗帜以壮声势,但是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垦殖学校也被解散。我爷爷没钱,不能投考别的学校,只好再次回到潜山老家。
1994年,我爷爷诞辰100周年,我和我二叔带着爷爷的一笔稿费来到老家,来到黄岭小学。新盖的校舍因为资金短缺,还没有安上玻璃。我二叔说,还是把爷爷的稿费捐给学校吧。不能再让老家的孩子们因为没钱读书而伤感,也不能让孩子们将来再写那样伤感的文章。这恐怕也是我爷爷张恨水的心愿。
湖北汉口:笔名“恨水”的由来
年轻人在家闲散着肯定不行。
爷爷20岁时东挪西借地凑了点钱,族兄和本家在汉口,搞文明新戏和小报,他冒着风险到汉口去。那位本家在小报馆里当独角编辑,爷爷到了汉口,亲戚也还算欢迎,寄寓在一家小杂货店楼上,天天到小报馆混几个小时,写些小稿子补补空白。那种小稿子居然有人看,有人说好,虽不得钱,我爷爷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恨水的名字就是那时开始用的,在以后的四十年里渐渐被老百姓所熟悉,他的本名心远已经很少有人知道。
早在垦殖学校作诗的时候,他就用过笔名“愁花恨水生”,后来爷爷读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他取了最后一句恨水两个字。
有很多人很神秘地问我,你爷爷和冰心是否有爱情故事。在这里我负责任地说,那纯属老百姓望文生义演绎出来的故事。恨水,冰心,恨水不结冰,怪贴切的,这个故事传播得太广,甚至比爷爷的文学作品还要普及,我们已经纠正了几十年,还有人这样问,我看到了老百姓的“顽固”。以后再有这样的问题我只会微笑着摇头,决不执一字一词。
我的老家是安徽安庆潜山县岭头镇,这里山清水秀,不仅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更具有极其丰厚的文化底蕴,融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精华于一体的古皖文化。距离潜山岭头镇不过二十公里的河镇,就是京剧鼻祖程长庚的家乡,近代以后开始流行弹腔、徽调和黄梅戏。弹腔是大戏,黄梅戏是小戏,到了当代,小戏黄梅戏却流向全国成了大戏。我爷爷儿时除了沉浸书籍中外,最大的娱乐享受就是看戏。他还有“程大老板同乡”印章一枚,这是他对程长庚的敬仰和作为同乡的自豪。到了晚年他还在怀念家乡的戏剧。1958年他写了《潜山春节》:“村前正唱采茶歌,百副花灯未算多。狮子蚌精相对舞,一班刚到一班过。”我请教安徽师范大学的谢家顺教授,他说,“采茶歌就是黄梅戏。”戏剧艺术对我爷爷后来文学创作的影响和熏陶是极其重要的。我爷爷后来办副刊《戏剧杂谈》便是他热衷的一个栏目。
前面说过我爷爷是个大嗓门,为了生存,他19岁由堂兄介绍,来到文明进化团。这是个话剧团,剧团老板就是当时鼎鼎大名的话剧艺术家李君磐和陈大悲。尽管我爷爷嗓门很大,长得也很精神,但毕竟不是演戏的料,他跟着话剧团主要的工作是写写说明书、传单、广告之类的杂活。话剧团到湖南常德演出,我爷爷初次登台客串了《落花梦》,他后来回忆说:“派我一个生角,是个半重要的角色,大家公认我演得还不错。”从演戏开始,他同时拉开了自己艺术人生的帏幕,从他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只是此时他的才华无处伸展,心情还是郁郁寡欢的。他已经20岁了,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人生方向。
爷爷的首要问题还是生存。
(摘自《我所知道的张恨水》,张纪著,金城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定价:2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