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索夫
加莉娜•达尼埃尔耶夫娜•克里莫娃生于莫斯科,1972年毕业于国立列宁莫斯科师范学院地理——生物学系。1990年进入高尔基文学院,师从叶•维诺库罗夫。她的作品包括《俄罗斯的自由诗选集》(1990),诗集《留局待取》(1994)、《直接话语》(1998)、《空气中的笔记》(2002)、《北方——南方》(2004),还曾编选《莫斯科缪斯1799-1977》(1998)、《莫斯科缪斯17世纪——21世纪》(2004)等。现任俄罗斯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主编,《各民族友谊》杂志诗歌编辑部主任,居住在莫斯科。

在哈尔滨发生的一切——我认为是奇迹!
只有命运之神能够馈赠这样的礼物。
我从哈尔滨回到北京与俄罗斯作家代表一起继续参观访问,回京的第二天,著名作家弗•沃伊诺维奇半真半假地说:“令人震惊的故事!把这个情节卖掉吧……”
女作家维•托克列娃则建议:“我们写一个电影脚本吧……”
我的朋友们对这一奇迹都感到震惊激动不已。莫斯科几家出版社提出发表短篇小说《侨居哈尔滨的吟唱班领唱》(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而我选中了《大陆》杂志。
我的亲戚们则更加激动,他们从以色列寄来了家人的旧照片,现寄给你们。妈妈不住嘴地叨念:“可惜,你爸爸没有活到今天……”
在保加利亚,人们知道我是诗人,我的这个短篇立刻被译成保加利亚文发表。来自哈尔滨的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们对此也很感兴趣,他们与我在莫斯科相见,他们是来参加学术会议的,这是在小说发表三个月后的事,这次会见非常有趣,是非官方性质,我把这篇小说稿和若干家庭照片给了他们,他们赠送给我关于哈尔滨犹太人历史和文化的精美画册。
我曾游历过世界很多地方,但只有中国对我尤为亲近,因为,我的根系之一深深扎在中国土地之中,我的叔祖父所罗门在中国找到了永久的归宿……我对他的妻子和长子的情况一无所知,也许,他们也长眠于这个墓地之中,在离他不远的地方。
令人难以忘怀的哈尔滨碧空,我渴望再一次漫步在松花江畔、中央大街,再次经过“马迭尔饭店”,再次走进我叔祖父曾吟唱和祈祷的犹太教堂。
多么渴望,在我找到的墓前敬献鲜花。
——加莉娜•达尼埃尔耶夫娜•克里莫娃
俄国人公墓位于哈尔滨郊区开阔的山岗上。我们那里,在这样高高的山岗上通常修建教堂,高耸入云,以便俯视人间的芸芸众生。这里,却不吝惜在这座山岗上修建公墓。公墓不大,也不壮观,与巴黎市郊的圣-热纳维耶芙-戴布瓦公墓无法相比,尽管哈尔滨被誉为东方的巴黎。考虑到时间和地点,对坟墓、墓碑和东正教十字架的简陋也就不容挑剔了。墓碑上有纯俄国人的姓名——乌斯吉诺夫、扎伊采夫、库兹涅佐夫,也有与中国人的姓名混合一起的——伊凡•伊凡诺维奇•朱、江萍•福明娜。公墓上空孤寂阴冷的风吹拂着,时而发出低沉的哀号。公墓除了我们之外别无他人,这里早已没有俄国侨民了,再也没有什么亲人前来拜谒和祭扫了。
丽玛抓了一把土装在塑料袋里,我们默默地向停在不远等候我们的汽车走去,阳光洒满大地,放眼望去一片熟悉的平原景观:开阔、平坦。一切像在家乡一样,呼吸着新鲜空气。
猛然,在只有几步远的地方,在汽车附近,我看见了另一个公墓入口处的白色拱门,六角星在金色阳光下格外清晰。

“我有很多的叔叔、伯伯和姑姑!”我父亲那很像播音员的嗓音仿佛在我童年记忆的黑色音箱中重新播放了出来,“我的祖父也就是你的曾祖父莫伊谢•兹拉特金是普里亚尼契卡村人,他活了一百一十一岁,生了十三个孩子,他们现在都在什么地方呢?我知道,有一个在哈尔滨,他的工作是教堂吟唱班领唱……好像叫所罗门。不过,我的好女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对谁都不许说半个字,要是说了出去,我们大家就……”父亲用大拇指在脖颈上划了一下,好像剃须刀割着脖颈一样。
当时,我第一次听说吟唱班领唱这个词。
而今经过了五十年父亲的这些话在我的记忆中复苏,具有了新的活力,自从丽玛•卡扎科娃提出让我与几位作家一起飞往中国的那一刻起,这些话牢固地嵌在我的心中。我的内心立刻发热,燃起了希望——如果万一?
“看,犹太人公墓……如果他在哈尔滨去世,那么,他是不是可能葬在这里呢?”
枝叶茂盛的粗壮桦树投下了大片荫影,墓碑和石板排列有序。墓地整洁肃穆。同样没有人,没有人等候什么人来,也不会有什么人来。在希伯来语中俄语有另外的写法,不过姓名也多为常见的:拉比诺维奇、海曼、卡茨、斯梅良斯基……
“他姓什么?”丽玛问我。
我们分别走在墓间小道上,读着有时模糊不清的,有时是全新的,涂有金字的碑文。
我第二次听说关于吟唱班领唱这个人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那时妈妈从澳大利亚参加医学大会回来,会议期间她住在悉尼的一位教授家里。
“您姓兹拉特金?”教授把斟满香槟酒的高脚杯递给我妈妈,并问她,“请原谅,你们家有什么亲戚在哈尔滨吗?”
他准确无误地把重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上。
“我丈夫的亲叔叔在那里,”妈妈喝了一口酒回答。
“……犹太教主教堂的吟唱班领唱,”教授继续说,“我们认识他,到现在我们都还怀念他呢!他叫所罗门•莫伊谢耶维奇,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他的那副好嗓子别提多美了!演唱歌剧都绰绰有余。在哈尔滨他与夏里亚宾见过面,当时夏里亚宾住在‘马迭尔饭店’,他举行音乐会时,兹拉特金甚至还为他演唱过呢。这个饭店现在还有,就在中央大街上。夏里亚宾高度评价圣歌、颂歌这类音乐艺术,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专家。您本人有没有听过你们叔叔的吟唱?”
“您说什么呀,我们从哪儿能听到呀?要知道,我是俄国人,受过洗礼,我的娘家姓奥列什金娜,我是苏共党员。犹太教教堂连参观都没有去过,虽然,我们家不远就有一个……我丈夫是犹太人,他姓兹拉特金,不过他也没去过犹太教教堂,也不会自己的语言,只会在节日酒宴上说一个词:‘尽情地喝吧!’……他也是苏共党员,当过民兵,上过前线直到战争结束,他在建设部工作,是基本建设处处长……他特别喜欢唱歌,是个男中音,唱得美极了,我甚至可以说,具有演员特有的歌喉,是祖传的基因,我听过很多歌唱家的演出,喜爱歌剧,特别是俄国歌剧,但是听教堂吟唱,从来没有机会。”
“非常、非常遗憾,吟唱班领唱大大超越歌唱家。这种音乐像音叉一样准确无误地为祈祷文定音!它使人一瞬间忘掉操劳和忧伤,忘掉忙碌,撕下我们那漠不关心、冷酷和麻木不仁的面纱。这需要灵活多变的歌喉,不然怎么能够表达微妙的情感、内心感受和细腻的思想呢……这是特别古老的一种圣歌。多么美妙动听啊!你们,你们是这位天才、这位领唱的至亲,你们却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吟唱,他唱圣歌时全城都会一片寂静……要知道,他经常在剧院、在音乐会上演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自由艺术家,虽然他在犹太教主教堂任专职……难道在莫斯科不是这样吗?”
妈妈无言以对,教授又添加了冰镇香槟酒,继续说:
“那位吟唱班领唱非常受尊重,可是不富有。我确切知道他有一个儿子死了。吟唱班领唱的小儿子血气方刚,是个充满幻想有信念的青年,他毫不掩饰对马克思和列宁的好感,他去了苏联。于是发生了不幸,确切地说是命运。他是犹太家庭教育出来的,有礼貌,行为举止都很得体。”
在莫斯科我们听到这一番话以后感到震惊,我们相信改革的浪潮冲到了我们家,再也不能否认我们在国外有亲属这样的事实了。
关于这位吟唱班领唱的事我就再也不知道更多了。
在犹太人墓地从一个墓向另一个墓缓步走着,突然内心感到颤抖、翻腾,从心底向上涌……妨碍呼吸,妨碍行动,不过清楚地知道这不是发冷打寒颤,而是不可名状的热产生的颤抖。纯粹玄而又玄的感觉,是心灵?是精神?类似的感觉有一次曾体验过,那是在耶路撒冷圣地,当时我觉得我的躯体已不复存在,代替躯体的是某种轻飘飘的东西,我毫无恐惧地意识到这一点。做了几次深呼吸,以便继续向前走,就在前面五十米左右的地方,在修剪一新的草坪上坐落着一个墓!石板简陋,边缘有点破损,上面的字是
犹太教主教堂吟唱班领唱

所罗门•莫伊谢耶维奇•兹拉特金
1953年11月24日
5714年17日 逝世
所罗门,我找到你了!
这是我们之间的心灵在呼唤,您等待了很久很久,企盼着在人世间关于对您的缅怀得以复活并永存,在您的墓上有人洒下热泪。
是您,所罗门唤起了我对家庭系谱树寻根的渴望。上帝以令人莫测的道路把我带到了您这里,创造了奇迹……我飞到了中国,乘火车到了哈尔滨,仅仅经过两个多小时找到了亲人的墓,难道这不是奇迹吗?这简直像大海捞针。
这是天意神助!
生活中各种离奇的事远比魔幻作品有力得多。
看来,我的这类意外的巧合、难以置信的奇遇具有遗传基因。
在战争期间我爸爸达尼埃尔•费奥多罗维奇•兹拉特金在卡累利阿前线打仗之后到了彼尔姆。他很饿,早上去了市场,想把几包香烟卖掉,或者换点食品,当地卖八百卢布一包烟,他卖七百卢布,一下子排起队来,其中有一个妇女,盯着看我爸爸,他有点不耐烦了,说:
“我说女公民,您总是看着我干什么?站在那里,什么也不买,为什么一个劲儿地盯着我?”
“您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儿子,他很像您,一模一样,”她大声哭了起来,“您想吃东西,是吗?走,到我家去,我让您吃个够……认识一下我的女儿!”
“瞧,简直是个媒婆……想把我带到她女儿那里去。这可不是无缘无故。当然去,我这个当兵的有什么好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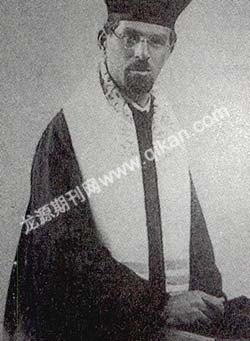
家里虽不富裕,倒也整洁。一位姑娘走上前来,青春已过,闪出犹太人带有愧色的眼神。大家坐下吃午饭,没有问他姓什么,叫什么,他们对此不感兴趣。她只谈儿子死得很惨,而客人与牺牲的儿子出奇地相像,妈妈痛哭之后到另一个房间休息去了。
“你们坐着,好好聊一聊……丹妮娅,给士兵看一看照相本。”
丹妮娅翻着相册,说:“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就是哥哥,而这个是我舅妈,她在列宁格勒,这个……”
我父亲当时喘不过气来,泪如雨下,号啕大哭,边哭边指着一张照片,上面有一男一女和两个孩子——男孩和女孩。
“妈妈,妈,你快过来,他感觉不好,”丹妮娅喊着。
她妈妈只穿一件衬衫就忙不迭地跑了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会有这张照片,他们是谁?”
“这是法布斯,我的弟弟法布斯,”女主人镇静地回答说。
“就是说,您是我姑姑!这是我父亲、母亲、姐姐和我。”
“啊,真的是你,我的侄子,我的好孩子,我亲爱的!怪不得我一直看着你,你长得和我的儿子一模一样,你那可怜的表哥……这么说妈妈的心——心灵感应!”
就这样,一夜之间我父亲找到了亲姑妈盖妮娅(可能叫盖丽艾塔)和表妹丹妮娅,并且同时还知道他父亲的真名叫法布斯不是费佳。

不久前,我堂姐艾拉全家办理去以色列定居手续时(为此必须提供很多证明他们是犹太人的文件),我们惊奇地发现自己祖母的名字不叫克拉拉,而是叫哈娅……
我站在吟唱班领唱的墓旁,回想1953年夏天,当时所罗门还健在,爸爸第一次领我到尼古拉耶夫去看望祖父、祖母。当时我五岁。他们的长形砖砌的独家住宅坐落在法列耶夫斯基街,祖母早已等候在大门口,看到我之后她用干燥冰冷的嘴唇不停地吻着我的前额,我紧缩全身,大声喊着:
“爸爸,你在哪儿?”
“你怎么这样说话呢?难道没有学会把父母称作“您”吗?”祖母公开斥责说。
我明白了,从第一眼我就不讨她喜欢,虽然爸爸替我说话,他说时代不同了,规矩也改变了。
克拉拉与别人截然不同。
我女朋友们的祖母当中没有一个人在家里穿着高跟便鞋、漂亮的衬衫,别着胸针,或者身穿带有饰物的丝绸连衣裙,几乎所有时间手里都离不开书本。那么她什么时候做饭,洗衣服或者打扫房间呢?看样子她不会干家务、也不关心这些,虽然父亲说克拉拉幼年时曾是孤儿,住在并不富裕的亲戚家里。我当时作为孩子很可怜她,特别想弄明白孤儿是怎样长大成人的……克拉拉从来没有放过牲口,没有挤过羊奶,没有饲养过猪和鸡,不像我的外祖母费妮娅。克拉拉从来没有砍过白菜,没有在散发着刺柏香味的木桶里腌过黄瓜和蘑菇,为了漫长而半饥半饱的冬天,为一大家子人和客人做食品储备。然而,她会烤带水果馅的酥皮甜点和做填馅的鱼。她会弹钢琴,会唱歌,唱的不是费妮娅唱的那些俄罗斯歌曲和乌克兰歌曲,而是表演歌剧,被称作咏叹调、练声曲、独唱短曲。
出嫁前,克拉拉•杰普利茨卡娅在音乐学院毕业后在奥德萨歌剧院当合唱演员,不久嫁给了银行小职员费奥多•莫伊谢耶维奇•兹拉特金,他比她小六岁,他们搬到了相邻的尼古拉耶夫,她开办了私人儿童歌剧院,上演音乐剧目,服装、布景都大获成功,感动了热爱子女的父母和易动情感的亲属们,引起了青少年演员的伙伴们的羡慕。主角多半是由阿妮娅和达尼埃尔——克拉拉和费奥多相差一岁的女儿和儿子担任。他们演出的古希腊神话歌剧的剧照至今还保存着。
这一切都发生在革命前,而十月革命以后,克拉拉只能作为一名默默无闻的音乐老师。

在那以后过了很久,试图寻根时我才感觉到我真的是克拉拉的孙女,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遗传性:我疯狂地爱上了小提琴,几乎成为职业音乐家,早在幼儿园我曾多次唱过浪漫曲,独唱短曲,十四岁的时候开始编剧,为了在短暂的夏天能够在诺金斯克儿童剧院演出,服装、道具都是从军官夫人们衣柜中挖掘出来的,还有我第一次接触诗歌……
“兹拉特金的血统,你和这个家族的人一模一样,”外祖母费妮娅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我的“艺术天赋”不知道是生气还是骄傲。
夏天在尼古拉耶夫,晚上闷热,吃着透心凉的西瓜,喝着冰镇汽水非常惬意。为此,需要买三公升汽水和红莓苔子果子露,赶快跑回家倒在杯子里趁汽水的泡沫还没有消失喝下去。全家围桌而坐等候吃饭,晚饭通常吃的有盛在深盘子里的大米水果粥(类似煮水果)。非常可笑。清晨我很沮丧,因为我明白了我在梦中自由自在游泳的暖洋洋的河流是什么——床褥上湿了一片,真太丢面子了。连睡在我身旁的胖猫“红毛儿”也溜走了。
我特别喜欢跟费佳爷爷去逛早市,好像在南方城市过节一样,鲜活虾在水桶里翻动着,货摊上摆着大头的虾虎鱼、黄灿灿的鲭鱼、晒干的竹荚鱼、新鲜的鲮鲱鱼,成堆成堆的玉米、茄子还有五颜六色的产品都在向顾客炫耀自己,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丰富美丽的市场,我永远记住并永远喜爱它。爷爷不善于讨价还价,不好意思。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始终是默默无闻、勤于持家的天使。
法布斯和哈娅——爷爷和奶奶的真名。
不,我们叫费佳和克拉拉。
生活,确切地说在生活面前的恐惧把他们弄成什么样子了!父母甚至不能对亲生儿女公开自己的真名实姓,要知道名字是神圣的,有些世袭的名字是命中注定的。他们离开犹太人定居区,为了按新方式适应新的生活,他们只好选择了新的,尽管是别人的名字……以新名登记办理护照,可能他们过的也是别人的生活。临终,也要以别人的名字长眠地下。那么,是什么人用他们的名字生活呢?
父亲很少与他的双亲见面,几乎不通信,这使他很痛苦,尤其是当他接到我祖父的来信哀求他给生病的母亲哪怕写几个字也行,那时他愧疚,甚至在我面前忏悔。克拉拉死于肺癌,此前她已经做过一次乳腺癌手术。有一次,我看见她高高隆起的假乳吓了一跳。克拉拉死在家里,很痛苦。她所疼爱的孙女艾拉准备出嫁,由于祖母病重,婚礼一拖再拖。克拉拉恳求不要推迟婚礼,不要改期,她渴望隔墙听到“苦啊!苦啊!”的喊声——新郎、新娘婚礼上接吻。她希望在自己家举办最后一次欢庆,虽然她已经不能弹琴助兴……是啊,家里早已没有钢琴:在战争期间,他们刚刚疏散到乌拉尔,家里就被洗劫一空。
我知道克拉拉乐于助人,无论是亲朋好友,无论是两旁外人,要么帮找栖身之处,要么介绍一些地址,要么给那些永远漂泊的犹太人钱和东西……也许这出自同情心,也许,是与犹太教精通经典律法的著名学者拉比留巴维契斯基的精神友谊和感人肺腑的交谈所产生的结果。
祖母逝世以后胖猫“红毛儿”也立刻消失了,没有克拉拉它也不想活下去。
这一切都是四十五年以前的往事了。
去年春天,我的堂姐季娜到尼古拉耶夫去,她前往克拉拉墓地祭拜,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没有被当地盗墓人破坏的奇迹般完好无损的墓旁、在波斯丁香树荫下一只红褐色的活猫躺在那儿……
为什么这一切回忆不可遏制地涌上我的心头?为什么恰恰在哈尔滨我命运中的犹太支系以莫名的方式突然闪现并大放光芒?爸爸已经不在人世。在他去世的前两年,八十六岁时,他受洗加入了东正教。终于信教了。看来,并非偶然的是他悄悄地说:“在哈尔滨我有一个叔叔,他叫所罗门……是教堂吟唱班领唱。”
爸爸,的确如此!

我找到了他!
陪同我们的中国朋友——翻译和当地文学杂志的主编、相貌喜人的孙丽(音译——译者),对找到亲人而感到的震惊和激动丝毫不亚于我和丽玛。赶快抓紧时间拍照,他们在记事本上记下了死者姓名、死亡日期,详细地询问了情况。就在那一瞬间,像劣质电影结尾那样,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士,他精神抖擞,戴一顶白色小帽子。
“你们好!”他愉快地问候,我们使用的交际语言是法语,交换了名片,他来自美国,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经理,前来拜谒他的先辈们。
“你们想不想做祈祷?”
“想做,”我立刻回答。
他拿出袖珍祈祷书,全神贯注开始用希伯来语读着祈祷文,我和丽玛站在他的左右呆然不动。
我是来自莫斯科的东正教徒站在不曾见过的叔祖父,犹太教主教堂吟唱班领唱的墓旁,不期而遇的来自美国的犹太人在我叔祖父的墓前读祈祷文——多少年没有人为他做过祈祷了?
我哭泣着。
此刻,为他祈祷——是上帝的意旨和仁慈。
随后我们去了犹太教教堂,从文化大革命起犹太教教堂和三十多个俄国东正教教堂都不再使用,在中国的天空下默默地耸立着。在哈尔滨已经没有犹太人了,但是,犹太教教堂成了哈尔滨犹太人历史和文化令人震惊的博物馆,在庞大的科学研究中心人们研究着不久前——只经过五代人——的历史遗产。
我怀着探索者激动的心情端详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前半期照片上犹太男人的面孔:具有贵族气派和风度,蓄着长须,他们是城市之父,家族之长。宴会、招待会、展示会。当地有名望的人们:银行家、工厂主、教会著名人士、工程师、医生、音乐家、运动健将。他们的美丽的妻子,幸福的孩子,他们和中东铁路的建设者们、俄国白军及移民们一起为哈尔滨的历史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哈尔滨是中国城市中最具俄国特征的城市,他们建造了美丽如画的哈尔滨,竭尽全力把现代风格移植到这里,使它与俄国的奥德萨、罗斯托夫、尼古拉耶夫非常相似。他们用自己的天才智慧和怀乡情绪营造了故乡的氛围。
我的叔祖父可能是这些人中的什么人呢?
等一等!瞧,是他的照片,确切地说是签名:吟唱班领唱,别无其他,没有姓名和日期。
“真不严谨!”我当编辑的职业习惯在内心挑剔着。
照片上的青年人脸庞窄小,眼睛不大,近视,这一切使我感到特别亲近。当然令我陌生的是,吟唱班领唱的圣衣和头饰,尽管眼眶的形式和我爸爸、艾拉、季娜,还有我的儿子雅罗斯拉夫的都完全一样,我儿子的眼睛是蓝颜色,头发深褐色,脸庞也是这样窄小,颧骨很高。
我多么希望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是所罗门!
他在这座教堂内吟唱,教徒们、妻子、儿女、朋友、邻居、崇拜者入迷地听着。这些人都在哪里呢?
也许,其中有人还活着,也许能够回应。
肯定有某些东西,除了坟墓之外至今仍留存着。
也许,档案馆中保存着,正等待着人们:如果不是我,那么可能是我的孙辈——要知道,犹太教主教堂吟唱班领唱、自由艺术家
所罗门•莫伊谢耶维奇•兹拉特金并不是在哈尔滨侨居的最后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