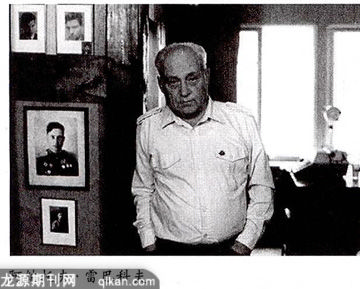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作家阿纳托夫·雷巴科夫(1991―1998)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在中国瞬间走红,短短一年间,就出了多种不同中译本。相形之下,雷巴科夫的遗著《长篇小说回忆录》就几乎不为人知,其实这部回忆录史料价值不低,而且很有趣,值得一读。本文为该书第二十五章,无题,题目为译者所加。《沉重的黄沙》写于一九七八年,以当时在苏联仍属较敏感的犹太民族为题材。《黄沙》转年即出了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就印了十万册。
我将题为《拉希利》(注:《沉重的黄沙》原名。拉希利为小说的女主角。)的长篇小说送交《新世界》。特瓦尔多夫斯基(注: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苏联著名诗人。曾两度出任《新世界》主编。)已去世,他的继任人科索拉波夫——党报的行政领导,为人正派,任内曾在《文学报》刊出了叶甫图申科的长诗《娘子谷》。现时主持编务的是诗人纳罗夫恰托夫,此人聪明,受过教育,曾就读于哲学、文学和历史研究所。过去他喝得厉害,但戒了。党的首长喜欢这样。他对长篇小说持警惕的态度,只有获得“上头”的批示,才能刊登。
只能这样了,《新世界》刊出过我的两部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预告过,但迄无下文,领导散文部的季阿娜·捷维克良,据我别列杰尔基诺(注:莫斯科近郊,为诗人、作家别墅区的所在地。)的邻居、剧作家亚历山大·克龙说,她为人开放。一九六二年曾积极参与揭发苏维埃作家出版社社长H·B·列休切夫斯基密告诗人鲍里斯·科尔尼洛夫和尼古拉·扎博洛茨基的行径。
把手稿交给她,开始等候回音。
我把长篇小说交给朋友阅读。
瓦夏·阿克肖洛夫读过了,到别列杰尔基诺来找我,就在窗口旁,不看我,只看着街道,审慎地说:
“咱们这儿登不了,有人会登。”——沉默。
从他的审慎中,即站在窗口旁,只管说,不看我,我捕捉到他可以帮忙的暗示。显然,存在着与西方文学团体的联系,存在着把我的手稿转到那儿去的可能性。他示意用什么谨慎的法子。《大都会》(注:苏联文学著名的“地下出版物”,由作家瓦西里·阿克肖诺夫主编,一共有23位作家供稿。)出版后,我的猜测获得了证实。
“在西方,这样的文学作品太多了,”我说,“应该在这儿凿穿墙壁。”
“留点儿神……”
谢明·伊兹拉列耶维奇·利普金(注:(1911年— ) 俄国诗人、翻译家、小说家。)喜欢长篇小说。我高度重视他的意见。杰出的诗人,诗歌翻译的行家,有着清白名声的人。阿克肖诺夫的文学丛刊《大都会》有参与者曾声明,如果它的作者中有谁受到什么惩罚,他们全体为表示抗议将退出作协。然而《大都会》的参加者维克托·叶罗费耶夫和叶甫盖尼·波波夫一遇到麻烦,只有两个人——利普金和他的妻子,诗人因娜·利斯尼扬斯卡娅——信守了上述诺言(不算阿克肖诺夫,他去了美国)。
尤里·特利丰诺夫(注:尤里·特利丰诺夫(1925—1981), 苏联小说家,相当一部分作品已译成中文出版。)对《沉重的黄沙》持复杂的态度。我俩很要好,我年纪要比他大得多,通过一连串的事件,我明白了,何以他在十三岁上就成了“人民公敌”的儿子,丧父(被枪决),失母(被押送集中营)。他隐瞒了这些情况,进入文学院,打这以后他一生的事业焕发出光彩。尽管领导散文研究班的康斯坦丁·费定(注:康斯坦丁·费定(1892—1977) 苏联作家,曾任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是一个随大流和看风使舵的角色,但青年时代小说写得不坏,对文学了解很透彻。费定很赞赏特利丰诺夫的才华,推荐中篇小说《大学生》参选斯大林奖金。一九五一年尤拉获奖了。这是正式的承认,但未必会令他感到荣幸。我想,特利丰诺夫对难以明言的东西比我们感受要强烈得多,实际上他也是这样。他佇候着自己的时刻。六十年代末他的几个短篇问世了。关于它们人们立刻议论起来。以后出版了《交换》、《长别离》、《另一种生活》、《滨河街公寓》、《老人》。他的作品大大提高了苏联散文的水平,他找到了自己的话,自己的形式。“公正”刺痛了特利丰诺夫,知识界瞬间将他的书一购而空,剧本《交换》和《滨河街公寓》在塔甘卡剧院上演时挤得水泄不通。在政治书籍出版社的《燃烧的革命者》丛书中,他写出民意党恐怖分子的“急不可耐”,获得其时“红色旅”猖獗一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高度赞赏和伯尔(注:海因利希·伯尔(1917—1985) 德国小说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本人的称赞。
晚上特利丰诺夫坐在中央法捷耶夫文艺工作者之家的饭店里,向别人出示德国人的赞扬文章。微微一笑,怡然自得。世界承认了他。长时间面对受伤害的自尊心的是孩子般天真的贡品,读过《沉重的黄沙》后,特利丰诺夫面挂宽容的讪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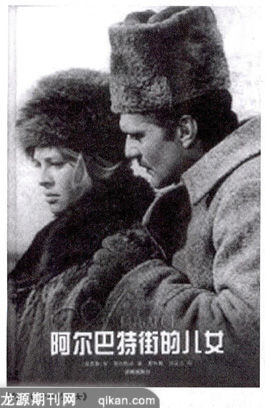
“托利亚,不要受骗了!大伙儿在夸你的长篇,但这还不是文学的顶峰。”
关于《阿尔巴特街的儿女》,手稿还我后,一般人都不说什么,只有一个人发现了:
“我把手稿交给萨沙·格拉特科夫(剧本《骠骑兵史诗》的作者,坐牢多年——雷巴科夫),他大吃一惊,你怎么把这段时间记得那么清楚。”
我不怪特利丰诺夫。我喜欢和理解他。他历经困难才获得自己的成就。他的天赋增强了力量,然而作家的才华令痛苦更甚,以至折了他的寿,一九八一年,特利丰诺夫去世,时年五十六岁。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日,我收到《新世界》的信:为确认我们的交谈,我遗憾地知会:我们不得不退回您的长篇小说《拉希利》,因为它未能纳入鄙刊的计划。季·捷维克良。
“谈话”确实是发生在这封信之前,更确切地说,发生在捷维克良关于长篇小说不可能在这段时间刊出的独白之前。独白颇具挑衅性,结果是我自己犯下错误,写出“无法通过的”的东西。
我把长篇小说送交名字似为《人民的友谊》的刊物。散文部的主管因娜·谢尔盖耶夫原来比捷维克良更坚决:“我们不会刊出这部小说,其时——一九三八年。战争是片面表现的——不但犹太人因战争而受苦,其他民族也一样。”
怎么办,投到哪儿去?我想起了《十月》杂志,我在那儿发表过长篇小说《司机》。潘菲洛夫(注:费奥多尔·潘菲洛夫(1896—1960)苏联作家,曾长期担任《十月》主编。)死后,杂志由符谢沃洛德·柯切托夫(注:(1912—1973),苏联小说家,代表作《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等均有中译本。)主持,成为反动力量的堡垒。知识界对杂志及其编辑嗤之以鼻。七十年代初柯切托夫死后,前线一代作家、阿纳托利·阿纳尼耶夫(注:(1925年—) 苏联作家。)被任命为总编辑,人们认为他还不错。他组织了新的编辑委员会,努力将开放的作者吸引到杂志中来。但他改变杂志声望的尝试全属徒劳——《十月》仍是反动的同义词。我估计,阿纳尼耶夫需要能吸引注意力的作品。
我与阿纳尼耶夫不熟,但认识杂志的编委成员格利戈里·巴克拉诺夫(注:(1923—)苏联作家。代表作《永远十九岁》有中译本。),同样是前线一代作家,请他把手稿交给阿纳尼耶夫。巴克拉诺夫读了小说。
“你知道,托利亚,我怕不成。我不是指一九三七年。而是犹太人……阿纳尼耶夫不见得敢冒险。”
“我请人——把我的稿件交给阿纳尼耶夫并说:‘雷巴科夫请你过目。’”
“阿纳尼耶夫如今在休假。”
“这样更好,把它放到桌子上。”
他把手稿取走,带回杂志社,放在阿纳尼耶夫的桌子上。后者休假回来后,在桌子上找到我的长篇,拿过来,阅读,打电话给我,请我到编辑部,解释说如果我同意修改的话可以刊出。修改些什么呢?编辑部其他同志读过后会下结论。
我不想用杂志里长篇小说陡生波折的故事来浪费读者的时间。我只想引用最长的(三页纸)结论中的几点:
阿·雷巴科夫长篇小说《拉希利》的编辑部结论。
在长篇小说的所有事件中,应赋予伟大卫国战争以全民、全民族灾难的特征,赋予纳粹主义——作为指向反全人类的思想体系,而不仅仅是反犹太人。
从小说中完全删去斯大林、莫洛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以及与之有关的议论。
完全删去列夫·拉赫连科(注: 《沉重的黄沙》中的人物,拉希利的父亲。)被捕和死亡的情节,以及所有与一九三七—三八年间政治审判有关的段落。
拉希利的呼吁应该不仅面向男人,而且面向所有人。
《拉希利》的书名应另改。
苏黎世市应改为瑞士其他德语城市。
散文部主任H·克留奇科夫
一九七八·三·九
所有这些类型的其余各点:删去、撤销、修改,不是犹太人,而是一般“人”等等以及诸如此类。副总编辑弗拉基米尔·茹科夫作了结论。他不明白:无论从长篇小说剔除多少个“犹太人”的单词,犹太人的小说任何时候都不会因而消失。
我把小说的名字改为《沉重的黄沙》,取自圣经(《约伯记》):“惟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言语急躁。”(注:引自和合本《圣经》第332页。)
评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与政治路线、与三十年代的审讯联在一起更困难。我想:同意,不同意?怎样活生生地剜下来。列夫·拉赫连科在小说中是作为“人民公敌”而被枪毙的——只好把他抛在火车下。德国人在前线撒的反犹太主义的传单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我把克努特·哈姆生(注:(1859—1952), 挪威作家,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二战时拥护德国法西斯。)的文本取而代之。但仍然成功地拈出了什么。甚至犹太人被害的这个数目——六百万人——被捂住的,它首先让我们在我的小说里披露了出来。
因为删节和修改,小说当然变得单薄,但它的主要激情仍在。
在《十月》刊出有一个优点非常重要。如果《新世界》杂志打算在第三期刊出小说,检查委员会要求提交整部小说,只有全部读过它才签署第一部分。在可靠的《十月》,检查员只读眼前的一期,而不要求读整部作品。这样我就过关了。检查员读过第一部分,似乎没啥反叛——革命前乌克兰的犹太小城,——签署,而当读到第二部分,然后是第三部分,突然发觉已经晚了,我已无从修改,腰斩,谁也担待不起。这意味着会酿成当前的文学丑闻。一九九五年在我选集中我把《沉重的黄沙》删去的一切全恢复了。
最可笑的是要求把苏黎世改成另一个城市,因为这时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列宁在苏黎世》出版了。他们害怕联想,甚至不允许发生在苏黎世!我把苏黎世改成巴塞尔。
以后,长篇小说业已独立成书,有人请我到苏共中央委员会,这样一个乏味的官员,就像过去带我到这儿的马斯林,手执一张小纸条宣读对长篇小说的批评。他毕恭毕敬地补充说:
“米哈依尔·安德列耶维奇的批注。”
我未能马上猜到,这个米哈依尔·安德列耶维奇是谁,后来一想——苏斯洛夫(注:米哈依尔·苏斯洛夫(1902—1982),去世前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在苏共其地位仅次于勃列日涅夫。),党的主要理论家,他不曾偷懒,读了书。不过,那时所有读《沉重的黄沙》的人都得在图书馆轮候。
苏斯洛夫曾就读于红色教授学院。乏味、平庸的沉重,他以这一点为人所知,在家里抄下列宁关于经济问题的主张的全部卡片。他公寓中的小房间里放满装着的卡片、引文和索引的盒子,列宁关于经济问题的每一句话都加以核实和抄录,这样一位一丝不苟、学究式的档案专家,端坐在家里抄卡片,孤僻而拒不应酬,也不钻营,因此得以完好无损。
有一次斯大林迫切需要为报告征引列宁关于一个小范围的经济问题的见解。斯大林机灵的秘书梅赫利斯(注:列夫·梅赫利斯(1889—1953),历任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苏联国家监察部长等要职。)谈到苏斯洛夫,他在红色教授学院的同学。赶紧去找他,马上找到他需要的。斯大林很清楚梅赫利斯的理论“极限”,问他,怎么这么快就搞到了引文。梅赫利斯谈到苏斯洛夫。打这起米哈依尔·安德列耶维奇便开始官运亨通,最终官拜政治局委员。其时关于苏斯洛夫升官的传说在莫斯科流行一时。
他的批评毫无价值,对小说没有任何意义,也不曾改变什么。我不曾加以反驳。只是想:“他们在干些什么呀,我们的领导人?在我们国家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吗?为啥他们自认有权干预作家的文本。?”
更有趣的是官员向我出示某教授的信,他确信,《沉重的黄沙》——犹太复国主义之作。“并非偶然,”—教授写道,“小说的主角生于巴塞尔,在那儿曾召开过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大会,某位凯尔茨利提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思想。”
我把杂志的“编辑部决议”放到官员面前:建议把苏黎世改为巴塞尔,这就是说让我再改上一次。我能改吗?在小说已为成千上万读者读过之后。
官员当然明白个中的荒唐,他两手一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