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罗·麦卡尼的音乐出版公司座落于伦敦苏豪(S·h·)广场,占据着一幢优雅别致的十八世纪建筑内的整整三层。他本人的办公室在三楼,从大厅乘狭小的电梯可达,也可以走楼梯。楼梯窄窄的,两边的墙壁上挂满了相框,里面都是麦卡尼自己和其他一些六十年代摇滚歌星的照片。其中还包括了一张布莱恩·琼斯(前滚石乐队的吉他手兼歌手)年轻时的黑白照。拍这张照片的人正是保罗的第一任爱妻琳达,她于1998年去世。
保罗的办公室俯瞰整个广场,内有一张拉盖书桌、一台老式的自动点唱机,两张大幅的德库宁(抽象派美国画家,荷兰籍)作品;地上铺着地毯,上面工整地印着音符--这样的摆设颇有点儿萨米·卡恩(美国著名电影歌曲作词家)的味道,但却是地地道道的麦卡尼风格。麦卡尼本人策划构思了第一张艺术品级别的摇滚唱片:《佩珀中士孤独心灵俱乐部》("Sgt. Pepper"s L·nely Hearts Club Band"),他自己也一直坦白,很渴望成为一名专业的音乐制作人。除了身为"甲壳虫"(Beetles,也被音译为"披头士")--这支盛行至今、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创作型流行乐队的成员之一,麦卡尼还独立经营着自己的MPL传播公司。公司拥有近三千项各类歌曲及百老汇舞台剧的版权,其中包括巴迪·霍利(美国垦荒时期著名摇滚歌星,其经纪人为"猫王"的发掘者)的专辑,《安妮》("Annie")、《红男绿女》("Guys and D·lls")和《火爆小子》("Grease")等百老汇经典音乐剧。MPL这一盛大的演艺帝国加上每一张售出的"甲壳虫"专辑所带来的版税收入使得保罗·麦卡尼贵为全英国富豪中的翘楚。当他楼上楼下的会计师们为他管理帐目忙得不可开交时,保罗自己却沉浸于创作不亦乐乎。五月我拜访时,他正事务繁多:两张DVD的制作,一张是他从前的一些影像作品,其中也包括了"翅膀合唱团"(The Wings)的一些歌曲,另一张则是《明眸我心》("Ecce C·r Meum"),一首阵容豪华的合唱。另外,他自己的最新流行乐专辑《流金记忆》("Mem·ry Alm·st Full")也在筹备制作当中。这是一张颇为怀古的私人专辑,多处鲜明地流露出了麦卡尼对岁月流逝的感怀,特别是随着他6月18日65岁生日的临近。他曾亲口承认这次生日仿佛人生中的一座里程碑,令他颇为费解。他悻悻道:"一想到就觉得害怕。仿佛,唉,总觉得不可能是我。"
麦卡尼坐在办公室里端的一个小沙发上,眼睛盯着跟前咖啡桌上的笔记本电脑。他身上套着一件灰色T恤,袖子长长的那种;暗红的裤子上有青色的格子。围他而坐的有他的项目经理帕迪·斯宾克、一名女助理和五个来自一家网页设计公司的年轻男人,他们会协助保罗共同完成预计下周上市的《流金记忆》。1962年,EMI百带唱片的乔治·马丁与"甲壳虫"乐队签下合约,此后双方一直保持合作。去年,保罗决定不再续约。他的新专辑将荣登星巴克公司旗下Hear Music的首张发行大碟。专辑的销售网络囊括了星巴克下面的所有咖啡店、各大唱片行以及iTune网络平台。iTune是苹果电脑公司下的著名在线音乐商店。("甲壳虫"乐队曾于1968年创立了一家多媒体公司,取名"苹果甲壳虫"。为此,苹果电脑公司的现任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之一史蒂夫·乔布斯一直与乐队之间就品牌名的使用权问题争论不休。)

麦卡尼感叹自己开始"厌恶"过去那种卖力推广成品专辑的做法。他觉得这样做有些"无聊"。他决定尝试一下全新的网络销售路径,因为这将会"和从前"甲壳虫"乐队发行专辑一样,激动人心。"问题是,保罗对于现如今盛行的网络下载的某些方面仍然感到无所适从。他首先过目了一张屏保的效果图,图片上他陷在一张黑色的沙发椅里。这张图片将在他的私人网站上被提供下载。接着,他开始和网络技术员们商讨如何制作专辑里《点点你的头》("N·d Y·ur Head")这首歌。
一位名叫尼可的设计员建议:"干嘛不把整张专辑的歌曲都放到网上去供歌迷们免费下载,然后让他们来自发地制作MTV?他们会自动把作品上传到Y·uTube 上。"(注:Y·uTube: www.y·utube.c·m 一个因特网网站,供使用者下载、上传及在线观看各类短片。)
麦卡尼朝坐在这圈人外围的斯宾克递了个眼神。尼克心想自己的建议怕是会遭否决,又接着解释说在网络空间里,你必须向歌迷们做出一定的让步,让他们来做主。然后看看他们会做出什么好东西来。他总结:"这就是"病毒式网络营销"的精髓所在。"(注:病毒式网络营销:viral marketing, 指通过用户的口碑宣传网络,信息像病毒一样传播和扩散。)
"不,不。"麦卡尼解释着,"我并不介意把整张专辑放到网上去。"他竭力想要表现出他乐于使用网络这一新生事物,但语气听来却有几分犹豫。他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斯宾克。
"好吧,我想想。"斯宾克开了口。
麦卡尼接着开始看刚完成的一个MTV,是要被投放到他的私人网站上的。画面里都是摇晃着的纽约一处音乐工作室里的场景。《流金记忆》就是在那里录制的。正当躬作一团、全神贯注地欣赏着剪辑后的效果时,麦卡尼突然冒出一句:"我们应该让大家知道这是我拍的吧,难道不是吗?"
"我们是可以这么做,但是--"其中一个技术员说到。
"因为如果迪伦(注:B·b Dylan,美国著名的民谣歌手,曾创作大量的反战民谣歌曲。他的风格对"甲壳虫"乐队的音乐创作有深远的影响。)
亲手拍了什么的话,我会很想知道的。"于是技术员们开始讨论怎样在作品中标明作者是麦卡尼本人。其中一人提议在作品图像上印上"保罗卡麦"(PaulCam)的名字。麦卡尼很喜欢这个主意。接着大家闲聊起来,保罗开始看起了手表。于是技术人员们迅速起身,保罗说着轻松的玩笑,和他的助理以及斯宾克一起把他们送到了门口。然后他套上了一件和他的裤子很搭衬的外套,踱步去附近的餐馆吃午饭。
麦卡尼刚走了两三步,便有一名身材魁梧、留着军人模样头型的年轻男子一个箭步冲到他跟前,使劲往他手里猛塞着什么。那是一张CD,"甲壳虫"的《西洋精选集》(The Beatles 1),上面已经有了一个黑色的签名。

"请写上"给Ll·yd"。"那男子说到。
麦卡尼照着签上。"给,伙计。"他说着归还了CD,然后双手插进口袋,继续前行。
那位歌迷突然出现的速度之快、力道之狠着实让人很不愉快。我不禁感言那个人说不定会成为下一个马克·戴维·查普曼。(注:Mark David Chapman:一位列侬的歌迷,患有精神疾病,1980年枪杀了列侬。)
"是呀,但也有可能是基督,带来保佑",麦卡尼有补充说,"当你注定气数已尽时,这是没办法的事。"
近年来,麦卡尼遭遇了一系列很不幸的重大损失:首先是与他相濡以沫二十九载的爱妻琳达死于乳癌;接着乔治·哈里森(Ge·rge Harris·n,"甲壳虫"乐队吉他手)在2001年死于癌症;再后来从去年开始,保罗与共同生活四年的第二任妻子希瑟·米尔分居。分居事件以及迫近中的离婚使得各类小报中充斥着关于二人的丑闻。其中一些甚至来自于法庭审判记录的泄露。里面的内容说到希尔指责麦卡尼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希尔还就某次麦卡尼在二人的争吵中将其推至浴缸里,并用酒杯碎片割伤她的手臂一事提出了控诉。我刚到伦敦的那周就发现大大小小的报纸争相报道着某位前任保镖的证词,声称麦卡尼一直以来受到抑郁症的困扰。对于所有传言,麦卡尼表示他尽力忽略。但对于那位"前保镖"的"声明",保罗颇感气恼:"当时我正在挑选别的报纸,然后就看到了这条新闻。","于是你就忍不住读了起来。发现里面一派胡言。然后你就得下决定,是不是要发表个声明,辩白说"事实不是这样的"。但问题在于类似这样的捏造实在太多。如果要一一应对,我的时间将会被白白耗光。就连吃饭、弹吉它或录制专辑的功夫都会不够。整天就是忙着辟谣。"基于这个原因,麦卡尼给自己定下了条原则:决不对任何有关离婚的传言作任何回应。

即使如此,麦卡尼的眼神里和他那沉默的举止间还是很清楚地流露出一股悲伤。就连他的最新力作《流金记忆》也不例外,充满了淡淡的忧郁。专辑里的倒数第二首曲子《最后的尽头》 ("The End ·f the End")是首听来颇为脆弱感怀的民谣。保罗在歌声中想象了自己会怎样离开这个世界。他还希望他的离去不会给那些还活着的朋友们带来任何的痛苦,而只是成为他们清晨醒来时的枕边谈笑。
在一家颇为昂贵、名为西格诺·祖里(Sign·r Zulli)的意大利餐厅里,一位笑容满面的餐厅领班前来欢迎麦卡尼的到来。他操着一口令人忍俊不禁的口音说道:"阿,"保拉"先生,您来了。您看上"却"气色不错。"麦卡尼随口答应着,抱歉地朝餐厅里的其他客人看了看。他被领到靠近餐厅大门的一张桌子就座。几分钟后,侍者端来了茄子做的开胃菜、主食意大利通心粉和一杯红酒。(麦卡尼早从七十年代初起就成为了一名素食主义者。)麦卡尼边吃边聊,谈起了过去作为一名"披头士"的生活以及他和约翰·列侬的关系。他回忆起当他第一次在列侬面前弹起《我看见她站在那儿》的开头部分时,列侬是如何摇了摇头。当时这首歌的开头部分为:"她那时十七岁/她从来不是个美丽的女皇。"他提到说《假如我倒下》("If I Fell")也许是所有列侬创作的歌曲中他最喜欢的一首。他甚至时常惊觉"甲壳虫"的诞生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他不禁疑惑地感慨:"这样的四个人居然能凑到一起。难道不令人觉得惊奇吗?"
此时,主厨从厨房里出来,走向我们这一桌。他请麦卡尼在他的夹克上签名。保罗习惯性地在他衣服的正面签上了大名,然后说该是回办公室的时候了。在走回苏豪广场的途中,他绕道进入了一条小巷。距离地面十英尺矮下去的一角有一处小商店。商店的一面墙上是由小块马赛克制成的拼贴画,看去颇为神秘诡异:一台电视机、旁边一个抽象模糊的人头。麦卡尼最近看了一些关于人物的摄影作品。他从中得到启发,决定在他自己的社区里举办个人涂鸦摄影展,以此为他的新专辑宣传造势。他拿出手机,拍下了墙上的图画。一个推着手推车的人漫不经心地路过,突然间仿佛意识到什么,傻傻站着盯着他看。
"嘿," 保罗平静地打了个招呼。
"要不要我用车推着你走?",一口标准的伦敦腔。
麦卡尼旋即放松下来。"好啊",他笑着说道。这时,一个戴着彩色墨镜的男人走了出来,粗鲁地将他的手机对准了麦卡尼。推车人随即往前逼近一步。直到这时,麦卡尼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堵在了一个小角落里。"呃--,好吧。"他勉强说道。于是戴墨镜的那个将手机位置调好,自己也转过头来对准镜头。咔嚓一声之后,默不作声地独自走开。麦卡尼表现出一股很明显的厌烦。他一边疾步前行,一边抱怨说:"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这样的。"推车人追了上来,索要签名。麦卡尼冷冷回道无名可签。那个人又开始恭维他,说很喜欢那张1983年发行的专辑《和平的笛声》("Pipes ·f Peace")。麦卡尼向他表示了感谢,迅速离开。步履加快。
他后悔地说:"刚才是我的错,我不应该停在那不动。"
第二天,麦卡尼由他的助手约翰·汉密尔驱车两小时带到了伦敦西南部的苏赛克斯郡(Sussex)。约翰跟随保罗已有整整三十二个年头。麦卡尼在苏赛克斯拥有一处自己的房子。他在房子附近建了一个录音室。这次来是因为和卡洛斯·保奈尔事先约好。保奈尔是一名很棒的古典音乐吉他手,他在帮助保罗用吉他弹奏协奏曲。麦卡尼在控制室旁的小厨房里等着。卡洛斯比约好的时间提前了几分钟到。"别的尝试古典音乐的流行乐手只是在他们的作品中加入一小段的古典乐曲。比如在一段九分钟长的曲子里加入两三分钟的古典音乐,"保奈尔介绍道,"但是保罗会专门设定一个音乐主题。他完全清楚古典音乐的作曲方法。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因为他甚至都不懂五线谱。"保奈尔解释了自己在录音室所要做的就是把麦卡尼用吉他和在电脑上写出的调子记录成五线谱。他俩首次会面是在去年五月上旬的某一天。正是在那天的早晨,英国媒体爆出了麦卡尼夫妇分居的新闻。见面之前,保奈尔还未听说此事。他回忆道:"那天我按时到达。在见到麦卡尼本人之前,他的助手提醒我说话要"谨慎"。我心里疑惑:为什么要"谨慎"?好吧,谁让他是了不起的"披头士"呢。然后我们见面了。他坦白直接地解释了一切,然后迅速地开始了工作。"麦卡尼对音乐的专心给保奈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时我们正在兴头上,电话突然响起。电话那头是保罗的律师。他起身接听,说上片刻。然后"嘣"的挂掉,立刻重新投入工作。"站在一旁的录音师史密斯·凯斯说道:"自分居后的几个月以来,他几乎每天都来。比以前更加卖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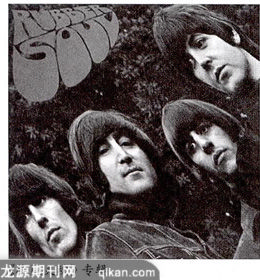
午后一点,麦卡尼重新回到了厨房。他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衫和棕色的灯芯绒裤子,看上去自信满满。前一天晚上,他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B.R.I.T Awards)。他的《明眸我心》("EcceC·r Meum")赢得了"最受欢迎专辑"大奖。麦卡尼在1998年着手准备《明眸我心》。他的前妻琳达当时正在和癌症抗争并最终去世。保罗回忆说:"琳达去世后,我时常忍不住掉眼泪。"我问他颁奖典礼后有没有出去欢庆。"没有。事实上,昨晚是我忙碌几个月以来睡得最好的一晚。"
他啜了几口茶,又返回控制室。那里挂着一些蜡染布块。最主要的摆设是一台长达二十英尺的六频混频器。保奈尔坐着,大腿上摆着厚厚一叠音乐稿纸。麦卡尼坐在红色的旋转椅上,面朝着大家。汉密尔递上一片全麦土司,上面涂着精制奶酪。他边吃边和史密斯谈起了前晚的典礼,他们俩当时都在现场。史密斯提及当晚获奖的两名女歌手,说她们在典礼结束后到处寻找麦卡尼。保罗叫道:"你在开我玩笑阿。"然后,他又用嘲讽、悲伤的语气加了句:"唉,她们太年轻啦。"
史密斯打开他电脑里的一个语音文件,是他们一年前录制的一首协奏曲的一部分。这首曲子完成以来,工作室里还没有人听过。史密斯说:"至少五月以后,没人听过。那真是一段糟糕的时光。"
麦卡尼也自言自语道:"至少是个糟糕的月份。"他转过身去,双脚跷在控制台上。
史密斯点击着鼠标,美妙的旋律随即从控制台上的音响里倾泻而出:弦乐器和黄铜管共同营造出凄美哀怨的氛围,而这一切又都被吉他弹奏的西班牙风格古典乐所覆盖。麦卡尼使用合成器做出了交响乐的效果,他计划以后用乐器把这种电脑合成的效果真正演奏出来。"长号的醇厚就能做到,"此时他的声音因为靠近混频器的原因而显得格外柔和动听,"哪怕用法式喇叭也能。声音很低沉。"
乐曲刚放完,他的一位助手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张CD。里面是保罗在最近一次电台节目里与吉尔斯·霍兰德(J··ls H·lland)以及一支小型乐队共同演奏的一首曲子。霍兰德是一名键盘手,英国人。他同时也主持一档电视节目。麦卡尼示意助手将CD放在播放机上。屋子里现在放着《今晚起舞》(Dance T·night)--《流金记忆》专辑里的第一首。歌曲中,麦卡尼弹着曼陀林。歌词听来颇为欢快:"人人今夜起舞/一切如此美妙。"但是他原本超级自然而平稳的嗓音却渐渐变得粗狂,歌里的小三和音也透露着悲伤。麦卡尼静静地听着,不时地跟着音乐点点头。等歌曲放完,保奈尔指出里面的曼陀林演奏有些地方走音了。
"是,我知道。"麦卡尼回答道,"但是我喜欢这样。"甲壳虫"一直把这个叫为"现场音"(A Fairgr·und S·und)--听着就像是当场演奏的。在我们早起的专辑里我们用过一些。" 当保奈尔在为吉他协奏曲的下个小节标上提示音时,麦卡尼仍在回忆:"我至今记得乐队第一次采用管弦乐队伴奏的情景。乔治·马丁会雇一些音乐家到百代的录音室。那时,这些古典音乐的演奏家们经常装模作样地假笑。一次,在录《嘿,裘德》("Hey,Jude")时,我们让那些人在歌曲的结尾部分加入一些拍手的声音。结果其中有个人严词拒绝。他还振振有词道:"我又不是被训练成拍手的。""话音刚落,保奈尔和史密斯就大笑起来。
保奈尔开始在稿纸上记录另一段吉他乐谱时,麦卡尼回忆起他曾经断断续续地尝试学会识谱:首先是在童年时期,他开始学钢琴时。后来很快他就觉得厌烦;之后,作为乐队的一员也试过一段时间,结果仍一样。他说:"现在,我甚至都不准备学了。好像从五线谱里读出来的东西总是和实际听到的不太一样。"他说列侬也不会读写五线谱。"一次,有人告诉我们说埃及的法老们不会读写。有专门的抄写员记录他们的思想。所以列侬和我过去经常说:"我们就跟法老一样。""
麦卡尼和保奈尔讨论了一会《浪漫》的配乐。这是一首甜美温馨的歌曲。然后两人来到了旁边一间屋子。屋子里铺着实木地板,有一台音乐会上用的那种平台大钢琴、电颤琴、吉他和其他一些设备。他们并肩坐在凳子上,透过面前的玻璃可以看到控制室里的史密斯。两人同时拿起了吉他,准备将麦卡尼想好要修改的一些段落重新弹一遍。但保罗却首先弹了一首巴赫(1685-1750,德国著名作曲家)的曲子。他说早在六十年代初时,自己经常和乔治·哈里森一起弹这首"宴会舞曲"。他演示了其中的一段后来如何成为了《黑鸟》("Blackbird")的前奏。他于是又演奏了《黑鸟》的一部分。突然,音乐戛然而止。保罗说道:"·K,回到工作中来。这些已经够有趣了,再弹下去我可得掉眼泪了。"
他让史密斯用扩音器放一下《农家男孩》("Farmb·y")的开头部分。这是一首五音符递增的乐章,吉他弹奏。麦卡尼早前录制的。史密斯照着放了出来,然后麦卡尼说道:"好,停。"他转向保奈尔,解释说想在里面加入更多的音符。
保奈尔弹了一段,音调变得更加丰富。
麦卡尼咕哝说:"我想里面的音阶可以变为原先的两倍。"所以,原先是……"他说着弹了一个琶音--"现在应该是……"他试着弹出脑海中想象的旋律,但却犯起难来。
保奈尔的手下迅速滑出一串音符。
"恩,"麦卡尼随口应了一声,有点心不在焉,"恩,应该还有一个音的,一个过渡音。"
保奈尔于是又弹出了一串递增音,比刚才的还要漂亮。
"哦,"麦卡尼轻哼了一声,语气中几分不确定。他试图要把心中的旋律唱出来,但又觉得实在难以把握。"只是每两个重复音,递增的音调。"他很坚持地指出。
保奈尔又试了一遍。
"耶,大概就是这个。"麦卡尼说这话时语气并不是很肯定。他建议先改下一段。二人就这样一来一往将近一个小时。
下午4:30,麦卡尼宣布工作到此为止。当天是周五。按常规,汉密尔会驱车将保罗送去米尔位于布莱顿(注:Bright·n:英国南部城市。)的家接他们三岁的女儿碧。麦卡尼担负着与米尔共同抚养碧的责任。他从不允许自己的工作占用任何与女儿相处的宝贵时光。去年二月,史蒂夫·乔布斯曾力邀他为苹果公司新产品IPh·ne手机的产品介绍会演唱三首歌曲。麦卡尼欣然答应了。但当他意识到那天正好是碧所在的托儿所放假的日子,他要和女儿在一起时又立刻婉拒了演出。
麦卡尼的父亲名叫吉姆,是一名棉花销售员。他同时也是利物浦的一名爵士乐喇叭手。他在二十年代组建了一支自己的乐队:"吉姆·马克爵士乐乐队",吹奏一些地方小调。麦卡尼的母亲玛丽是一名接生员。这个家都是靠她在挣钱维持。幼年时期,麦卡尼随着父母频繁地搬迁于利物浦的各个角落,口袋里没有一分零花钱。但童年在麦卡尼的记忆里仍然是快乐的,因为有音乐为伴。他的父亲时常在钢琴上弹奏爵士乐,并带他参加各种摇滚乐队的演唱会。十几岁时,麦卡尼开始听一些当地噪音爵士乐(英国的一种摇滚音乐)的歌。他深深地爱上了"猫王"和 "小理查德"(注:Little Richard:美国的另一位摇滚先锋,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呼喊型摇滚的典型代表。)。十四岁那年,他变卖了父亲赠给他的小号,买了把吉他。同年,他的母亲被诊断出患有乳癌。在经历了手术的痛苦之后,她最终离开。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麦卡尼写了自己的第一首歌:《我失去了我的小女孩》("I L·st My Little Girl")。对于这首情歌,麦卡尼在多年后回忆道:"我当时不认为自己写的东西和母亲有任何关系。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这首歌确实是为母亲而写。"他解释说,"我当时十四岁。突然之间你感到脑海里连她的模样都记不清。这很可怕,一种类似于突然跌入谷底的恐惧。"
为了能让两个儿子--麦卡尼和弟弟麦克按时上床睡觉,他们的父亲想办法在两人的房间里组装了一台收音机,并给他们找来了耳机。于是,保罗每晚都听着音乐和电台节目进入梦乡。对此,他感到"能够带来不可思议的想像"。他告诉我说《佩珀中士孤独心灵俱乐部》里一些对音乐很灵活的处理正是得益于早年他对一些电台歌曲的模糊记忆。一次,他回忆起小时候听一档电台节目。当听到耳机里爆发出的笑声时他竟如此的激动,感到无比神秘向往。突然,他灵机一动,构思出将专辑的开头变成众人的欢笑。"你无从知道到底是什么引得大伙笑成那样。难道是某人的裤子掉了?会是什么呢?用这些奇妙放飞你的想象,这就是我们追求的效果。"
(此处有一首插入的诗歌)
智慧
放纵身心,
感受你的一切,
我,惶恐中心颤;
无言以对,缄口沉默,
然心有渴求,她伴我左右;
惊叹着,
我竟无需遮掩,
智慧已经降临;
父辈旧人,言荡耳畔,
岁月流淌,智恍他方,
身形渐微,缥缈天外;
像孩提旋律,
音乐醉人,我翩翩起步,
闺房之间,我漫步轻盈;
爱你之前,
侧耳倾听,那外面的世界;
而今,我惶恐中心颤,
心中,独守一个秘密。
--伊丽莎白·麦克林
1957年7月6日,麦卡尼十五岁的某一天,他的朋友伊凡·沃翰说服他穿越整个利物浦城参加伍尔顿(W··lt·n)社区的教堂庆典。到时将会有一支高中生组合"石矿男孩"("The Quarry Men")摇滚乐队演出。当麦卡尼看到乐队主唱--十六岁的列侬居然用一个走音的吉他弹出了五弦琴的调子、在台上蹿来蹿去现场编唱歌词时,他完全惊呆了。等演唱结束,麦卡尼在后台找到了乐队成员,当即在钢琴前炫耀一番。他用钢琴弹了一首杰瑞·李·路易斯的歌(美国著名摇滚歌星和钢琴家),又借来吉他弹了一首艾迪·科驰兰(Eddie C·chran:英国著名吉他手)的《二十翱翔》("Twenty Flight R·ck")。几天后,从一位与二人分别相识的朋友那儿麦卡尼获知列侬希望他能加入他们的乐队。多年以后,列侬曾对"甲壳虫"乐队早期的传记手亨特·戴维斯坦白说对于麦卡尼的加入他挣扎了很久:"当时我是乐队的绝对领导者。如果让他加入进来,会发生什么呢?"
麦卡尼教会列侬如何将吉他的音弹得更和谐。他与乐队合奏了一首当地的酒吧舞曲,然后他透露自己写过一些歌。他把《我失去了我的小女孩》弹给列侬听。结果列侬以此为基础自己写了一首歌。渐渐地,两人开始一起逃学,成天待在麦卡尼的家里,潜心写歌。麦卡尼回忆说:"如果他写出了什么好歌,我就想写出更好的。他也一样。这就是我们合作的方式。"稍后,他又补充说:"我们俩都不懂五线谱,写歌纯粹是靠直觉。这让人很激动。你听到一段很动听的曲子,然后问"那个是哪里的?""怎么弄出来的?"而对方会说"我也不知道。"于是你就只能让他"再来一遍。""
就和所有其他满怀抱负的音乐家们一样,列侬和麦卡尼热切地渴望将自己的作品公布于世。在那个时代,他们没有任何参照的榜样。同时代的摇滚歌星们所演唱的歌曲都是由专业的词曲家所写。巴迪·霍利是个例外。麦卡尼谈起说:"我们很喜欢他。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就是那一天》("That"ll Be the Day")里面的歌词时的情景:"就是那一天,嘿嘿嘿,我会死去。"他顿了顿说:"死?这样的字眼居然出现在流行音乐中。这可有点儿吓人。我们喜欢这样的东西。"麦卡尼也很崇拜更老一些的创作人,如科勒·珀特、罗杰斯以及哈姆斯丹。当他得知列侬与他品味相同时很是欢心:"约翰最喜欢的歌里有一首叫作《小小的善意谎言》"Little White Lies"(由沃特·唐纳德森所写)。这让我十分震惊。我禁不住叫道"哇,天哪。我们居然如此相似。""就这样,二人齐心协力,努力探索如何将古典音乐里纷繁错杂的音调结构、深刻丰富的歌词含义以及灵活多变的曲调变化融入到摇滚乐的创作中去。
在结为挚友的第一年里,两个人一共写出了上百首歌曲。其中的两首《爱我》("L·ve Me D·")和《909之后》("The ·ne After 909")被收录到日后的"甲壳虫"乐队专辑中。同时,麦卡尼还在利物浦表演艺术学院(The Liverp··l Institute)上语法学校。在每天乘车上学的途中,有一个看上去比他小一岁的男孩总是在他后一站下车。那个男孩打扮得像个摇滚青年,留着一头"猫王"那样的发型,引起了麦卡尼的注意。麦卡尼觉得自己作为"学长"不应该主动上去搭话。直到有一天,两人坐到了一块儿,那个男孩主动介绍了自己。他名叫乔治·哈里森,吉他弹得不错。此后,麦卡尼经常和哈里森聚在一起即兴弹奏。1958年,在麦卡尼的强烈推荐下,列侬终于同意让十四岁的哈里森加入乐队。
就这样,"石矿男孩"乐队再也不是从前那支默默无闻、只会慌乱地即兴演唱的高中生乐队。他们具备了技艺高超的领衔吉他手、拥有了自己的原创歌曲、每次演出前更必是精心准备;并且,他们的音乐梦想也变得更加远大。
1958年的夏季,列侬的母亲不幸丧生车祸。肇事者是一个警察,事故发生时并不当班。于是,列侬和麦卡尼一样,变成了没有母亲的男孩。麦卡尼私下告诉我:"这是我们之间一条坚固的纽带。"两人虽交情深厚,却表现得一点都不热乎。保罗解释道:"我们是北部的男孩,不会整天把什么心中的感觉挂在嘴边,更不会特意坐下来互相吹捧。我们只是心照不宣。我记得一次我们滑了一整天的雪。晚上回到宾馆,我和约翰被安排在一个房间。林戈(Ring· Star,后来加入乐队的鼓手)和乔治在另一间。我们两听了一首录在磁带里的小样。歌名是"这处,那处,每一处"("Here, There, Everywhere"),是我自己创作的一首曲子。列侬听着听着就顿住了,然后开口问道:"是哪张专辑里的?是《左轮手枪》里的?"他一边脱着滑雪鞋,一边漫不经心地说了句"这个,不错。"就这么简简单单一句话,让我激动万分。这是真正的赞美。"
1960年,乐队开始在一些二流场所演唱,去苏格兰进行了一次短期的旅行,几次将要在德国汉堡举行的演出也都提上了日程。此时,乐队已经正式更名为"甲壳虫",玩笑式地模仿了巴迪·霍利的一只后备乐队的名字:"蟋蟀"("The Crickets")。在当时的鼓手彼得·贝斯特(Pete Best)和贝斯手斯图亚特·苏茨里费(Stuart Sutcliffe)的配合下,乐队常常连续排练好几个小时,演奏一些"长得像马拉松"的曲子。他们甚至通过豪饮啤酒和服用安非他明来提神。第二年,乐队重返汉堡。在那,苏茨里费的女友、一名德国的艺术系学生建议队员们统一将头发扎在头前。她还亲自为他们设计了发型。而在利物浦,乐队则主要是在一家名叫"巨穴"的酒吧(Cavern Club)驻唱。1961年的下半年,正是在"巨穴"里,乐队被前来观看表演的布莱恩·爱泼斯坦(Brian Epstein)发现。爱泼斯坦是当地一家唱片行的老板。于是,他成为了乐队的经理人。第二年的六月,"甲壳虫"在百代唱片里秘密录制了一首歌。四个月后,乐队由林戈担任鼓手,正式发行了第一首单曲《爱我》(L·ve Me D·)。歌曲迅速荣登全英排行榜的第17位。来年一月,乐队的第二首单曲面世:《请让我开怀》(Please Please Me),问鼎排行榜第一位。二月,乐队飞往美国,参加了著名的电视节目《爱德·沙利文现场秀》。
麦卡尼在伦敦拥有一处房产,位于圣·约翰·伍德区(St.J·hn"s W··d)一处僻静的道路上。徒步几分钟便可到达院道路上(Abbey R·ad)百代唱片的录音室(麦卡尼所有的时间不是在伦敦就是在苏塞克斯度过)。这处房子购于1964年。那里,麦卡尼与列侬一起写下了许多"甲壳虫"最负盛名的名曲。他自己也独立创作了不少。这幢爱德华式的三层建筑相当的豪华气派。外围十英尺的高墙使得她幽静地独矗于街角。入口则是自动的安全门,麦卡尼通过遥控器控制其开关。周二中午,他回到了这处住所。之前的周末、周一以及银行休假日他都是和碧一起度过的。他和大女儿玛丽约好傍晚见。玛丽是一名摄影师,她将为父亲拍一些照片作为宣传专辑之用。(麦卡尼与前妻琳达还有另外两个子女:史黛拉,一名时尚设计师和詹姆斯,一名音乐家。同时,他还是希瑟的继父。希瑟为琳达与前任丈夫所生。她是一名陶艺师。)
麦卡尼身穿一套深棕色的西装,领带结耷拉着,衬衫领口也松着。他打开宅子大门,将我带进了宽敞的大厅里,墙上挂满了镶嵌在相框里的照片。许多都是麦卡尼自己拍下的。其中一张是一个印度的建筑工人正在马路边施工,穿着怪异,满身泥泞。大厅桌子上的花瓶里插着满满一捧鲜花,而在客厅一旁的厨房里,园艺师正不亦乐乎地修剪更多花朵的茎叶。(花瓶里的鲜花每周一换。)他的管家玛丽亚在炉边忙活。保罗亲切地与他们打过招呼,径直把我领进位于房子后部的一间大客厅。客厅装饰得堪称完美:方形的木制咖啡桌、舒适高贵的沙发、几张座椅和一个书架。墙上挂着一些现代艺术作品:菲利普·喀斯特的帆布画(注:Philip Gust·n:美国著名招贴画画家。)、另一幅德库宁的作品(他办公室里还有一幅),还有一幅麦卡尼自己画的表现主义风格的油画。画面上是一头公牛。他颇为自豪地指出自己是如何灵巧地徒手画出牛角那蜿蜒错综的线条。房间的一端有两扇法式抽拉门,恰好面对着沐浴在阳光里的花园。一条弯曲的小径直通一处小小的圆顶屋。麦卡尼在六十年代就盖了这个屋子。那是他思考冥想的小天地。
客厅的一角端坐着一架色泽光亮的钢琴。上面镶着乳黄色象牙制成的键盘。"这是我父亲的钢琴",麦卡尼介绍着钢琴的来历,"无巧不成书。它居然是由布莱恩·爱泼斯坦的父亲--哈里·爱泼斯坦那购得。买的时候,我们谁都没听过爱泼斯坦家族,只知道他们在利物浦有个铺子,卖些音乐器材。店名叫"北端音乐商店"(The N·rth End Musical St·res)。英文缩写为"NEMS",也就是布莱恩公司的名字。"甲壳虫"乐队曾一度和NEMS签约。我父亲买这架琴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呢。"麦卡尼说着就把身子倾到键盘上,随手拨了一串琵音,接着《麦当娜女士》(一首英国的爵士乐)的开头旋律便从他的指间流淌开来。几个小节之后,他停了下来,身体站直,说道:"以前这里放的是一架施坦威(Steinway)小型钢琴。我所创作的大部分"披头士"音乐都是在那架琴上面写出来的。它现在放在我乡下的房子里。"他接着补充《院道路》("Abbey R·ad")就是他和列侬在这个屋子里写出来的。
麦卡尼慢慢走向了书橱,里面有两张他的全家照。照片里,他和弟弟麦克还都只是小男孩。他取出一本精装版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gress"),随手翻着,说:"这是迪尔姨妈给我的。"果然,书上写着"给保罗,1953"的字样。"但是我一点也不喜欢这本书,"他把书放回了书架:"我喜欢的只是它是迪尔姨妈送给我的。她盼望我会成为一个正直有用的人。"说完,他转身走向厨房,用轻快的语调唱着:"玛丽亚,我看见一个女孩名叫玛丽亚。"他让她送一些茶来,要加上豆奶。没过一会儿,她就端着一个银盘走了进来,上面放着茶壶和杯子。她请示:"要我沏好吗?"
麦卡尼诙谐地用一口"受宠若惊"的语气回答道:"我们自己来。"
十六岁那年,麦卡尼在他父亲的钢琴上写了首曲子,名叫《遥想六十四》。回想起来,他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我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写下一首叫《遥想六十四》的曲子呢?"几年下来,曲子听来欢快如昨。只是一直没有谱上歌词。他说:"它就仿佛是个音乐陷阱。其间,我和列侬变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而这个曲子几乎也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经典笑谈。约翰经常故作询问说:"你老在钢琴上弹的那个曲子怎么样了?你应该把它用起来。""最终,麦卡尼在二十多岁时填了词,并最终将这首歌收录到了《库珀中士》那张专辑里。对此,他评价道:"二十几岁时再填词是对的,比十六岁一开始写的歌词肯定要好多了。后来写的那个版本看上去更玩世不恭。却也因此显得分外有深度,表达出了某种观点,而且还特别简洁。我前阵子刚刚重新听了听。"他说完大笑起来:"事实上,我最近老是在听它。我自己也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另外一首约翰时常向我提起的歌是《米歇尔》。"这是专辑《橡胶灵魂》("Rubber S·ul")里的一首情歌,歌词里面有几句是法语。这首歌的旋律一直可以追溯到"甲壳虫"们最早相聚的日子。当时,列侬刚刚进入利物浦艺术学院(Liverp··l C·llege ·f Art)进修。他邀请麦卡尼和哈里森参加他的班级晚会。回顾起那段时光,麦卡尼忍俊不禁:"我们总是会穿上黑色的套头毛衣,觉得那样会看上去成熟稳重一些。因为在场的女孩都比我们大。每每在这样的场合,我就抱着吉他静坐在角落里,觉得这样看上去会更有趣些,像个"法国人"。"于是,麦卡尼就在那样的角落里弹着《米歇尔》的调子,时不时装腔来几句法语词。"去年,约翰问我:"你那首法语歌怎么样啦?调子很不错。""列侬的朋友伊凡·沃翰的妻子曾在法国留学。"于是我就去拜访她,让她帮我想写法语歌词,填到《米歇尔》的曲子里去。"她教我说"belle"(法语单词,意味美丽),我于是回应到:"好,等一会。"我用吉他试了试"ma belle"(我的美丽的人儿),感觉很不错。
随着乐队日益成熟,麦卡尼与列侬直接共同创作的机会有所减少。但两人还是时常交换各自的想法。1965年,麦卡尼不经意间读了一本名叫《日常信件》(Daily Mail)的书,很受启发。他不太记得作者的姓名,只说可能是马丁·艾米斯(注:Martin Amis:著名作家金斯利·艾米斯之子,是当代英国作家中最有影响的小说家和文体家之一。)。之后,他开始着手写《书信诗人》("Paperback Writer")。他把这首歌想象成一个渴望成为作家的人写给出版商的恳求信。某天,他来到列侬位于市郊韦桥郡(Weybridge)的家中,高兴地宣布:"看!我想出了个新主意,是一封信。"列侬疑惑不解:"什么?"于是麦卡尼兴奋地回道:"很妙的新东西,你听听"亲爱的先生或女士……"他就这样不停地读完了整首歌词。"列侬给出的回答是:"很好,就这样。"当麦卡尼说:"我们可以再改改……"时,列侬抢过话头:"不用,就那样。"
《昨天》("Yesterday")的曲调则来自同年里麦卡尼的一个梦。他将还没有全部完成的曲子拿给列侬看。里面胡乱填了些乱七八糟的词作为占位符:"炒鸡蛋,宝贝,没你的大腿好看。"之后的几天,当两人努力为曲子写词时,这句歌词一直被挂在嘴边成了笑柄。最终,在一次与当时的女友简·阿什乘坐汽车从里斯本前往葡萄牙南部的三个小时旅途中,他写出了歌词。麦卡尼想了想说:"对于一个小孩而言,那些歌词有些成熟了。很有点阴暗的色彩。但是被唱出来时却感觉好一些。不过,以心理学来分析的话,我现在时常恍惚歌词里那几句"为何她要离开/我不明白/她也不愿告白/怕是我曾失言/我怀念从前"会不会是我在怀念母亲呢?"
1961年,乐队的贝斯手斯图亚特·苏茨里费意外离队出走。情急之下,麦卡尼顶上。结果就和写歌一样,他的表现震惊四座。麦卡尼对我讲到:"我想我只不过是赶鸭子上架了,总得有人来专门干这个。于是我们就找到了詹姆斯·加迈森,一名底特律的贝斯手。他的贝斯弹得精采绝伦。"然而,麦卡尼并没有完全放弃贝斯。他以其独有的天份创新地用贝斯弹出对位法(把两个或多个旋律合成使其具有和谐的关系又保持各自的线条的一种方法)音调,穿插于乐队的歌曲中。其高超的技艺和新颖的匠心至今令人叹服。在1980年的一次采访中,列侬说道:"保罗是所有贝斯手中最具创意者之一。"此外,麦卡尼的嗓音也独具才能,可以适应任何风格的歌曲。在演唱《爱情买不来》("Can"t Buy Me L·ve")时,他仿佛"猫王"第二,醇厚的高音令人心醉;而演绎起《失落心情》("I"m D·wn")时,他则神似小理查德。对此,麦卡尼自己无比庆幸:"我很幸运可以拥有一副好嗓子。我自己都不明白它怎么能如此美妙。"
从1963年到1965年底,"甲壳虫"乐队共录制了六张专辑:《请让我开怀》("Please Please Me")、《"甲壳虫"伴我行》("With the Beatles")、《辛劳之夜》("A Hard Day"s Night")、《"甲壳虫"大碟》("Beatles" f·r Sale)、《救命》("Help")、以及《橡胶灵魂》("Rubber S·ul")。他们定期在各地巡演,还分别在《救命》和《辛劳之夜》两部影片中作了明星客串。如此高量的产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唱片录制体系。麦卡尼至今对此印象深刻:"那时,我们只是简单地从成年人大哥--乔治·马丁以及制作人那儿接到召唤。安排好一切后他们会通知说:"我们需要很多歌。你们明天上午十点准时到。半个小时喝茶、准备,十点半开工到一点半。然后休息一个小时,两点半复工,五点半结束。"我们在上半段能录完两首,下午又是两首,现在想想真不敢相信。通常,乔治和林戈甚至都不知道要录什么。约翰和我于是就示范给他们看。"说着说着,他就随口唱起了《橡胶灵魂》的那首《女孩》("Girl")。在这首歌里,每唱完一小节,列侬都会重复唱到"女孩,女孩",中间会加进一声蔑视的唏嘘。"这时,列侬会告诉大家他希望中间能表现出倒吸一口冷气的声音。大家很快就这个想法达成共识。很明显,乔治和林戈总是能第一时间心领神会,默契十足地说:"耶,耶",从来没有类似"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的话。等林戈用打鼓棒敲了几下节拍,我们立刻各就各位,音乐响起。
"在如此高效率的工作方式下,我们五点半就可以结束。晚上的时间便可归自己自由支配,享受一下文明的雅趣。生活在国际大都市伦敦,我可以去伦敦国家电影院(Nati·nal Film Theatre)观赏科林·布莱克里(注:C·lin Blakely:英国著名男演员,曾出演多部侦探电影。)在《裘诺与孔雀》里的表演("Jun· and the Payc·ck")(英国戏剧家Sean ·"Casey 的一部舞台剧,希区柯克后来将之拍摄为同名电影)、去看看电影《远离尘嚣》(根据英国著名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的同名作品改编的电影)、去博物馆里徜徉一番或者去参加某个高级宴会。于是,第二天早晨录音前的茶点时间里,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兴致勃勃地交流一番。"
新专辑里有首欢快的轻摇滚,名叫《那就是我》("That Was Me"),麦卡尼将它诠释得淋漓尽致。彻底展现出多年以后,他的嗓音完美依旧,音域惊人。歌词里有几句听起来很琅琅上口,描写了他作为一名"披头士"的生活:"那就是我/蜘蛛网里/地下室里/汗流浃背的我/一纸合约/上了电视/那就是我。"我告诉他这些歌词仿佛是对往昔生活打出的一个惊叹号。
"就是这个意思,我自己确实很惊讶。当我回顾过去时,我不由自主地感到过去的一切是在令人称奇。这种感觉无法控制。伟大的"甲壳虫"只拥有她宠爱的四名成员,而我竟是其中之一;无可比拟的列侬/麦卡尼这对黄金组合里,我跻身一半;身兼此二职足以人生无憾。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写出了《昨天》,那就是我。只有一个人写出了《让它去》("Let It Be")、写出了《山顶的傻瓜》("F··l ·n the Hill")和《麦当娜女士》,而那个人仍然是我。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成就出一个奇特而辉煌的人生。所以,能有幸参与到这所有的其中实在让人大出所料。你得掐痛自己才能确信这一切真的存在。《那就是我》所想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心情。"
但是,麦卡尼也承认,"甲壳虫"的大名有时也是一种负担:"就仿佛你做一切的事情都是在某个影子的笼罩下。很显然,"甲壳虫"绝对是个巨大的影子。结果就是,每当现在我写了首歌,总感觉其中的某种成分会将作品自动否决。但是再想想,又觉得这歌不错。"话虽如此,新专辑里还是收录了一些新作,比如《最后的尽头》("The End ·f the End")。这首作品令他本人颇为满意,以致每次听的时候他都会忍不住叫到:"妈的,真是好听!"。特别是其中几行反复吟唱的歌词,让他偏爱有加:
当某天我终于死去;
愿闻你们笑着打趣;
那古老的云烟;
变成地毯,昨日重现;
孩子们踩踏,嘻笑玩乐;
然后又仰躺,静静倾听;
那旧时的故事,那不老的往昔。
他继续解释说:"虽然喜欢这首歌,但我确实认为有些东西在经过时间的洗礼后会永远沉淀。就好像无论你做了什么,总有些记忆会尘封于脑海。一次,有人问迪伦:"你会不会写出另一首《铃鼓先生》("Tamb·urine Man")? 迪伦答得好:"不能--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我觉得这句话里蕴藏着真理:你确实回不去了。我再也不可能像从前一样痴迷于什么书信诗人,因为我只能是个年轻的作家。年岁流逝,"诗人"再也回不来了。"
我和麦卡尼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摄政公园(Regent"s Park),毗邻他在伦敦的寓所。他将地点约在公园西头的一处咖啡厅里,旁边就是游人划船的小湖。我早到了几分钟,只见窗外黑蒙蒙的天空,仿佛要下雨。公园里没有游客,稍显寂寥。然后,我瞧见麦卡尼从远处缓缓走近。他身穿咖啡色西服,天蓝色衬衫。突然,他停住脚步,凝视着空荡荡的游乐场。他抬头看见我,挥了挥手,邀我坐到了咖啡厅的露天小院里。此情此景,回想当年"甲壳虫"的解散再合适不过了。矛盾最先的争端始于1968年。当时,乐队刚完成了专辑《甲壳虫》("The Beatles"),或又叫作《白色专辑》("The White Album")。列侬与日本女艺术家小野洋子(Y·k· ·n·)坠入爱河,乐队成员间就各种商业决策争议不断。1969年,列侬说服了除麦卡尼以外的另外两名乐队成员,聘请脾气暴躁、口吻生硬的美国人艾伦·克兰(Allen Klein)为乐队经理人(前经理人布莱恩·爱泼斯坦已于1967年去世);而麦卡尼则主张由他的岳父、出色的律师李·伊斯特曼出任这一职务。其他成员疑心这会让麦卡尼在乐队内享有某种特权进而控制整个团队,因而坚决反对。其他三人与克兰签订合约,麦卡尼选择独自单飞。同年,克兰与百代唱片重新进行了谈判,最终敲定从该年直到1976年期间,乐队每年发行两张专辑。克兰还将成员们的版税收入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价:1969年到1972年间,从原先每张唱片的39美分涨到58美分,而从1973年开始到1976年,这一数字还会提高到72美分。
1969年一月,乐队开始拍摄一部名为《让它去》的影片。这部与专辑同名的纪录片原本是想展现四人如何快乐地录制新唱片,最终却表现了乐队的四分五裂。人们所见的是哈里森阴冷痛楚的面庞,是斯塔郁闷冷漠的愁苦;而团队的领袖列侬,除了一直坚定支持他的小野洋子,几乎与世隔绝,不闻不问;麦卡尼则一直竭力挽救,不停地鼓舞士气、团结人心,到头来却只是一场徒劳。
说到小野洋子,我插了句:"那时候列侬不顾大家反对,将小野洋子带到录音室,片刻不离。究竟是谁的错,谁也说不清--你分不清到底是列侬执意带着她,还是当她明显感觉到自己不受欢迎时却还是不肯离开。"对此,麦卡尼却很宽容:"我们谁都不要责怪。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就像大桥下面的潺潺流水,没必要抓着不放。当时,他们是情侣。这个理由,超越一切。"根据当时的报道,列侬在那段时间里吸上了毒品可卡因,这也一度使得他与麦卡尼之间的沟通变得更不可能。我询问麦卡尼列侬当时的毒瘾到了什么程度,他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吸毒的事,他从没和我说过。"之后,他又补充了一句,"我根本不能忍受去看《让它去》。"
1969年底,乐队的纠纷终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甲壳虫"解散。(而正式的对外宣布则是几个月之后的事了。)那段时间里,麦卡尼感觉自己几近崩溃:"最令人心痛的倒还不是离开乐队,而是在何种情形下离开。事实上,我不得不起诉他们,别无他法。我原本是想起诉艾伦·克兰,只要他离开,一切就会平息。但问题是,他和整件事并没有直接关联。律师们告诉我唯一能够起诉的只有乐队其他成员。我告诉他们:"不行,我办不到。"于是这就把我困在了--也不算是绝望--某种两难抉择之中。那是一段异常艰难的时期。无论到哪开会,我都是一对三。更难过的是他们还都是你的朋友。"
"到今天,仍然会有人说:"那个人把朋友告上了法庭。"那语气仿佛我很高兴这样做,仿佛这一切都很轻松似的。"
突然,一位妇女站在了我们旁边,两个小男孩则在不远处等着。她礼貌地询问:"打扰了。能不能请您和我的儿子拍张合照?"麦卡尼显然很不喜欢自己的谈话被打断,客气地回答她:"很抱歉,恐怕不行。我可以和您握手,但不合影。"
"我是想把照片寄给父母……"
"我知道,亲爱的。你,还有每一个前来的人,都这么说。那也就是为什么我拒绝合影。我希望您不会介意,认为我很傲慢。"
"不会。"她说。
"但是我确实觉得您的两个孩子看上去可爱极了。"
那位妇女最终带着孩子走开了。麦卡尼开始抱怨道:"这年头,人手一个照相机,连手机都能拍照。今天早上,我刚被两个街头摄像师撞到,后来又有两个歌迷要来合影。我真的厌烦了和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一张一张地拍照,特别是正当我享受私人时间的片刻。"
我又把话题转回了"甲壳虫"乐队的解散。他继续说道:"那真是一段地狱般的日子,我差点被击垮。被告的人是我的朋友们,我自己也根本无心工作。白天里,我日日买醉,欺骗自己是在参加"派对",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琳达是我唯一的救星,真正的大救星。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勇敢地面对,也帮助我勇敢起来。"我好奇那段时间里他有没有新作品。他想了想,说:"可能有一首,叫《你是意外》("I"m Amazed"),倾诉了我对琳达的需要。那段时间太可怕,就像歌词里说的:我是一个孤独的人/身处的这一切/我无法理解。"1970年,在乐队正式对外宣布解散之后不久,麦卡尼发行了首张个人大碟《麦卡尼》("McCartney"),结果好评如潮,销量不俗。《你是意外》便是专辑中的一首。
1971年3月,漫长的诉讼之后,法庭最终宣判麦卡尼胜诉。一切与乐队相关的商业活动与收入作为涉讼财产被处理,克兰的权力被一律收回。"一切终于都结束了。我们踢走了克兰,多年的友谊即刻恢复。三位朋友们,一个一个地,对我表达了感谢。"到1972年,其他三名乐队成员都已对克兰心生厌恶,拒绝续签任何合同。克兰上告他们单方面终止合约,结果却反而自己又被告上法庭。(官司最后在庭外被私下和解。)
七十年代中期,列侬定居美国。在那,多年未见的两位老友终于重聚。麦卡尼回忆道:"他看上去很清爽,气色很好。我经常去纽约出差,然后和他见上一面。那种旧日情谊重回身边的感觉真是太美好了。"到1980年十二月,列侬被枪杀以前,两人已经恢复了伙伴关系。"对此,我终生感恩。如果我们一直形同陌人,我会非常难过。"
凄冷的细雨还是淅淅沥沥地漂了起来。在他的建议下,我们移回了咖啡厅,坐在一个角落里。我非常急切地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对于麦卡尼而言,六十年代的岁月算不算得上是个奇迹?他很坦白地说道:"这段时光在我脑海里确实是个奇迹,"他的语气并不笃定,"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还记得在《让它去》的开头部分,我写道:"当我发现自己身陷麻烦/圣母玛丽亚降临我身旁。"我感觉自己已经游荡得太久。某天,我做了个梦,梦里母亲来到我身前,说了句:"让它去"。于是这首歌就这么诞生了。所以,事实上,一切并不是都如想象中那么美妙,并不仅仅是一段黄金记忆。"
我注意到,在采访中,麦卡尼提及母亲的次数不亚于提起"甲壳虫"的次数。这让我想起了五天前,在他的MPL公司里,采访第一天他说过的某些话。那天阳光灿烂,微风徐徐,是个可爱的伦敦春季的午后。大概就是同样的天气给了麦卡尼灵感,写出了专辑《左轮手枪》里的那首《晴日阳光》("G··d Day Sunshine")吧。那天,我们聊了这几年里他遭遇到的一系列重大的损失。当时,他是这么说的:"在这一点上,我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十四岁时失去母亲,是我人生中一幕重大的悲剧。但是,纵观过去,我仍然乐观开朗、满怀激情、努力前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很清楚这才是她所希望看到的。同样,这也是琳达、约翰、乔治和我父亲,他们大家的希望。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积极向上的人。想到自己的离去会把我推向无穷苦痛和一蹶不振,他们一定会担心忧愁。我想通了这个道理,它帮助我远离消极、不至堕落。"说这些话时,他的目光移向了窗外的苏豪广场。看着那灿烂的阳光点亮片片新叶,他说:"每当阳光像今天这样光彩照耀,我心中就会充满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