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九月,在去俄罗斯之前准备路上要看的书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两本书,一本是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另一本是有清楚的莫斯科城区图的《俄罗斯地图册》。布尔加科夫生前最大的愿望是创作一部不朽的作品。他在寂寞的、贫困潦倒的生活压力下,花了十二年时间,呕心沥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写出了与三四十年代苏联文学环境格格不入的《大师和玛格丽特》。他生前知道,这部长篇小说会像他别的很多作品一样,一时不能得到出版;但是他却没有想到,它得在黑暗的抽屉里等待四分之一个世纪,才有机会与他祖国的读者见面,而且首次见面还得以删节本的形式;完整的版本则还要再艰难地等待五年,直到一九七三年才得以问世。不过,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他坚信这将是一部辉煌的(“辉煌”是他最喜欢用的一个词)不朽之作,就像小说中那个创作了关于本丢•彼拉多(注:本丢·彼拉多(?-36年),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执政官。根据新约圣经所述,耶稣基督在他的任内被判钉十字架)的历史小说的主人公相信自己就是“大师”一样。历史也确实是最为公正的审判官,许多曾经喧闹一时的文学垃圾早已被世人丢弃,而《大师和玛格丽特》无可估量的价值则让世人再也无法回避,布尔加科夫也当仁不让,进入了由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文学大师组成的不朽者行列。
对《大师和玛格丽特》,我从前至少读过两遍。此次去俄罗斯,我随身带上它,最大的心愿就是一边重读这部作品,一边能够有机会到小说人物活动过的一些地方去亲身感受一番。比如,位于莫斯科德库林花园大街附近的牧首塘公园和杂耍剧院。前者,是小说开篇出现的第一个场景,在那里,正当“莫文联”理事会主席柏辽兹滔滔不绝地向诗人“无家汉”伊万(一个贯串整个小说的人物)灌输无神论思想,引经据典地讲解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耶稣的时候,魔王沃兰德出场了;而在小说结束的时候,每逢春天月圆的黄昏时分,已经放弃写诗、转而搞起哲学历史研究的伊万,就会回到那里,坐在当初他、柏辽兹和沃兰德一起坐过的长椅上,一边仰望明月中龙马似的黑影,一边陷入回忆和沉思。后者,距离牧首塘公园不算很远,是魔王沃兰德和他的随从通过表演魔术,观察进入二十世纪的莫斯科居民内心是否发生了变化的场所。再比如著名的阿尔巴特大街。小说中的“大师”就是在那里的一条小胡同租了一套半地下室,默默地创作了他的 “本丢•彼拉多”历史小说,他和玛格丽特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也主要是在那里上演的。那条大街的某个胡同里,还有玛格丽特曾经住过的漂亮的带花园和哥特式塔楼的小洋房——原型奥斯多冉卡21号,也应该去瞧瞧;在小说第二部开始的地方,作者甚至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跳出来直接告诉读者:“那地方美极了,”“谁要是想去,请对我说一声,我可以告诉他地址和去的路线—那所小楼至今还完好无损呢。”此外还有麻雀山—苏联时期,曾一度改名为列宁山,那是魔王和他的随从、“大师”和玛格丽特最后告别莫斯科的地方;当然,不能忘了新圣女公墓,那是布尔加科夫最后安息的地方,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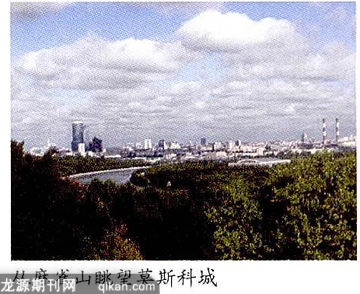
由于随团的行程安排,我对布尔加科夫及其小说人物活动场所的寻访,并不能按照小说里的顺序和个人意愿去进行。甚至,在莫斯科的几天里,从头至尾都没有机会到牧首塘公园或花园大街一带去看一眼。真正与布尔加科夫及其小说人物有关的寻访,是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九月十一日开始的。
那天上午,差不多十一点钟,我随团来到位于莫斯科西南侧的麻雀山观景台。麻雀山高出莫斯科河六七十米,观景台后面是著名的莫斯科大学主楼;当年毛泽东就是在那里接见留苏学生时,说了那句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站在观景台上,可以隔着丛密的树林眺望蜿蜒似裙带的莫斯科河,及河对岸辽阔的莫斯科市区。在临近中午的明净阳光下,许多高楼大厦和笔直耸立的尖塔熠熠生辉;虽然隔着相当的距离,却也仿佛能听到空气中回响着的市政建设此起彼伏的轰鸣声,和繁华大街上的喧闹噪声。在《大师和玛格丽特》走向尾声的辉煌章节里,“大师”和玛格丽特骑着能够飞翔的神驹在此降落,与即将告别莫斯科的沃兰德及其侍从汇合。那时,天色已近黄昏,莫斯科城刚刚经历了一场大雷雨的洗礼,天空里悬着一道七色的彩虹。“大师”曳着拖地的黑斗篷,来到断崖前。他就要永远告别这座给过他爱情和痛苦的人间城市了,一股强烈的惆怅从他心底油然升起。他时而举目远望,时而又俯首沉思,好像既要把夕辉笼罩下的整个城区尽收眼底,又要穷尽脚下那横遭践踏的芳草的奥秘。为了配合他依依惜别的心情,在小说里扮演重要角色的黑猫河马和绰号巴松管的唱诗班指挥卡罗维夫各显其能,一前一后发出一声长啸,仿佛用带响的画笔在空中画出一道“从此一去不复还”的诀别之音。夜幕徐徐降临,他们一行五人骑着骏马冲向神秘的夜空,在他们身后,莫斯科城不见了,只剩下一片茫茫的烟雾。
据说在莫斯科市区有七座高地,克里姆林宫所在的地方是其中之一,麻雀山也是其中之一。在历史上,拜占庭帝国于十五世纪中叶覆灭后,沙皇伊凡三世不仅娶了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为妻,还把拜占庭帝国的徽章双头鹰接过来,当作俄罗斯自己的国徽。从此,无论是在外人、还是在俄罗斯人自己眼中,俄罗斯都成了拜占庭帝国衣钵真正的继承人;而都城莫斯科更是把自己视为“第三罗马”,就像君士坦丁堡是“第二罗马”一样。罗马帝国的都城最初是在七座山丘上建造起来的,这一历史使得俄罗斯人不仅把“七”当作自己的吉祥数字,而且在莫斯科也找出七座山丘高地,处处以罗马为样板。这样,俯临莫斯科河的麻雀山自然首当其冲,成了他们的必选。所以,当我站在麻雀山观景台,一边回想《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相关篇章,一边联想起这些历史沉积和传说;布尔加科夫让他小说的主要人物选择这里作为退场之前的聚集地点,仿佛在有意无意中具有了某种穿越历史的蕴涵。

午餐之后,我们一行人来到因为安葬着众多俄罗斯名人而闻名的新圣女公墓。这座公墓背靠新处女修道院,并因这座修道院而得名。以前,从一些布尔加科夫的中文译者写的文章里,我知道这位大师的墓地就在这里。而且,我约略知道,他的墓地非常简朴,既没有占很大面积,也没有高大奢华的大理石或花岗岩墓碑。因为事先并不了解他的墓地的具体位置,我便抱着希望问我们的临时导游。让我深感遗憾的是,这个中国山东籍的留俄研究生居然不知道这位前苏联作家是谁,更别提知道他的墓的位置了。这个导游介绍说,这座公墓里安葬的主要是俄罗斯近现代史上的一些政要名人,战斗英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当中比较著名的有经典作家果戈理和契诃夫的墓地,有红色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和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墓地。我心头袭过一阵无奈。但是我到布尔加科夫墓前默立片刻的心愿丝毫没有减弱。所以,当导游领着我们来到叶利钦的墓前时,我根本没有心情听他讲解与叶利钦墓有关的趣闻,前俄罗斯总统墓地鲜花簇拥的华丽设置和排场,也丝毫勾不起我的钦羡和好奇;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找到布尔加科夫朴实无华的墓地。于是,在跟着导游瞻仰了我很喜欢的、当然也是布尔加科夫敬仰的果戈理的墓,瞻仰了与果戈理墓只有一条石板小路相隔的契诃夫墓,又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碑式的墓瞥了一眼之后,我便离开大队,独自在一排排墓地中间匆匆地寻觅起来。凡是那些有高大墓碑或精美雕塑的墓地,我都无心留步,即便那下面安葬的可能是某个让世人敬仰的大人物;我知道这些奢华的世俗物质跟布尔加科夫的安息之所是无关的。我只留心察看那些朴素的、没有什么装饰的墓冢,并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布尔加科夫的不朽灵魂,让我这个在生命里永远不能见到他、但真挚地热爱他的作品的卑微人物,能够找到他的墓地,能够在他的墓前伫立片刻,致以个人的敬慕。我觉得,在他的墓石上,至少会刻着一个半身的头像,打着蝴蝶领结,眉头紧锁,双唇紧闭,右眼上可能戴着单片眼镜,睿智的眼神里含着严肃的深邃。凭着这种猜想和对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俄文字母拼写的粗略记忆,我匆匆寻找了半个多小时,一直到预定离开公墓的时间到了,也未能瞥见他的墓地的踪影。在走出公墓大门的时候,我只好在心里祈愿:大师啊,以后若有机会再来,我一定预先打听清楚您的墓地的方位,带着你的书,带着一束鲜花,来向您致敬。

下午快五点钟的时候,我们一行人来到在莫斯科要参观的最后一站,洋溢着艺术与休闲气息的阿尔巴特大街。苏联时期,有许多著名诗人、作家和艺术家都曾在这条大街上住过。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布尔加科夫也毫不例外地把写作“本丢•彼拉多”的“大师”安置在这条大街上某个胡同的一套僻静的半地下室里。写作进展顺利的时候,“大师”就走出他的离群索居的居所,去周围的大街小巷散散步,或是到附近的某家餐馆去就餐。整整一个冬季,“大师”都在全力以赴地写作;随着春季来临,他的住所外面的丁香花丛开始披上绿装,散发出奇妙的芳香,他的“本丢•彼拉多”故事也在迅速接近尾声。某一天,他穿过阿尔巴特广场,蹓跶到了特维尔大街;在那里的一个胡同口,他终于邂逅了他生命中的女神――穿着黑色春大衣、手里捧着一束黄花的玛格丽特。爱神在他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一下子就闯入了他的灵魂;用他自述的话,就是:“如同走在偏僻小巷时平地冒出来个杀人凶手似的,爱神遽然来到我们面前,它的利箭当即穿透了我们两人的心!”之后,在爱情的滋润下,“大师”信心百倍地继续他的小说创作;而愉快地反复阅读他的作品的玛格丽特,不仅赠给他“大师”的称号,还充满爱意地为他缝制了一顶黑色小圆帽,用黄线醒目地绣着俄语“大师”的首个字母“M”。到了八月份,关于本丢•彼拉多的小说完成了。随着“大师”与玛格丽特捧着这部小说回到现实生活,他们幸福的、不问世事的生活也很快一去不复返了。现实社会不仅不接受“大师”的作品,而且形形色色的耍大棒的批判文章很快纷至沓来,对他形成无情的围攻。绝望的“大师”最后竟逃遁到一家精神病医院,躲了起来。
那天下午,在蔚蓝的天空下,临近傍晚的夕阳把阿尔巴特大街一侧的楼房映照得犹如水洗过一样,明净发亮。我猜想:“大师”一定曾在类似这样的时刻,在这条街上,贴着有阳光的一侧独自漫步。在走过一家装饰得比较富丽、里面灯火通明的餐馆时,我又想,他兴许曾到这里某个靠窗的餐桌旁吃过晚餐吧。因为不会讲俄语,我没有找到玛格丽特曾经住过的小楼房的原型,奥斯多冉卡21号。但是在一个胡同口,我看到一尊铜像;他高高的额头,长长的身影浅浅地烙印在铺石地面上,双手插在裤兜里,右胳膊夹着一卷文稿。看到他的时候,我首先联想到《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诗人“无家汉”伊万,随即又联想到了“大师”。我不知道这尊铜像是不是跟他们中的哪一个有关系;也许它只是某个在阿尔巴特大街住过的普通文人的塑像,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想到的他们。诗人伊万在被魔王沃兰德有关“莫文联”理事会主席柏辽兹的死亡方式的精确预言深深震撼之后,乘着夜幕,曾经在阿尔巴特大街一带的神秘胡同里悄悄穿行;而“大师”或许就是从这尊铜像所在的胡同里面的某个半地下室走出来,到阿尔巴特大街上消磨一天成功写作之后的时光的。也许我在这尊铜像前产生的这些思绪,只是毫无根据的、可笑的胡思乱想。但是我并不在乎什么现实或根据,我不想让它们束缚住我的想象;我希望藉着这种浮想联翩,稍微弥补一下在新圣女公墓未能找到布尔加科夫墓地所留下的遗憾。
告别了阿尔巴特大街,我在莫斯科对布尔加科夫及其小说人物有关的寻访,似乎也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然而,命运的安排,自古以来都不是凡尘之人所能预料的。
九月十二日一早,我随团乘飞机离开莫斯科,到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多瑙河上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晚上六点多钟,导游把我们带到位于佩斯区(注:布达佩斯是由多瑙河两边的两个城区组成的,一边是布达区,另一边是佩斯区。)的著名的瓦茨步行街。正是日光迅速消退、暮色如潮水般笼罩街道的时候。瓦茨街上的路灯不多;街道两旁的各种店铺里散射出朦胧的亮光,让整个街道洋溢着刚刚滑入黄昏的懒洋洋的绛紫色;行人就像在光影昏蒙的水底浮游的鱼儿,似乎也都放慢了脚步,享受着夜生活来临之前的宁静。我漫无目的地在这条街上转了一圈,最后走进了一家书店。里面除了两三个店员,几乎没有顾客。我走到标着Fiction字样的书架前,想看看作者名字由R打头的书中有没有拉什迪(注:萨尔曼·拉什迪于1948年在印度出生,后在英国长大,现居住在纽约。起代表作有《午夜的孩子》、《撒旦诗篇》、《摩尔人最后的叹息》)的新书,或是有没有名字由O打头的Ovide的《女英雄书简》。但是,还没有看几眼,一位年轻店员走过来告诉我,他们打烊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只好不情愿地转身,准备离开。这时,布尔加科夫突然又闯入我的意识。我用不太准确的英语问店员,是否有英文版的布尔加科夫的作品,比如《大师和玛格丽特》。那位年轻的男店员似乎没有听懂我的话,他对着站在收银台后面的年轻女店员咕咕噜噜地说了些什么。我又连忙对他们补充说,布尔加科夫是俄罗斯的、苏联时期的著名作家,《大师和玛格丽特》是一部非常有名的长篇小说。那位漂亮的女店员好像沉思了一下,然后用匈牙利语对男店员说了几句话。于是,一本英国兰登书屋版的英译《大师和玛格丽特》拿到了我面前。我如获至宝地赶紧付了3190福林(注:福林是匈牙利的货币名,1元人民币大约可以换25福林。),买了一本。在我走出书店大门的瞬间,女店员和她的同伴也迅速关掉了店里的几盏灯,准备下班了。

在莫斯科的时候,我曾经在火车站、宾馆附近的书店去看过,希望能找到一本英语版的《大师和玛格丽特》,但是那些书店只有一两种装帧很一般的俄语原版的,而我对俄语又完全一窍不通。现在,居然在布达佩斯的一家书店买到了兰登版的英译本,我内心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回想起买书过程中的细节,就更是让我不由得浮想联翩了。想想看,在一个说匈牙利语的国家,买一本从俄语翻译成英语的非匈牙利作家的作品,其中难以言表的巧合不能不让我惊叹。何况,当时正是书店就要关门的时候。我至今还保存着那家书店给的收银条,上面显示着收款时间—19:01,还有书店门牌号――瓦茨街22号。当然,尤其让我感激的是那位年轻的女店员。联想当时的情景,我禁不住把她和小说中的玛格丽特联系起来。也许她就是玛格丽特的化身;或者,就像小说中魔王沃兰德的侍从所说,玛格丽特是十六世纪法国纳瓦尔王后玛戈的后裔,这个店员的身上很可能也流着这个古老王族的血液,而且她的名字很可能就叫玛戈、玛丽或玛格丽特。或许,正是由于我在新处女公墓没能找到布尔加科夫的墓地,大师的在天之灵就在瓦茨街这家书店即将打烊的时刻,通过这个说匈牙利语、却知道甚至读过《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姑娘,以这种看似不足为奇的方式,赐给我一些幸福的安慰。
不过,让人惊喜、欣慰的事情并不到此为止。数日之后,九月十七日,在我从莫斯科转机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去拜访了作家莫言先生。莫言大约一周前刚从俄罗斯回来,他是随中国作家出访团到俄罗斯参加“中国文化年”活动的。在他家里,我们自然讲起了在俄罗斯的观感。当我谈到在新处女公墓留下的遗憾时,莫言告诉我,他们也去了那里,而且瞻仰了布尔加科夫的墓地,因为带他们去的俄罗斯作协的人知道墓地的位置。然后,莫言又拿出他的数码相机,让我看他拍的布尔加科夫墓地照片。就这样,在一个数码化的世界,我与念念不忘的布尔加科夫墓地相遇了。
照片一共三张,非常清晰。在满怀惊喜地端详着照片的同时,我不由得为布尔加科夫墓地格外的朴素所震撼。那不是我所想象中的一般的朴素,而是简陋得令人难以置信。那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长方形土墓。墓地里种植着几行叫不上名字的、低矮的花草,还落了许多无花果。一块粗砺、浑拙的青色墓石浅浅地埋在墓土中,上面只是简单地刻着布尔加科夫和陪伴他走过生命最后十年的第三任妻子——叶莲娜•谢尔盖耶芙娜•布尔加科娃――两人的名字与生卒年份,根本没有我想象中的布尔加科夫头像。墓石的左前边,一个咖啡色的透明塑料瓶里插着两株百合,很明显是仰慕他的无名读者敬献的;墓石的右后侧,种着几棵紫菊和水仙。这就是一代文学大师最后的安息之地,即使与公墓里的那些最普通的墓冢相比,它也是过于简陋的,更不要说与周围那些用大理石或花岗岩装饰得豪华、气派的墓地相比了。但它是安静的,无比安静的,就像那些躺在花草间的无花果一样安静;只有拂过那些花草和墓石的微风,以及热爱大师作品的读者的敬意,永远陪伴着它。就像《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大师”,在两间简陋的、很不起眼的半地下室里,创作了他的寓意深远、有关本丢•彼拉多的历史小说;躺在这座朴实无华的墓地下面的布尔加科夫,早已在世界读者的心中竖起了一座雄伟的、辉煌的纪念碑。
后来,我又从一些资料中了解到,那块青色墓石背后竟然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布尔加科夫生前最推崇的作家果戈理的遗骸,原来安葬的地方是彼得堡的丹尼尔修道院;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迁至新处女公墓后,在新墓地竖立了一座有果戈理半身塑像的白色大理石纪念碑,原来在丹尼尔修道院的那块墓碑就被废弃了。一九四○年三月十日,布尔加科夫去世,他的妻子叶莲娜•谢尔盖耶芙娜想尽办法,找到那块被废的墓碑,买下来,把它变成了布尔加科夫的墓石。于是,果戈理曾经的墓碑脱胎换骨,成了布尔加科夫安息之地的守护石,仿佛一位前辈大师的不朽之魂永远守护着一个生前历尽磨难的后来者。我想,叶莲娜•谢尔盖耶芙娜一定知道,布尔加科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读果戈理的《死魂灵》了,而且,果戈理和他的作品曾在无数阴沉的、让人无法入眠的夜间,给布尔加科夫带来无穷的慰藉。这真是一位与布尔加科夫的灵魂贴得很近的伟大的俄罗斯女性啊。她就是《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原型;正如玛格丽特对小说中的“大师”始终保有炽热的爱情,对他的小说手稿无比珍爱,叶莲娜•谢尔盖耶芙娜在布尔加科夫穷困、寂寞的最后十年,同样是始终与丈夫相依相伴、患难与共,在他去世后,又以生命珍藏、整理了他的所有作品和手稿。在《大师和玛格丽特》第二部中,布尔加科夫之所以能够创作出那些洋溢着浪漫激情和幻想的爱情篇章,大部分灵感肯定就是来自这位理解他、并深深爱着他的妻子;因为,在叶莲娜•谢尔盖耶芙娜心目中,他就是无冕之王,就是不朽的“大师”。
我知足了。到此,这趟对布尔加科夫及其作品人物活动场所的寻访,也应该算是非常圆满了。而且,布尔加科夫在天之灵所赐的精神慰藉,甚至让我这样的平凡之人感到受宠若惊。但我还是祈愿,在未来岁月中,能够再有机会去寻访,去参观他的博物馆,去他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
2008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