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译/马振骋
文/[法]丹·弗朗克
丹·弗朗克(Dan Franck),1953年生于法国。在巴黎索邦大学攻读社会学,毕业后零星打工若干年,后专心从事文学与历史写作。至今二十多年,已有十几部作品问世。
1980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希腊历朔日》,书名是法语一句俗语,希腊理发中没有朔日,这个奇怪的书名也即是说永远等不到那一天。这部书旋即获得当年的“处女作小说奖”。
弗朗克写作勤奋,自后每隔两三年便发表一部作品,内容不仅是小说,且有关于音乐、绘画,也参加电视剧编剧。主要作品有《告别》(1987)、《疯人陵园》(1989)、《分离》(1991,获勒诺多奖,已译成17国语言,并改编成电影)。还于朋友让·沃特兰合作写有《波罗历险记》从属。
《波希米亚人》(1998)与《自由派作家们》(2004)可以说是姐妹篇。《波希米亚人》写20世纪初,在巴黎蒙马特尔与蒙帕那斯区内艰苦与欢乐的艺术家:阿波利奈尔、毕加索、莫迪利亚尼、苏丁、曼雷……这些艺术史上出类拔萃的人物创造了艺术新语言,使整个20世纪艺坛精彩纷呈,影响直至今日二十一世纪。
《自由派作家们》里的任务崛起于1930年代,他们经历的是史诗时代。在俄罗斯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接着又是斯大林肃反运动和莫斯科审判案,同时又有西班牙内战。人们战斗,不仅是拯救一个民族,而是保卫一种意识形态世界观。欧美各国试图遏止法西斯主义的勇士、工人、知识分子不顾阻挡,跨过比利牛斯山参加国际纵队。马尔罗、卡帕、奥威尔、海明威、毕加索都带着自己的武器——钢笔、画笔、照相机——让这些烧焦的土地绽放艺术的异草奇葩。
丹·弗朗克的叙事中,历史事实与与小说手法交织在一起,这些事迹令人激奋,令人掉泪,今天看来那么不可思议,却又是永远那么真实,并让我们看到什么是艺术家、文学家的真正品质。
一、绮尔达与罗伯特·卡帕
9月5日,在科尔多瓦前线塞罗穆里亚诺附近,一个男人倒下了。他穿件白衬衫,戴顶全国劳工联合会会徽的橄榄帽,一支列贝尔枪,由皮背带系住的腰带上绑了几发子弹。这人叫费特里可·波莱尔·加西亚。他即将成为西班牙内战中最著名的战士。因为,正当他随同他的同志准备跨过一条小沟时,一位摄影师正窥伺着。在他们趴在地上用枪瞄准时,在他们面对敌人的火力正要冲上去时,在他们举枪连续发射往前跑时,那位摄影师的镜头正对着那个无政府主义者和他的同志拍,拍到他面孔上中了一弹,走路踉跄,张开双臂,脸部抽搐,站立不住整个儿倒了下去。
罗伯特·卡帕二十三岁。直到那时,在国际摄影界默默无闻,他刚才拍了一张具有象征意义的照片,不久流传全世界(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
这个青年又给他的徕卡相机装上胶卷,穿过被战士踩踏过的留茬麦地。他跟一个灰绿眼珠的褐发少女汇合,她也斜挎着一个相机。他抓住她的手,奔向一辆共和派的卡车,车子载了他们驶向一个还不知道的目的地。罗伯特·卡帕和绮尔达·波霍里尔斯就是这样,在整个西班牙战争时期随着机缘捕捉镜头。
从7月18日,他们在巴黎走遍各个报馆,两人要求获得委派。《见闻》杂志最后同意派他们跟其他记者一起出发。8月5日,一架飞机把这组人送到了巴塞罗纳。记者就分散到全国各地。在抵达塞罗穆里亚诺以后,卡帕和绮尔达到过加泰罗尼亚全境,然后到了阿拉贡前线跟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在一起。他们回到托莱多,然后又是巴塞罗纳。然后巴黎。一举成名。自由派作家们!33绮尔达与罗伯特。
安德烈·弗里德曼十七岁。那时还不叫罗伯特·卡帕。他跟安德烈·克特斯和其他给现代摄影带来辉煌成就的人一样,也是匈牙利人。他在布达佩斯游行反对霍尔蒂摄政的独裁统治。他被捕。放出来后逃至德国。他在那里必须工作。但他不懂接待国的语言又能做什么呢?去发现一个不需要使用语言的工具。为什么不是摄影呢?
他就试了起来。有人借给他一台伏格脱兰德6×9相机,他用来拍出第一批照片。1931年,他进了柏林迪普霍特公司,由一位达达主义欣赏者管理的先锋派影社。他在暗室内洗印放大。当他走出门,街上都是纳粹分子了。安德烈从来不怕打架。但怎样才能跟这些日夜在大马路上列队经过的褐衫党暴徒有效斗争呢?冬天他跟同伴在希特勒分子要经过的路上浇上几桶水,结了冰让穿灰绿色的士兵跌倒。

他回到实验室心里着急。他感兴趣的不是在室内工作,而是写报道。必须等待机会。安德烈郁郁不乐。终于,1932年11月有一天,由于迪普霍特的摄影师都派在外面,实验室的小伙子也接到了出差的任务。托洛茨基要到哥本哈根,同时——也是日期巧合——还有美国滑稽明星劳莱与哈台。派他去柏林把这三位公众人物的照片拍回来。拍那两位幽默演员,没什么大问题。而那位政治领袖,是另一回事。因为托洛茨基不喜欢照相,总是害怕在那些大箱子和闪光灯后面躲着斯大林派来的武装杀手。有一支两百名警察组成的护卫队保证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安全。在这样的条件怎么走近他才能不引起注意呢?
安德烈带了一只35毫米徕卡小相机,那时这个机子还不曾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甚至还引起大多数职业老手的怀疑或讪笑。那时代,他的同行宁愿使用叫托洛茨基不信任的这些庞大笨重的平板照相暗箱。报刊编辑部喜欢这样拍出来的照片,不像小的不能修改。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也在同一时期开始从事摄影,也选择徕卡;克特斯和其他几位也是这样。他们赞赏这种机子小巧玲珑、光度亮,快门速度高,曝光时间短。
安德烈口袋里藏了相机,到了体育馆入口处,革命家将在那里面发表演说。他毫无阻碍地通过检查与验证,坐到了主席台附近,身子贴在墙上,在不用闪光灯情况下曝光长而手不抖动,对着演说者拍了一系列照片,居然没给人发现。
当他回到柏林,迪普霍特公司举行庆祝会:《世界镜报》刊载了托洛茨基的照片。
1933年,帝国大厦纵火案后,安德烈·弗里德曼,这个匈牙利犹太人,跟着古斯塔夫·雷格莱走上了流亡之路。他去维也纳,然后回到布达佩斯,再去巴黎,没有一分钱,没有人支援。他唯一的财富就是那个照相机,当他手头拮据影响到生存时就去押当,一赚到法郎立即去赎回。为了果腹,他去塞纳河钓鱼。鱼发臭。他在面包店里偷面包。这事危险。他向常在圆顶和洛东达咖啡馆泡吧的穷画家讨几个钱。朝不保夕。亨利·卡蒂埃-布勒松遇到他帮了他一把,把他带到革命作家艺术家联合会会议上。
1934年2月6日,年轻的费里德曼受雇当上一位摄影家的助手,负责把器材带到协和广场,法西斯社团将在那里向民主开火。几星期后,他认识了比他大二十岁的安德烈·克特斯,后来又认识了罗马尼亚人布拉赛。周围这些人立即欣赏他的才华,也靠了他们,安德烈受聘于各摄影社,分配到一些次要的任务,如冲印工作或出售相册。
1934年,他遇到了绮尔达。她是犹太人,德国人,反对纳粹。她也是从自己的国家逃离出来的。这个自由派女青年,加入极左派运动,青春美丽勾魂摄魄,安德烈见了立刻迷上了。但她不是自由的。他也不是,他与《时尚》杂志社工作的一个时装摄影师还保持来往。
他割断了关系。她也是。他们隔天在下等旅馆见面,然后分开,因为绮尔达不愿有太密切的关系。除了工作上的。
1934年,安德烈被《见闻》杂志派到萨尔地区做报道。回来后他赊购了一台徕卡相机,带了这个机子创造了传奇。他拍摄了1936年大罢工,人民阵线游行和胜利。绮尔达协助他,给照片的说明打字。他们俩一起走遍各大报社出售照片。由于事情进展不像他们希望的那么快,他们使用了一个简单的花招,却得到了不可估量的效果。他们各自自称是一位天才摄影家的助手与销售员,全世界的报社都在争夺,他的名字叫罗伯特·卡帕。
从此以后,安德烈·费里德曼就用这个名字写他的报道。至于绮尔达·波霍里尔,变成了绮尔达·塔罗。她不愿委屈自己当销售秘书,也要有个摄影记者的身份。他们就这样双双到了西班牙。他带了他的徕卡,她带了她的洛莱法兰克斯。他们去巴塞罗纳、马德里、毕尔巴鄂。到阿尔梅里亚与格拉纳达之间的山区。后来又到马德里、格尔尼卡附近。他带了他的35毫米相机尽量贴近目标投身到火线中。动作迅速轻快,取景器对准面孔,发明了一种拍摄战争的新方法。而她不如他期盼的那么爱他,不管他怎么努力,怎么要求。这个男人身材魁梧相貌英俊,魅力十足,一生不愿结婚要保持独立 ,即使和影星英格丽·褒曼往来几年也不结婚,而是深深眷恋这个矮小的棕发女人。1937年费特里可·波莱尔·加西亚扑倒在西班牙土地上的这张照片发表后,英国报刊颁给他世界最佳战争摄影师的头衔时,她也在他身边。这张照片就叫《士兵之死》。
1937年7月30日,奥斯特利茨车站,早晨八点钟。
罗伯特·卡帕身体僵直地站在月台上,瞧着火车头驰近。记者穿黑衣。他在哭。他没有带着他的徕卡相机。几个朋友围着他。他们是来等候绮尔达·塔罗的。
这个青年女子报道了第二届保卫文化作家大会开幕式,回到了马德里。她愿意为阿拉贡主编的《今晚报》持续报道共和派在马德里东北部向布吕纳特城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有两个兵团投入这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战役,目的是切断集结在大学城和卡萨德冈波的佛朗哥军队的给养。这是一场硬仗,试图减轻对首都的两面夹攻压力。
绮尔达在烈阳下亲历了这场激烈的殊死战。九万共和国士兵,在装甲车、空军和野战炮的支持下,抗击佛朗哥的摩尔兵。绮尔达的身影小巧灵活,伏在壕沟里,她一手拿着自己的洛莱法兰克斯,一手拿着卡帕借给她的小摄影机,腰间别着一把手枪。她叫她的同行钦佩,也让战士倾慕,个个都赞扬她的非凡勇气。她离开护墙去拍摄进行狙击和低空飞行的飞机。她在枪林弹雨中大笑,跑遍战场的角角落落,捕捉冲锋、装甲车行动、进攻与后退的镜头。她成了部队的吉祥物。她像孩子那么纯情,像玩偶那么可爱。但是冷静坚定,她要用自己的照片向全世界证明不干涉政策是一个神话,德国与意大利军队在全力支持法西斯分子。总参谋部军官敦促她离开前线,她拒绝服从他们的命令。她眼睛瞄着取景器,在她的胶卷上拍下了爆炸的炸弹,跳着死亡芭蕾的飞机,在炮弹下倒地的人,从机关枪发出的子弹。
共和派攻下了布吕纳特。他们占领了几天。秃鹰兵团前来增援法西斯。德国梅塞施密特机打击苏联查多机。新轰炸机造成第十二、十三和十五国际纵队重大伤亡。7月24日上午,佛朗哥分子又攻下布吕纳特。
25日,绮尔达在马德里公路上宿营。她要寄送她的照片,26日到巴黎与卡帕约会。她拦下了一辆车子。里面有伤员躺在后座上。青年女子爬上踏脚板。司机启动。但是对面来了一辆装甲车。汽车为了躲开往旁边一闪。装甲车撞上了汽车车身。踏脚板的一边。
绮尔达被送至美国战地医院,当晚就对她做手术。她要求人家关照卡帕和《今晚报》编辑部。她第二天黎明时死去。
27日在巴黎,卡帕从《人道报》上得到消息。他立刻动身去图卢兹接绮尔达的尸体,它应该由飞机运回来的,但是由于灵柩最后运到了佩皮尼昂,从那里又有火车送至巴黎,卡帕又回来了。
所以,7月30日上午八点钟,他为什么等待在奥斯特利茨火车站。他等待绮尔达·塔罗盖满了花朵的棺木。因为一路上,在巴伦西亚,在马德里,青年女子的朋友和崇拜者在她四周献上了几百朵花。
绮尔达八月一日安葬在圣拉雪兹公墓。她二十六岁生日那天。几千人跟在送葬队伍后面。第一排有阿拉贡。他的旁边是卡帕。落葬以后,他逃到阿姆斯特丹独自痛哭他永远消失的至爱。
但是他后来回到了西班牙。
二、特鲁埃尔
1937年7月那个月,雷格莱在马德里治伤,卡帕在哀悼塔罗,海明威则进了白宫。玛泰·吉尔汉姆向埃丽诺·罗斯福引见他,他向总统夫妇介绍伊文思的影片《西班牙土地》,由海明威自己写、自己念的解说词。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美国政府重新思考不干涉政策的原则。同样在好莱坞,像马尔罗在他之前做过那样,海明威也为共和派事业募集资金。还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他支持作家介入反法西斯事业。
9月,他在玛泰陪同下又回到西班牙。
马德里战线上情况稳定了下来。居民已经习惯走在被炮弹炸开、填满石块的坑坑洼洼路面上。许多大楼都有窟窿,缺少窗户。大门都被拆走。但是入口处堆着沙包保护的电影院座无虚席,酒吧人满为患,所有商店都开门。
海明威比任何哪个战地记者都精明,学会了穿过马路怎样防范枪击,他认出哪些角落最不危险和最少中流弹。他让玛泰躲在身后轻松地从佛罗里达酒店到了盖洛特酒店,那是俄罗斯人的殿堂,他在那里就像在自己家里。岗哨一看见他,他就友好地打个招呼,像是一声口令。他走进去不用通行证,穿过大厅也非常自然,乘电梯直达那些楼层,跟苏联同志,尤其是《真理报》常驻记者科尔佐夫,碰杯喝酒。海明威没有改变他对共产党的过敏心理,绝对没有。但俄罗斯人的军事与组织才能叫他像其他许多人一样肃然起敬。他甚至同意给《真理报》写一篇文章。
海明威离开盖洛特,朝着冈维亚去,走进基可特,这是所有战地记者和马德里名流聚首的酒吧。啤酒与威士忌已经绝迹,供应的是西班牙人粗制滥造的代用品,海明威刮好胡子也当剃须水使用。作家亲临战争现场这种气概就叫大家佩服。还有他的勇敢。
他总是第一批前赴前线的人。这样1937年12月他到了特鲁埃尔。
共和派包围特鲁埃尔后,把城市攻了下来。
海明威又出发前往巴塞罗纳。12月29日,佛朗哥对特鲁埃尔发起凶猛的反攻。一月份,在公共大楼、住房和地窖都有战斗,老百姓已经疏散。天气冻得像西伯利亚,坦克与卡车发动机里的油都上了冻。这次轮到共和派被法西斯分子包围了。法西斯分子受到秃鹰兵团意大利人与德国人的支持。国际纵队直到那时都没有直接参战,也被要求去增援。但是它们没有能够遏制正面进攻。
二月份,法西斯分子重新占领特鲁埃尔。共和派在这场战役中损失了三万人。一万五千人死亡,同样数目的人被俘。
在巴黎,安德列·马尔罗发表了《希望》。在基韦斯特,海明威把他的笔记都集中整理,后来成为他下一部小说的题材:《丧钟为谁而鸣》。
他们在佛罗里达酒店相遇,他们互不喜欢。是作家之间的嫉妒?海明威称赞《人的处境》,不欣赏《希望》。他认为马尔罗过早离开西班牙这艘船而泄了气。他是不是忘记自己又太迟上船了呢?不管怎样,马尔罗是在战争初起时就介入进去,而海明威则跟着最后一批人折返过来。他两人都写了一部书,都拍了一部电影。
1938年初,共和派当局要求马尔罗根据自己的西班牙经历拍一部电影作品。政府的意图是要全世界警惕不干涉政策是一个骗局。在约请以前,马尔罗可能已经想到拍一部电影。
在他的思想里,这部电影不应该是他的小说的改编,虽然其中主要元素可以借用。剧本要围绕共和国航空事业,但不止于此。电影理所当然要在西班牙拍摄。
马尔罗在几星期内写出脚本第一稿。马克斯·奥勃,西班牙剧作家,把它翻译成他的语言。然后作家变成电影人,组织他的摄制组。
海明威已从美国回来。可他不在马德里,也不在巴塞罗纳。他坐在司机驾驶的一辆汽车里朝着埃布罗河前线驰去。他像那时在西班牙的所有观察家一样,知道共和国的命运就取决于这一仗。因为自从佛朗哥占领了阿斯图里亚斯和巴斯克地区,形势对政府严峻可怕。它不但失去了关系经济命脉的矿产区,今后还必须面对一支已经占领国家三分之二领土的军队。法西斯军队在二月份两次攻下特鲁埃尔后,又进行集结,对阿拉贡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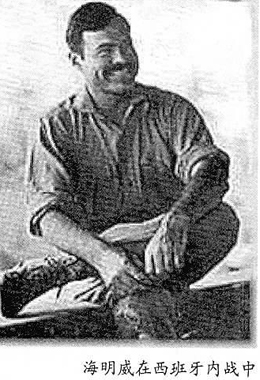
从三月份起在埃布罗河边岸,二十万法西斯军队面对十万共和国军队。双方都挖了壕沟。人人都躲在芦苇丛里等待。
民族派3月9日进攻。他们比对方兵员更多,装备更精良。只用了几天工夫就攻破了防线。他们沿着埃布罗河右岸长驱直入。他们朝贝尔切特进军,攻下了城市。海明威叫自己的车子停下,观察一架有八架机关枪的单翼飞机,朝着他飞下来的动作。飞机又爬升了。它把一批炸弹扔向雷乌斯。记者—作家只是在爆炸后几分钟就开进了城市。他发现房屋洞穿,水管断裂,马匹受伤,但谁都不愿结果它们,认为它们还可能使唤。
海明威朝加泰罗尼亚法尔塞城驰去。他遇见难民:妇女、儿童、老人,坐在满是床褥、餐具、被单、麦袋和什物的大车上。“一名老妪挥着鞭子驾一辆大车,哽咽哭泣。这是我一天中唯一看到掉眼泪的女人。”(引自海明威《在前线》)
然后汽车放慢了,让首先没有武器的士兵先走,然后是卡车、辎重、背步枪的步兵、大炮、装甲车……然后是国际纵队中海明威认识的美国战士,有几人住在纽约、芝加哥,他们向作家保证在这一边的共和国军队会在埃布罗河抵抗到底的。
1938年4月3日这天,海明威要司机向右转弯,开上塔拉戈纳-巴塞罗纳公路。
十二天后,在托尔托萨附近,作家观察到十五架德国汉格尔机和意大利轰炸机,由德国空军战斗机护航,攻击一个步兵连。法西斯分子离地中海只有几公里远。他们势如破竹朝着海边去。安德烈·马尔蒂,外号阿尔瓦塞特屠夫,下令对企图逃跑或往后败退的国际纵队志愿兵都格杀勿论。但仗打败了,全线溃退。4月15日,早晨四点钟,海明威还在加泰罗尼亚的月色下开着车走。他迎面遇见难民与士兵。他停下,问他们情况。他赶在他们前面到了在埃布罗河河口的托尔托萨,他希望在那里越过河道再北上巴塞罗纳。但是桥已被法西斯飞机炸毁。
司机往回转,挤入了涌过来的几十辆卡车之间,最后是通过一座用几块大小不一的木板拼成的临时桥梁过河的。
当晚,法西斯军队得到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支援,到了海边。大事不好:共和国被切成两截。
《特鲁埃尔山脉》好歹在艰难中继续拍摄。政府把城里的摄影棚调拨给摄制组使用,还配上几名技术人员,安德烈和约塞特从埃布罗前线去找来的一名录音师。但绝大部分的器材来自法国。这就是照明设备和胶片。依靠莫利尼埃在航空界的各种门道,在巴黎与达喀尔之间飞航的航空邮政公司飞机,有时在图卢兹或巴塞罗纳降落,在那里一名机组人员就收下从法国运过来的器材。马尔罗凭判断拍片。他不能够审看拍好的片子。他的工作很多取决于临场发挥。
每天根据拍摄进度,尤其是当时情况决定分镜头处理。每天早晨,有一辆汽车把马尔罗的三名秘书之一送到丽兹酒店门口。她带了一台打字机,听写作者口述的新剧本,代替已不能再用的旧剧本。然后她就去马克斯·奥勃住的美琪酒店。这位戏剧家立即翻译新剧本,经常都是当天或第二天就拍。同样也会在拍摄现场,导演叫停,拿起一张纸,他又成了编剧,写出一组他刚才来了灵感的意想不到的一组镜头。
政府掌握的一切军用物资都用于战事,原来要用坦克的镜头都删去。要用飞机的镜头也删去,除了仅剩下在共和国军队的一架波泰机,允许马尔罗用于拍摄起飞与飞行。这些画面与从纪录片中取出的画面掺在一块使用。至于其他东西,那是用啥做啥了。这即是说用一座木制的驾驶舱,隔板是移动的,让摄影机拍摄时可以有必要的景深,或者用断裂的机架拼凑起来,造成真实的幻觉。有一次很幸运,拍摄组弄到一架拉泰科艾尔旧飞机。放机关枪的地方放上了摄影机,飞机起飞了。不料被法西斯空军当作了战斗机,差点葬身炮火之中。
1938年11月5日。
水位猛烈上升使埃布罗河不好行驶,一艘小船在河面上摇晃,险象环生。法西斯分子在北岸打开了堤坝,要淹死后撤的共和国战士。木船现在已被一根绳子系在对岸。绳子骤然断裂。船漂流而去。一阵激流使它左右颠簸,危险地朝着几块铁片撞过去,那是被佛朗哥空军炸毁的一座桥梁的残骸。在船上是一个船夫和三五个记者。他们从前线回来,由于局势过于危急,指挥部把他们送往后方。
船夫是瘦弱的农民,显然营养不良已有多时了。他对着激流无可奈何地抗争。有一位记者抓住船桨,插入水中,用力划,使船走上原来的线路。它奇迹般地搁浅在河滩上。海明威刚才救了同伴们的命,在他们喝彩声中下了船。卡帕给他的莱卡装上胶卷,跟着他。他们跑着去藏匿在芦苇中。
海明威在八月份回到西班牙。10月30日拂晓,法西斯分子在埃布罗前线进行大规模反攻时,他正在那里。卡帕也是刚在那里重新见到他的。
几小时以前,他们一起渡过河流。巴黎公社营营长陪着他们。桥梁已经全部摧毁,他们登上一条有四个划桨人的大木船。海明威用香烟支付他们。他们又回到埃布罗的莫拉,这座城市已成废墟,卡帕拍了很长时间。然后他们又往回走。他们是最后一批渡过埃布罗河的人。现在,海明威朝巴塞罗那而去,而卡帕则到塞格河——埃布罗河的支流——去找共和国军队。62西班牙换位游戏自由派作家们!
摄影师还没有从绮尔达死亡的伤病中恢复过来。他不能原谅自己带着这个少妇走上死亡之路。但是,过了几个借酒浇愁的夜晚,到荷兰去了一趟,然后又是纽约,第三次旅行是到了中国,之后他精神好了一些。他有其他冒险事迹。在纽约,由朋友凯尔代兹(他从此定居在那里)的帮助,他完成了一部书,汇集了绮尔达与他在西班牙拍摄的照片。这部作品是献给那位女摄影师的,谁问他他就会指着她的肖像照说她从前、现在一直是他的妻子。他是永远不会把她忘记的。
在纽约,他与《生活》杂志社订了一份合同稿酬预支,照片以后再寄。这样,他与伊文思一起去中国报道中日战争。1938年1月到9月他留在中国。一回到法国他立即又去西班牙,特鲁埃尔战役时他在那里住过一个短时间。就在海明威回美国之前他与他一起在圣诞子夜弥撒后聚餐。
他在塞格,拍摄了共和国士兵飞快越过一个遭轰炸的地段,从一堆石头上跳入一个天然掩体,把他们受伤的同志拉回来。他眼睛瞄在莱卡取景器,在胶卷上拍出令人难忘的镜头,《生活》杂志用满满两大页发表出来。工作结束,他又前往法国。

海明威也走了。他把玛泰留在巴塞罗那美琪酒店。自己回美国,妻子波丽娜在等着他。但是跨过边境以前,他跟林肯旅的美国志愿者度过一天,他们也要回国了。整整十五年,海明威再也没有踏上西班牙国土。他以自己的方式——这也是马尔罗的方式——继续进行他在那块土地上长年累月作过的斗争;1940年,他发表了他的关于西班牙战争的小说《丧钟为谁而敲》,第一年销售出五十万部,此书献给他的第三任妻子玛泰·吉尔汉姆。
12月23日,法西斯分子在北方发动他们最后的进攻。马尔罗在巴塞罗那继续拍摄《特鲁埃尔山脉》。几星期以来,工作条件变得不止是艰难,简直是折磨人。城里几乎没有吃的东西。食品供应只能来自国外,但是由于佛朗哥军舰实施封锁,无法运送。当一艘船好不容易突破战船的阻拦,就遭到飞机的轰炸。以致造成了饥荒。摄制组也是依靠亲朋好友从法国捎过来的东西过日子。
更糟糕的是,埃布罗河失守后,佛朗哥沿着河岸北上。他们轰炸了塔拉戈纳,正在逼近巴塞罗那。这部影片怎么才能拍完呢?
逃亡者挤满加泰罗尼亚各条公路。在海港,他们绝望地要爬上已经超员,而且迟早也要遭到敌人战斗机扫射的船只。别的问题不谈,先说怎么回法国去?政府自身也从一个个城市朝北方迁移。大家还看到内务部长手执武器,试图指挥通往法国的主要公路上的交通。巴塞罗那的马路上堆满垃圾,附近的爆炸声震耳欲聋,一百万名难民挤来挤去,到处呈现恐惧与绝望气氛。有人抢劫空无一人的商店。大家察看天空中巡逻的飞机。有人看哪里有黑烟,表示火正在烧过来。
1月10日,在美琪酒店大堂里,马尔罗遇见从法国过来的卡帕。玛泰也在。轰炸使她非常受惊。卡帕为了安慰她,待在房间里陪着她。后来他挎了莱卡相机溜到加泰罗尼亚公路上。他对着逃在佛朗哥分子前面的难民拍照。
雅古埃纵队向塔拉戈纳进军。1月14日,它攻下了城市。巴塞罗那公路如大门洞开。卡帕回到美琪酒店。他在1月25日夜里离开加泰罗尼亚首府,而法西斯分子到了城市的郊区。他寻找在卡尔达塔的美国大使馆,留在西班牙的最后一批美国人等待登上“奥马哈”号巡洋舰。《生活》杂志做到让卡帕跟这些人一起离开。但是摄影师加以拒绝。他去找难民,陪着他们逃难。好像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都在向北方涌去,再加上已经逃离安达卢西亚的人,加上已经逃离埃斯特雷马杜拉的人,加上从战争初起时已经逃离落入敌人手里的领土的人,再加上安东尼奥·马查多,他逃离祖国再也没有回去。
几辆官方的汽车开在公路上,朝佩修斯而去。有几辆车上堆的是哥雅、委拉斯凯兹或提香的画,这些画已从普拉多博物馆运至菲格拉斯,现在政府要送往日内瓦。后面紧随的是呼哧呼哧的卡车,由于上面的人超额压得滚动艰难。在其中一辆卡车上,约塞特缩着身子靠着马尔罗。马尔罗坐在栏板后面跟其他旅客一边。在他的脚边有一只纸箱和几只纸袋,里面包着最后几卷已冲印的胶片。片子摄制工作并没有完成,只拍了脚本的三分之二的。后来到了维尔弗朗什德鲁埃格才补拍了不可缺少的镜头,完成衔接与补充。在茹安维尔剪辑。重新配音。缺失部分用解说词补充。
1939年春天全片完成。流亡的西班牙政府成员观看了片子,预期在1939年9月15日问世。但是在法国驻马德里的新大使干预下《特鲁埃尔山脉》遭到达拉第政府的禁止。在二战时期,有一份拷贝奇迹似的保存了下来。影片在1945年6月放映,片名改为《希望》,获得路易-德吕克奖。
要求禁映这部影片的法国驻西班牙大使是一位法兰西元帅。他的名字叫菲列普·贝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