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柏栎
文:[英]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注:该文作者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和文学传记家。在此文中,她对伊迪丝·华顿的短篇小说作了一番研究。)(Margaret Drabble)

华顿对文艺、智辩、装饰和高级时装潮流中突如其来的事物和普遍遵循的东西生就了一双锐目。她能够发现伪品,也能够识别真货。在任何意义上,她都是一位行万里路的女性,而她鉴赏的领域也是十分广阔。
读短篇小说最好是读集子。伊迪丝·华顿是这种文体的行家里手(她这个年龄的人会毫不犹豫地把她看作是短篇小说大师),她这两大册由小说家莫琳·霍华德(Maureen Howard)收集编订的文集,也声名渐隆。这两册书内容丰富,从天马行空到现实主义,从讥诮讽刺到温情脉脉,华顿尝试的风格之多让人眼花缭乱,而她也确实写得得心应手。这里有故纸堆里的题材——鬼故事,寓言,历史幻想,还有描写一个狂热怀旧的鉴赏家的篇什。同时也有不少对当代欧美习俗的精透剖析。华顿给礼仪和道德之辩带来了新锐视角。她深知该怎样写好一篇小说。在《写一篇战争小说》(Writing a War Story)中,她构思了一个准作家,欧文·斯邦。此人发现自己面对大叠淡紫色稿纸时,竟不知所措,没法把她“丰盈的印象”表达出来。
这件事情她想得越多,就好像越不知道该怎么去写一篇战争小说,或者写成其它形式。为什么小说总得有开头,又得有结尾?生活可不是这样,它就是过啊过的。
如果华顿自己也有过这种怀疑,她可掩饰得很好。她从容不迫地组织材料。构思、选材、剪裁、成文,最后摆在读者面前的是瓜熟蒂落,令人满意的专业产品。我们读她的作品,就觉得万无一失。她的小说总有成效。

这两册书篇幅实在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我没有读过,也不知道该从哪里读起才好。那么就让我们先来赏评一篇华顿不太重要的小说,探一探那或许是所谓的蛇尾吧。这篇小说讽刺了文学名声莫名其妙的性质,情节完整,风格俨然,俏皮之处引得读者开怀不已。《赔款》(Expiation)最初发表在1903年12月的《赫斯特环球杂志》(Hearst"s International-Cosmopolitan),当时华顿已经成名,但还没有像两年后发表《欢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时拥有那么多读者,所以也还没有为发现自己名声显赫或喜或忧过,尽管这篇小说显示她已为此做好了准备。《赔款》写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作者在等待自己首部长篇小说《张与弛》发表后的舆论反映时,既期待又害怕的心理。篇名是揶揄华顿在1876到1877年间——当时她才十五岁——写的一个未发表的同名中篇,关于一段和虚构的恶意评论交织在一起的倒霉恋爱(其中部分是对煽情小说的滑稽模仿,她母亲不主张她读那些小说)。这立马就可以和简·奥斯汀的早期作品来番比较,因为近一个世纪前,奥斯汀也是在相仿的年纪开始文学创作,她的处女作《爱情和友谊》(Love and Friendship)以及其它练笔也是对情感小说的仿作。华顿的作品中渗透着奥斯汀的影响:这两位小说家都兴致勃勃地嘲讽把作家当件事来干的人,也嘲讽在叙述手法和风格上改弦易帜的做法。
在这篇有趣的作品中,文坛新手保拉·费斯罗——一个婚姻如意,身份体面的纽约名流,和她的表姐克林其夫人形成对比。克林其夫人精明世故,喜欢死撑台面,婚姻不太如意,而她丈夫从未在小说里出现过。她以写作为生,写一些自己姑且称之为“伪科学和口语鸟类学”的文章——诸如《鸟窝半敞》和《怎样闻花》。她们的叔叔则是第三种作者,是个自以为是的人,在奥斯宁当主教。他的文学作品有《约拿的痛哭》(二十章无韵诗)和《明亮地穿过玻璃杯》。后者是个陶冶情操的故事,说的是一个患了肺痨的贫苦女孩如何勉力养活两个白痴妹妹。我们猜想,这位主教的大作销路不怎么样。
有趣的是,虽然这三个人的文学创作态度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发觉要使一部作品畅销,猛烈的抨击比浮泛的赞扬更能见效。华顿精彩地刻画了费斯罗夫人所受的微妙的心理折磨,先是因为她丈夫对她毫无原则的赞美和“愚不可及的认同”而痛苦不已,接着是害怕她的主教叔叔会因她的书不太宣扬道德律而恼火,而且一旦把他惹恼就毫无办法了,最后是由于评论家们公认《张与弛》具有“耳目一新的人生观”。最后一种打击当然最要命。她的第一个评论者认为她震撼人心的社会批判“虽然人物刻画毫无力度,情节也缺乏连贯性,但家庭生活描写得很好,可以称得上是个相当不错的故事”,我们未来的易卜生一听到这话就满心恐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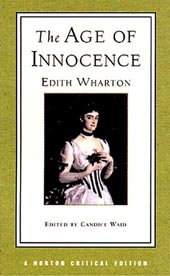
主教被说服了到教坛上抨击侄女的小说,于是它立即畅销起来,一场潮流过后,大家的结局都挺好。当费斯罗夫人看到她的“印有作者像的新版书(第十五万册)”被装饰在车站的书肆中,不由抱怨道,“他们没有权利把我的照片当作招贴画!”自从那天她“不太确信地”告诉克林其夫人说她觉得一本书的成败完全应该按照书的好坏为准,她很快就取得长足的进步,学到不少东西。
对打造文名的讽刺想象扎根于当时的年代,主教对小说的批判能带来商业价值显然和恶毒攻击托马斯·哈代的《无名的裘德》不无关系。1894年,该书在《哈泼斯新月刊》(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上连载时,引燃了熊熊怒火。它被一位主教当众烧毁,过后却大大地出名。(在1912年版的前言中,哈代写道,此书“被一位主教焚毁,他很可能是因为无法来烧死我而感到绝望”。)但是,《赔款》也是为我们这个时代而作的,如今猛烈的抨击虽然不是出自主教之口,但还是能把书卖出去。

华顿对文艺、智辩、装饰和高级时装潮流中突如其来的事物和普遍遵循的东西生就了一双锐目。她能够发现伪品,也能够识别真货。在任何意义上,她都是一位行万里路的女性,而她鉴赏的领域也是十分广阔。外表上她不是个现代主义者,但她的阅读量惊人,而且她分析社会的手段一寸不拉地紧跟时代——其实是超越时代。向来认为,她对道德风尚的嬗变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而这正是她小说的主心骨之一。在多篇小说中,她着力于绘制新的二十世纪社会地图。她预见到传统宗教的式微和相对主义思想多样化的发展。(在《信仰的种子》(The Seed of the Faith)里,她满怀同情并恰如其分地低调刻画了一个年轻穷传教士的疑虑。他被困于北非,在与“一个正在研究中部山区部落的法国民族学家”有过两三次交谈后,很是悲惨地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无知。)在她的图表中,离婚率正势不可挡地攀升,而妇女解放的进程却缓慢并不时裹足不前。在《估算》(The Reckoning)和其它一些短篇中,她细细描述了那些自称信仰她所谓的“新种族主义”的人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挣扎所付出的高昂的个人代价。离婚和各种婚外情为她提供许多故事情节,而她的写法则从讽刺到悲剧到悲喜剧一再改变,有时在一篇小说内都有细微变化。
我们一直认为伊迪丝·华顿喜欢在作品中陈列那些苛刻的行为规范,表现纽约贵族阶层凶暴残忍的特性,但是这里的一些短篇却别具惊人的现代意味。在《另外的两个》(The Other Two)中,一个快乐丈夫有个结婚多次、很有魅力的妻子,由于一系列古怪的巧合,他要在家里请他妻子的两位前夫喝茶。他发现,妻子招呼两位不速之客的态度“随意而亲切”,于是这个场合就不那么怪异了。这个词选得好,它充分证明了这是一个新世界——尽管那个殷勤的第三任丈夫能否一直在这个世界里快活下去是个问题。
试比较调子更沉的《其他时间》(Autres Temps)和《长远计划》(The Long Run),这两篇讨论的都是和性有关的年龄和失败问题。前一篇中的黎蔻特夫人,由于一次两性事件上的出轨,多年没有回纽约,后来她回到刚刚离婚又结婚的女儿家中,大惑不解地得知如今离婚已经被社会接受了。但是她发现自己处身于一片影射和误解当中,甚至那些急不可待地告诉她一切都已改变的人也在排斥她。对于她女儿来说,未来也许是在这里,也许光明。但是在黎蔻特夫人而言,这太迟了。

同样在《长远计划》中,就像是《安娜·卡列尼娜》的模式,一个勇敢又不循传统的已婚妇女不顾一切地把自己献给了爱着自己的男人,而且非常清楚他就像渥伦斯基伯爵一样,已经设想到私奔后的未来是“百无聊赖的夫妻在简陋的矿泉疗养院打发时光,靠着旅馆熟人的好处过活;要不就是两个自负的可怜虫关在一栋好房子里吵嘴,因为他们好得没法适应那个对他们来说是绝无仅有的社交圈子”。然而她的勇气无济于事:他拒绝了她,也拒绝了凑合着生活的念头。最后“在长远计划中”,我们看到,他们失去了机会,错过了抉择,都降格成了妥协而平庸的人。
华顿笔下的妇女纠缠在习惯势力和新的性自由可能之间,她自己享受过这种自由,虽然代价高昂。她描述了社会关系和未来展望施加在妇女身上的历史性畸变——家庭之中,两性之间,女人之间。女人的竞争和嫉妒——弗吉尼娅·伍尔夫预言过的那个旧体制中的情感当会在新体制下消失——在有名的《罗马热》(Roman Fever)中得到精彩的表现。特别有意思的是华顿对母性扭曲的描写。她没有孩子,而且也不像一般人那样沉溺于母性冲动。她的早期作品《鹈鹕》(The Pelican)故事情节简单,写的是母爱误入歧途后造成的毁灭性后果。篇幅较长,含义模糊的《避难所》(Sanctuary)要复杂得多,不能把它归结到任何一种确切的理解上去。它写的是慈祥无私的母爱呢,还是有害的母性占有?我们看到的女人,是彻底妨碍儿子寻求真正的成人自由呢,还是把儿子从父亲道德败坏的命运中挽救出来?而笔触是那样地不偏不倚,几乎不可能——我觉得确实是不可能——据此来下定论。对动机的心理分析非常深刻,故事中行为的道德意义却暧昧不明,这样小说就呈现出自身的意义来了。我们能用我们的方式来解释,也能用弗洛伊德的方式。这是一场精彩的内心斗争,可是无论好天使和坏天使都披着重重伪装。
同样引人入胜的《她的儿子》(Her Son)面目就清楚许多,这说的是一个漂亮的寡妇结婚时没有收养她丈夫的儿子,后来却心生愧疚,一直在寻找那个私生子。人到中年,她越发因此耿耿于心,不能释怀,最后走向毁灭。错综复杂的情节通过一个若即若离的男性叙述人逐步展开。这种口技表演式的手法在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中很常见,华顿也常常毫不含糊地加以运用。(她显然觉得由男性来当叙述人更加保险:在这些短篇小说里,她极少冒险使用女性叙述人,尽管她在处理女性题材和女性观点时是信心十足的。)《她的儿子》是篇相当成功的小说,每一幕——包括最后也是最令人吃惊的意外——都是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避难所》里的故事有些不切实际,情节虽然更加热闹,却透着一股子挖苦味。叙事技巧圆熟,有莫泊桑的风格,最后关于小刀的转折尤见功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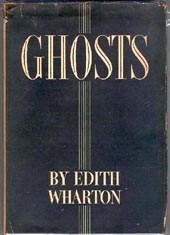
短篇小说的格局往往不是开头吸引人,就是结尾刺激人,华顿当然也没有回避这些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她的生活也是相当富有戏剧性——意外的遗产,经济罪,他人的早逝。一碰到猝死和不太光彩的情节需要,伤寒、肺结核、破产都是作者的惯施之伎,这也反映了常见的社会现实:艺术家确有病死在阁楼上的,商贾也有因股票交易而破产的。华顿圈子里那帮靠收租过着奢侈生活的朋友,也不能幸免于当时的疾病:华顿的同代人阿诺德·本涅特是个名声鹊起、非常成功的小说家,他和华顿一样,嗜好以蒸汽游艇、摩托汽车等为交通工具的昂贵旅行,后来在巴黎餐馆里喝了一瓶子水就染上伤寒,好歹也就这么死了——这种死法,鉴于本涅特的现实主义风格,他是肯定不愿去写的。所以我们不能因华顿描写了许多突发事件和不太可能的事情而怪罪她。和本涅特一样,华顿也喜欢描写暴富,在优秀的喜剧寓言《天鹅绒耳套》(Velvet Ear-Pads)和《书信》(The Letters)中就用得很好。后者写的是一个穷教师莉齐是怎么被一笔意外的遗产改变的。有人或许觉得这不太可能,但是华顿在1888年就亲身经历过,当时她和莉齐一样急需用钱,而就在爱琴海的航船上,她从一个“隐居纽约的表亲”那里继承了十二万美元。

华顿出身于衣食无忧的家庭,因此她多方面受益,但她也为之付出不菲的代价,往往长时间地精神紧张,经常患病。她不太描写极度紧张以致精神崩溃的内心世界,她笔下的人物,无论男女(除开那些在故事里遭受厄运的)都是精力旺盛,身强力壮。也许只在她的鬼故事中,她那孱弱的身体和精疲力竭的自我斗争才能以次要的主题浮现出来。这里有几篇经典鬼故事,而集子里将近三分之一(六十七篇中的二十篇)的文章都有超自然现象和惊悚情节。鬼故事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华顿写作的部分动机也无疑是要取悦读者。
她的典范有奥斯卡·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1890),这个故事几次改头换面出现在小说集里。有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The Turn of the Screw)(1898)和《阿斯朋文稿》(The Aspern Papers)(1888),后者超自然现象较少,但也是鬼影重重。老畅销书《古董商的鬼故事》(Ghost Stories of an Antiquary)(1904)的作者M.R. 詹姆士也在小说集里留下了痕迹。还能看出罗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和托马斯·哈代的影响,这两位都时不时地光顾这个题材。华顿举重若轻地谋篇布局,虽然有些地方也无非只是让人脊背发凉的老做法罢了——也就是常见的亡灵,咒语和乡屋闹鬼。有人要说关押少女这种主题是反映了世纪之交妇女无能为力的社会现实,而华顿也在这种可能性上做了些变动,包括父亲关押女儿和男管家的鬼魂监守死了很久的妻子。但这既缺乏创意,又没什么说服力,尽管故事是很好看。读者会觉得她写作时考虑更多的是笔墨和钱包,而不是想象力。虽然她也从玛丽·雪莱那里借用了少许效果,但她完全没能激起《弗兰肯斯坦》那种无法言喻的共鸣。

在我看来,这些鬼故事中最好的一个是题为《玛丽·帕斯克小姐》(Miss Mary Pask)的奇怪小短篇。故事发生在烘托气氛的布列塔尼,男叙述人擅自决定要去拜访一个美国朋友的姐姐,她独自隐居在亡灵港?(Baie des Trepasses)的一栋房子里。他到的那晚——当然是夜晚——浓雾弥漫,老大不情愿的向导还离他而去。他找到了一头白发,激动不已的帕斯克小姐,可是正当他找到她时,他想起来她其实已经死了——他忘了(这有点不太可能)她是在前一年秋天死的。故事结尾处的转折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小说中老妇人和年轻男子的相遇写得很出色,老妇人的风蚀之躯让年轻人触目惊心:“我看着布满皱纹的柔软手指和傻乎乎的椭圆形指尖,那曾经是多么顺眼又可爱的粉红色小指尖,如今在发黄的指甲下成了蓝色。我心里阵阵害怕,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
集子里篇幅较长,给人印象较深的是《马恩河》(The Marne),不过里面的超自然现象却有点画蛇添足。小说记叙了一个说法语的美国年轻人对一战的看法,通篇文气生动,基本上写得恰到好处。华顿曾在巴黎参加过救援,也几次到过前线,她把这段经历很好地用在了小说里面。战争开始时,滞留在欧洲的美国人恐慌万分,小说对他们的描述毫不逊色于萨克雷《名利场》中对滑铁卢战役的描写。那些美国人在是否要参战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那段文字读起来神清气爽。细节生动真实,一针见血:那些人起先还自鸣得意地倡导孤立主义,后来摇身一变成为群情激昂的爱国人士,相信起“美国的使命”和“自由引导世界”来。华顿对他们的评论影射了现实中的邪恶而危险。小说男主角,年轻的特洛伊·贝尔纳普的性格(虽然大概不是因为他响亮的大名)也深深吸引了我们。他早年就喜欢上了巴黎,“每年六月搭着最昂贵的航运公司最快的蒸汽班轮”和家人一起从纽约来巴黎。他对法国的热情和华顿很像,她身临其境地写出他充满男子气概的遗憾:由于年龄不够,他无法为自己的居留国而战。随着战争的进行,他参加了救护队来满足自己的热望。小说结束的时候,特洛伊发现自己终于在偶然中被卷入激烈的战斗,那是马恩河第二次战役。(这和司汤达《巴马修道院》中年轻的法布里斯在滑铁卢的历险有骄人的类似之处)整篇小说都很好,因此最后华顿把结尾写成了个煽情又超自然的样子未免令人抱憾。特洛伊深爱着的法国老师在四年前马恩河的第一次战役中就牺牲了,但后来又作为拯救天使再次出现。这个结尾和华顿先前的讽刺实在不太搭调。
《马恩河》是献给“1918年8月12日为法国捐躯的罗纳德·西蒙上尉。”写到此处,我正远离我的书斋,而附近也没有任何英文图书馆可以让我查阅罗纳德·西蒙上尉的真人真事,否则我也许会收回我的驳斥。或许,我能写上一小段我自己的鬼故事来补偿这些驳斥。
写这篇文章时我人在威尼斯,身边都是鬼魂。12月31日,我去那里呆了一个月,目的是为了避开我最新在英国发表的小说必然会引起的大惊小怪,事先这部小说被(在没有读过的情况下)抨击过,但干这事的人不是主教,而是我的许多家里人,个中原委我很理解。
我来到威尼斯就是一种很华顿式的风格,虽然可能没有那么宏伟,手头还有一部写了一半的小说在继续,美国图书馆出版社的活页校样像卜筮叶子一样在我四周扑扇。(华顿最后一篇鬼故事《所有灵魂的》(All Souls")的最后一页神秘兮兮地失踪了。这一发现让我惊惶失措——我能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吗?)在威尼斯读华顿,正如我所料,是件乐事。我还发现,而且我早知道我会发现,里面有篇以威尼斯为背景的好小说:《一瞥》(A Glimpse)。小说写得很美,照例是由一个经验丰富的男性旁观者担当叙述人,讲的是一个男大提琴家和一个女钢琴家之间的夺权斗争。我读到这篇小说的前一天正好去里亚托附近的圣帕塔雷渥教堂听维瓦尔第的音乐会,而大提琴家和钢琴家的事就是在里亚托引起了一番联想和沉思。这种事情就会发生在这里。当天晚上,我从里亚托走回家,正巧看到了一次月全食。
我住在我和我女儿的朋友的公寓里。这房子是她曾姨妈的,五年前过世了,活到了九十岁,人走了,房子里还都是她的东西和回忆。她是个画家,她凝固了的生命还挂在墙上。她的书,纸牌,烹饪用具也还都在,她的伞立在伞架上,她没有完成的刺绣躺在抽屉里。她的毛茸茸的虎斑猫不时从花园跑进来啃点吃的。
仲冬时节的威尼斯鬼魅出没,既迷人又惊魂。我卧室窗下,高涨的碧波轻拍在通往小运河的台阶上。有两天棒极了,我出去给自己和猫咪买牛奶,从广场回来时,被涨潮断了退路。每天清晨,警报声穿透鬼气森森的阴霾。一月初的高水位之后阳光灿烂,但冷得刺骨,气温远远落在零下,桥上挂满了冰凌子。我这才发现没有带够暖和的衣服。
一个衣柜里挂着几件姨妈的衣服,她侄女不舍得把这些做工精良,严谨的好衣服扔掉。一个冰冻三尺的夜里,我试了件姨妈的毛大衣。正好合身。我差点想穿着它出去逛一圈,到寒冷寂静,空无一人的赛斯切尔大街上走走。若我真这么干了,肯定会有个邻居从窗口探出来,自言自语说:“我的好朋友埃莉娜·巴列瑞的鬼魂在那里走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