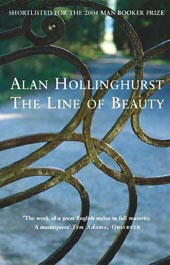
译:李小飞、马宏伟
文:[英] 艾伦·霍林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
窗边突然起了一阵骚动。杰弗里·蒂奇菲尔说:“啊,首相的车到了。”说这话时,他看上去像个在高贵威严的主人面前连头也不敢抬的男仆。他朝门口走去,欣喜若狂,顾不得理会他的话在宾客中引起的震动。客人们面面相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有一两个人不以为然地退回角落里;男人们则无伤大雅地相互推搡几下。尼克跟随人群上到楼梯平台,觉得首相行事实在是谨慎。要是没有这一大群人,没有这般兴师动众,她准会不悦。他被挤到楼梯第一个拐角的栏杆旁,微笑着俯视下方,看上去像一幅历史油画中某个引人注目的无名侍从。门打开了,寒气扑面而来,在潮湿的刺激下,人们益发兴奋。女人们因喜悦不安而发抖。夜晚是她们努力要去征服而又难以驾驭的时刻。那位尖刻的分析家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在笑声和咋舌声中差点绊倒。杰拉尔德早就走到了街上,毕恭毕敬地与特别支队的警察站成一排。瑞切尔就站在房内,窗外的光线透过蒙蒙细雨,照在她半透明的上衣上,令瑞切尔的身体仿佛罩上了一圈光环。人们听到了那个为人熟知的嗓音。人们热切地期待着,有一两秒时间,周遭鸦雀无声。而后,她,出现在大家面前。
她迈着一贯的优雅碎步走进来,暗示着压抑了许久的尴尬和笨拙已经转化为权势。她目不斜视,打量这所陌生的房子。目光所到之处,都让她更确信了自己的魅力。大厅里的大镜子似乎在欢迎她的到来;镜子里映出了人们欢迎的面容。虽然有些面孔看似高贵,但表情远远超越了高傲,是一种混合着大胆和羞涩的着迷神态。她似乎对大家的注目很满意,并愉快地回报以王室成员般的致意。她似乎并未注意到大门的颜色。
楼上又恢复了平静。但这种平静很特别,是那种序曲结束、大幕拉开之后,等着好戏开场的平静。人们又镇定下来。夫人走进房间时(跟在夫人身后的丈夫谦恭地退到一旁,要了杯酒,去找老朋友),人们自动地排成一列迎候。巴里·格鲁姆经过春季应召女郎事件的打击,刚刚恢复了元气。当首相握住他的手时,他诚惶诚恐地低下头;后来有人说,他当时居然说了声“你好”。她诙谐地与万尼打了个招呼,因为最近他们刚刚见过。万尼因为首相还记得他而感到荣耀,但却放弃了再次与她谈话的荣幸;尽管在握她手的一刹那,他还在犹豫是否要行吻手礼。杰拉尔德嫉妒地继续引着她前进,低声介绍着宾客的名字。尼克出神地望着她走近。她真是仪态万方。别人多么优雅,配戴多少珠宝,也无法跟她媲美。她的头发完美无缺,以致他开始想象它湿漉漉地披在她脸上的样子。她穿着黑色长裙,白色和金色相间的阔肩外套上绣着精美的刺绣图案,就像卢里坦尼亚(注:古代欧洲王国。)王国的制服。领口开得很低,露出华贵的珍珠项链。尼克紧盯着那串项链,目光落在她一大片裸露的胸脯以及丰腴的脖颈上。“她真美呀!”特鲁迪·蒂奇菲尔说,不由自主地陶醉了。主人在引见尼克时一带而过,把他的名字淹没在长长的社交辞令中,还令人吃惊地撒了个小谎:“尼克·盖斯特……孩子们的好朋友……年轻的大学教师。”尼克觉得自己既受了抬举,又有点丢面子,因为首相不大喜欢大学教师之类的人物。他点头微笑,能感觉到她的蓝眼睛在他脸上短暂地停留了一下,似乎不太自信,旋即却回过神来,主动向突然出现在他身边的约翰·提姆斯招呼道:“约翰,你好!”“首相……”约翰·提姆斯没跟首相握手,一边用热情而幽默的语气答应着,一边拥抱了她。队伍最后是孩子们,一对美目流盼、天下无双的金童玉女。托比依然神采奕奕;凯瑟琳既没闹情绪也没提傻问题,欢快地一面说“你好”,一面与首相握手,目不转睛地盯着首相,像小孩子见了魔法师那么好奇。“啊,对了,这是我的男友,”她边说边推了一把贾斯帕,却忘了介绍他的名字。“你好,”首相干巴巴地说,似在暗示她需要一杯饮料,而特里斯托也带着温顺、怯生生的微笑,不失时机地及时捧上。

尼克匆匆喝了点东西提神,然后小跑着下楼,发现万尼正从杰拉尔德和瑞切尔的卧室里出来。“天哪,小心点,亲爱的,”他说。
“我就用了一下洗手间,”万尼说。
“喔,”尼克说。心想他酩酊大醉,晕晕乎乎,根本不知道这有多危险。“非用不可的话,用我的好了。”
“还得爬楼梯,”万尼说。
尼克喜欢可卡因的感觉。它能驱除香槟、红酒、白葡萄酒引起的迷糊。它能把这些感觉积攒起来,然后转到快乐银行的新帐户里。它能使人头脑清醒,像一剂醒酒的良药。他搂住万尼的肩膀,问他近况如何。“我们见面的机会太少了,”他说。他们开始往楼下走。刚走了三四级台阶,尼克的眼睛发现了什么,有人在万尼刚出来的那间宽大的白色调卧室里走动。作为房子的守护人,他有义务阻止麻烦发生。他本能地警觉起来。贾斯帕从屋子里走出来,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仿佛拿着钥匙领着买主看房子。他向尼克点点头,挤挤眼。“正要去凯的房间,”他说。
“那么,”尼克一边说一边和万尼继续下楼,每走一两步,就若有所思地踌躇一下,似乎觉得他们应该默契地同时停住脚步。“你上了那个滥交的家伙了?”
“该上,伙计,该上。”
“是啊,”尼克说道,抽了抽鼻子,不悦地撇了撇嘴。他试图在万尼泛出可疑的玫瑰红的脸上找出内疚的迹象;他曾瞥见过他俩在卫生间鬼混。万尼堕落的爱情,吸毒之后的放纵。“那么这不再是我们俩的秘密了,”他说。万尼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却没有挑衅的意思。尼克也许现在还算清醒、有理智,而万尼已经到了飘飘欲仙、眨巴着眼睛、连房间和朋友都分不清的地步了。尼克让他走了,可卡因带来的心跳加速之感,已经变成了奋力短跑后引起的那种恐慌感。他掩饰地笑了笑,药力发作,似绽放的花朵;他似要从中寻找一个更快乐的话题。谁是谁非已经不重要了,现在想得再多也毫无意义。外面帐篷里音乐已经响起,到处都充满着恣意放纵的气氛。
他在客厅一角发现了凯瑟琳,退休大使老琼蒂·斯塔福德正龇牙咧嘴地笑着跟她聊天。他像童话书里快乐的胡话连篇的怪兽,凑近她:“不,我认为你会喜欢多布洛尼克(注:克罗地亚最大旅游中心和疗养胜地。),”他说着,眼睛意味深长地闭了一下。“戴克理先饭店,迷人极了。”
“嗯,”凯瑟琳应道。
“我们总是订新婚套房,你知道的,有一张大床,可以尽情狂欢。”
“应该不是在你的新婚之夜吧。”
“你好,琼蒂爵士。”
“啊,你年轻英俊的情郎来了,我要遭殃了。我也累了。”琼蒂脚步蹒跚地望外走,又去追在另一个女人的屁股后面,没想到那女人正是首相。他摇摇头,回头望了一眼:“了不起啊,真是的……首相……”
“我想刚才有个醉醺醺的老头在向你求欢,”尼克说。
“有人注意总不是坏事,”凯瑟琳说着,一屁股坐到沙发里。“坐这儿吧。你知道贾斯去哪儿了?”
“没看见他,”尼克说。

摄影师跑来跑去,闪光灯在镜子里闪个不停。他在宾客中间穿梭流连,穿着晚礼服、打着蝴蝶结,样子像个似曾相识的讨厌家伙,笑着凑过来,然后,“噗”的一声——拍得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因为刚拍的大部分照片要么有人眨了眼,要么有人扭了头,只好回来重拍。于是,他们又聚拢在一起,面对着镜头;或者端着架子,装作满不在乎,假装没看见他。尼克坐到凯瑟琳旁边,悠闲地盘起一条腿,脸上挂着特有的优雅笑容。他觉得自己可以这样表演一个晚上。他觉得美妙极了,他喜欢这样的夜晚,要是以性爱结束就更圆满了。当然,没有的话也无所谓。尽量用别的事情来弥补缺憾吧。
“唔,你身上的味儿很好闻,”凯瑟琳说道。
“噢,就用了点‘我保证’(注:原文为法文,疑是一种香水牌子。),”尼克冲着她挥了挥袖口。“你跟首相的十二秒钟谈话讲完了吗?”
“我正想说呢,被杰拉尔德打断了。”
“我听了一会儿她晚餐时的谈话,她表现得既普通,又宽容,真是大人物的做派。”
“贪婪,”凯瑟琳说道。
“他们都喜欢那样,他们整晚如释重负地探讨人造黄油和天然黄油的优劣,而她突然把话题转到了共同农业政策,给他们出难题。”
“你没向她谈谈你的想法?”
“没有……”尼克说,“她受制于人,不是吗?她大权在握,却不敢越雷池一步。”
“在这儿她可说了不算,”凯瑟琳说着,示意特里斯托过来。“你想喝点什么?”
“我喝点什么呢?”尼克说,面对特里斯托的程式化微笑诡秘地一笑,眼睛在这位侍者的身上扫视着。“我最想要点什么呢?”
“来杯香槟吗,先生?要么更烈一点的?”

“香槟吧,过会儿再喝点烈性的。”尼克拉长声音说。他眼前升起了欢乐的场景,快感逐渐加深,这是酒精和毒品联合产生的美妙效果。冒险的感觉更增加了安全感;他如今确定自己可以和特里斯托做多年来他一直想做的那件事了。特里斯托只是点点头,当他俯身去取空杯子时,他快速在尼克膝盖上重重地靠了一下。尼克看着他穿过拥挤的房间,有好大一会儿,眼前出现的是同一种幻觉,不论是在这里还是在沃克斯伍德:那些金灿灿的光芒,那些镜子,穿过的一个又一个房间,偶然瞥见的转瞬即逝的燕尾服下摆。这些你梦寐以求的东西,现在都不请自到。原来的拼命追逐只是焦急等待的另一种方式。杰拉尔德说得对:一切都有回报。特里斯托回来以后,欠身奉上托盘里的酒。尼克举起杯子,半是笼统半是隐秘地说:“为我们干杯。”
“为我们干杯,”凯瑟琳说。“别再调戏那个侍从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费登今晚好像很活跃,我说,他平常可不是这样。”他们看过去,只见托比四仰八叉地坐在首相的沙发上,不知在讲什么笑话。首相身旁一大片凹下去的沙发就是个接待区,那些有求于她的人坐过去当一两分钟听众,然后,被友好地赶开。至于托比,也许是借着他饭后的成功演讲,已经在那里坐了好久。
“要是万尼没给他笑粉吃,我倒奇怪了。”
“噢,上帝!”凯瑟琳不屑一顾,转而又笑着说,“你知道他是什么人,他会向她提议‘打炮’——或者,诸如此类的其他说法。”
“她已经喝了不少了,是不是?但好像没什么影响。”
“看那些男人围着她真是好笑。他们带了妻子来,却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看那个,对,握手的那个,‘是,首相,是,是,’却腾不出空来介绍他妻子,显然巴不得她赶快消失,好独自与夫人共度良宵——看,妻子要坐下了,那家伙恼了……噢,她给他出了个难题——他蹲下了……他跪到地毯上了。”
“也许她会让他吻她……”
“噢,当然不会……”
“吻她的戒指,亲爱的!”
“也许吧,硕大无比的戒指。”
“穿着那套衣服,她挺有点女王风度的,对吧?”
“女王风度?得了,亲爱的,她就像个西部乡村歌手。”
凯瑟琳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引得人们纷纷转过身来,他们表情各异,有的是迁就容忍,有的是恼怒不满。她看来还在持续她的尖叫,不过是在胸腔里。她把颤抖的杯子举在眼前。“这些香槟酒杯可真大!”她说。
“我知道,它们可是大号的,不是吗?”尼克说。

公共花园里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焰火声,一时间,炮声大作,雷声隆隆。窗户格格作响,房子里回响着嘭嘭声。人们欢呼着躲闪,首相却没有避让,她把语气放硬了,就像在闹哄哄的议院里挺身面对别人发难一样。在她周围的大臣们像野鸡一样骚动不安。
“实际上,令我吃惊的是,”尼克说,“是那些绅士们的娘娘腔,那种异性恋者们的娘娘腔。”
“我倒希望,”凯瑟琳说,“哦……让杰拉尔德……”
“亲爱的,总体看来,杰拉尔德是个干粗活的,跟这些人相比,他就像个矿工纠察。看看那个老家伙,哦……什么大臣来着?他是管什么的大臣来着?”
“不知道。他是管什么的大王吧。粉红脸,我在电视上见过他。”
那个人站在首相身后,像个正在展览的马戏团老板,并随时随地地保护着她。他不时盯着她的头发看一阵,垂涎三尺。他一头银白色蜷发抹过发油,向后梳成波浪发式,一只手不时向脑后作势地一抿。他是为数不多的穿白礼服的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上衣是奶油色丝织直翻领,一排闪闪发光的蓝纽扣,一直扣到紫色天鹅绒的蝴蝶结底下。硬硬的衣领限制了脖子的转动,使他显出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腹部的紧身装饰丝带使他不得不昂首挺胸,脸憋得更红了。
凯瑟琳说:“没见过任何有自尊心的同性恋穿成那样。”
“噢,我可不会那么过分,”尼克说,不知道他俩到底谁更刻薄。“那只是一种特许的虚荣。”
“他就是虚荣大王,亲爱的!”凯瑟琳说着,又“噢”地大叫一声。
他来到一楼的洗手间,快速吸了一小卷可卡因。似乎没必要偷偷摸摸地上楼。他用拇指轮流按住一个鼻孔吸食,冲着那张杰拉尔德与罗纳德·里根握手的照片傻笑。那老家伙根本不像认识杰拉尔德的样子——他老是露出一副仁慈的样子。外面砰砰响着音乐节拍,刚才还是爵士乐,现在已经换成老掉牙的摇滚乐,可以想见,那就是瑞切尔和杰拉尔德二十五年前伴随着翩翩起舞的那一种。焰火还在劈啪爆响。锁住的门外传来一伙人的狂呼声,其中酝酿着秘密的机会:这里有两个人是他想要的。门把手响起来,他收拾了一下,再检查一遍,冲了冲马桶,对着镜子整了整蝴蝶领结,才慢悠悠地走出来,正眼也没瞧一下等在外边的警察。
公爵夫人已经取代了他在凯瑟琳旁边的位子,于是,他四周看了看。拥挤的客厅就是他的游乐场。他情不自禁而又坚定地朝着首相的沙发信步走去。托比像演员谢幕一样退下来,脸上依然挂着微笑。他不会透露她都说了些什么。帕特里夫人一直在四周逡巡,这时,她欠身握住首相的手,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就像尼克见了他崇敬的作家,除了一句“我喜欢你的作品”,别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一样。可帕特里夫人是个老太太,那智慧的皱纹与母性的骄傲堪与童真的敬畏以及顺从媲美。尼克听不清楚她在说什么……或许是关于垃圾问题?……他可以确定连她自己也没听到首相在说什么,可那无关紧要。她们手拉手,带着敬意,甚至有些和解的意思。这让帕特里夫人兴奋不已,对于首相这却是司空见惯,例行公事而已。她们都醉醺醺的,把手拉来推去,大呼小叫的,像是要吵架似的。首相似在表示她倒愿意吵上一架,那正是她的拿手好戏。因此,当帕特夫人卑躬屈膝地往下退时,她拿起空酒杯砸到“虚荣大王”的腿上。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尼克走过去,半跪着坐在沙发边上,就像戏中人求婚那样。尼克欣喜地盯着首相的面庞、头部、鹰钩鼻和她宽阔的额头。在他看来,它活像是漩涡画派和巴洛克艺术风格的完美而不可思议的融合。她脸上倏地闪过一丝动物般的微笑,一个蓝色而明亮的挑战。那个温柔的注视眨了一次,两次、三次——预示着时机来临。那眼神闪烁不定,似光影变幻莫测。尼克心跳加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脱口说道:“首相,愿意跳支舞吗?”
“你知道,我非常乐意,”首相用坚定的女低音回答。面对匪夷所思的厚颜狂妄,首相身边的男人们一边退让,一边掩住口窃笑。等他与她在人们的战栗和震惊中走出客厅,他听见整件事已经被人添油加醋、刨根问底了。宴会的重心突然转移了,没有谁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效应,也没有一个人能招架得住。他微笑着将视线保持在同一个角度,对那些人视而不见,姿态亲密地陶醉于首相的问话以及自己大胆巧妙的对答。人们簇拥着他们走下石阶,穿过挂着灯笼的长廊,既是围观者,又是陪衬人。“我不大被人邀请跳舞,”首相说,“尤其是被大学老师请。”尼克这才发现杰拉尔德并没完全弄明白:她棋高一招,她有自己独特的洞察力。她对方块图案的墙纸和蓝色大门不作任何评价——她看似什么都没去注意,实际却——记在了心里。
他们踏着“从我的云彩上下来”的旋律,走进镶嵌着木头地板的正厅,客人稀稀拉拉,气氛却很热烈。杰拉尔德正与嘴唇紧闭的詹妮·格鲁姆跳慢步;巴里拥着邦妮在场地里转来转去;瑞切尔神情慵懒地与琼蒂·斯塔福德安静地跳着摇摆舞。这时,杰拉尔德看见了首相。他的偶像,她以前说过不会跳舞,现在,喝过几杯威士忌,居然屈尊与尼克跳舞,而且态度如此亲昵。现在,尼克以前在艾弗森太太那里受过的训练,就像乘法表一样从脑子里蹦出来:步法敏捷,轻握手臂。但他跳得更欢快,感觉自己能在整个舞场里跳跃旋转,让首相在他怀里气喘吁吁。可是,杰拉尔德阻止了这一切。
他们聚到楼上尼克的浴室,他们三个人。万尼又是咬牙,又是抽鼻子,像个打摆子的病人。他双目空洞、面色晦暗、焦虑不安、神情茫然。他说他没事,精神头好着呐。他全神贯注地打开从《论坛》杂志上撕下来的一小片纸,把上面的粉末刮干净。尼克坐到浴池边上,一屁股坐进去,翘着二郎腿,看着特里斯托撒了一泡长长的尿。
“别那样,”万尼戏嘘地说。
特里斯托咯咯笑着说:“他喜欢那样。”
“我知道,”尼克说。
“我想起来在哪儿见过你了,”特里斯托一边说,一边拉上裤子拉链,冲了马桶。他洗了洗手,对着镜子说:“那是在托比先生的生日宴上。在那个大房子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没错,”尼克说。挣扎着起身,脱掉外套。特里斯托也脱去了燕尾服,似乎对他们要做的事心照不宣。如此默契,赢得了尼克的微笑。
“那时你到厨房来找我,我以为你喝醉了。”
“我喝醉了吗?”尼克含含糊糊地说。
“我很抱歉,因为我说了过一会儿去见你,却没有去。”
“我们明白,”万尼说。
“别在意,”尼克说,“我早忘了那事儿了。”
特里斯托一只手搭到尼克的肩膀上,尼克会意地掏出钱包给了他二十英镑。特里斯托把脸偏过来,把他肥硕的舌头插进尼克嘴里,吻了他足足十秒钟,然后拔出舌头,转身走了。万尼忙着对付那撮可卡因,根本没注意他们。特里斯托走过去,俯在他肩膀上看了看,说:“我这样做会有大麻烦。”
“没事,”万尼说,“有警察守卫的房子,那是再安全不过的。”
“对,可我是说老板那里。就一小会儿,对吧?”
“看你喜不喜欢了,”万尼说着,头也不回地伸手在侍者的胯上乱摸。
“我说,你是想多要钱吧?”尼克问。
“我他妈的刚给了他五十英镑,”万尼吼道。
特里斯托趸着步子,又照照镜子。他说:“你没把你老婆带来?”
“他妈的,她不是我老婆,你这个婊子,”万尼乐了。
特里斯托冲尼克咧嘴一笑:“我看见你和夫人跳舞了,”他说,“蹦来蹦去的,我觉得她挺喜欢你。”
万尼头一仰,干笑一声:“下次再见到她,我倒要问问她对尼克意下如何。”
“你是她的好朋友,对不?”特里斯托说着,又冲尼克咧嘴一笑。
“好朋友,”万尼说着,弹了弹他做好的东西。“超级好友……”他转身盯着他们,“你们难道不爱她吗?难道她不美吗?”
特里斯托做了个鬼脸:“是,不错,正合我意。宴会多多,金钱多多,小费多多。一百镑,两百镑……”
“天哪,你这个婊子,”万尼说。
尼克走到水盆那里喝了两杯水。“我需要抽上一支。”他咕哝道。他们现在都充足了电,迫切地要往下做,要借着药力带来的麻木感恢复信心。这个想法超越了快感,像脱缰的野马,它让他们误以为可以选择,可以理智地选择,实质上却已是身不由己。
特里斯托弯腰吸他的那份儿,万尼摸着他的阴茎,尼克摸着他的屁股。“还说是好东西,哪儿弄来的?”特里斯托后退一步,躲开一会儿,大声抽着鼻子。
“从罗尼那儿搞来的,”万尼说。“他叫罗尼。啊,感觉好多了,”他翕动着鼻翼,“我爱罗尼。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惟一的朋友。”
“除了首相之外,”尼克说。
特里斯托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傻笑。他说:“我认为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他,尼克。不是吗?”
“尼克,他不过是个婊子,”万尼说。“他看中的是我的钱。”
尼克从抽了一半的纸条上抬起头。“他意思是说他是我的老板,”他说,带点卖弄的意味。
“他妈的,他干什么活了?”万尼说。
“实际上,这就是我的工作之一,”尼克冒失地说。
“什么?什么他妈的工作?”特里斯托说,笑得像个白痴。
“无论如何,”尼克说,“他是个百万富翁,所以……。”
“我是个千万富翁,”万尼板着脸装腔作势地说,“我现在要你亮出你的拿手好戏。”
“什么拿手好戏?”尼克说。
“等着瞧,”万尼说。
“希望这药没把我的小弟弟弄软了。”
“要是你的小弟弟软了,我就他妈的收回我的钱。”
特里斯托把长裤和内裤都褪到膝盖处,坐在一张小藤椅边上。他硕大黝黑的阴茎松软地耷拉着。他两只手把衬衫卷到肋骨上方,捻着自己的乳头。“你想帮我吗?”他说。
万尼嘘了一声,走过去站到他身后,边用食指和中指掐扭、玩弄侍者的乳头,边俯身看着他。特里斯托发出呻吟,笑着咬住焦灼的嘴唇。他低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那家伙醒过来,膨胀着,懒洋洋地颤动着从大腿间钻出,随着包皮一点点后退,露出了粉红色的微笑。对他来说,这永远都像个奇迹。“就是这样,”万尼说。
“就这个?”尼克说。
“你喜欢吗?”特里斯托说,在尼克眼里,他那张脸突然变得贪婪而陌生。当然,他的那家伙是这个夜晚潜伏的欲念,这一幕陌生情景背后潜伏着的欲念,这个欲念蔓延着,被打了折扣,当最后浮出水面真相大白时却愚蠢无比。
尼克问道:“这么说,你以前就见过?”
“噢,他就想要这个,”特里斯托说。
万尼已经跪到地上,笨拙地想要尽情享用他渴望已久的东西。他已脱下了裤子,可他的那家伙经过可卡因的狂风暴雨式的冲击,已经缩拢了,几乎看不到了。他已经迷失了自我,顾不上羞耻了——这是你花钱自找的。他抽动着鼻子,又舔又吮;晶亮的黏液混合着血滴与没有溶解的毒粉,顺着他的鼻子流到侍者的腿上。显然,侍者本人从没这么干过,他早已从万尼身上了解到其中的利害。现在,他像是对着一群朋友喋喋不休地饶起舌来。他冲着万尼点头说道:“我第一次见他就是这样。在托比先生的聚会上。他让我吃可卡因,而我干他的屁库。”
“他的皮裤?噢,你是说屁股,我明白了。”尼克笑着,搀杂了冷漠的嘲笑,带点调侃,又有些酸楚。他看着那个侍者熟练地把手插进情人的黑色蜷发,显得漫不经心,从容不迫,似乎万尼不是在跟他口交,而只是个漂亮任性的、跑到大人堆里渴望得到夸奖的孩子。特里斯托抚摸他的头发,笑着夸奖道:“他付钱总是很大方。”
“这我敢肯定,”尼克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只避孕套。
“来吧,”特里斯托说。
楼下,首相要走了。杰拉尔德跟她共舞了足有十分钟。他冒雨把她送上车,脸上浮现出晚会成功后亲密而轻松的光芒。焰火还在如枪似炮地鸣放,他们抬头仰望天空。瑞切尔站在门口,邦妮立在她身后。杰拉尔德篡夺了秘密警察的位置,俯身向前把车门关好,幸福而不由自主地掬了个躬。路灯下的雨丝如万千银针般闪烁着,戴姆勒汽车发出一声唐突的叹息,轰鸣着渐渐驶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