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首先,祝贺您的小说《美的线条》(The Line of Beauty)获得了今年的布克奖,大家都知道世界文学大奖布克奖(Man Booker Prize)是英国年度最重要的文学小说创作奖。这项创设于1968年的文学奖用于奖励当年以英文写作的最佳小说作品,可以说在整个英语世界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那么能不能告诉大家赢得布克奖对您意味着什么呢?
霍:可以。这是一项英国最大的,包括奖金额度上也是最为丰厚的奖项,是颁发给用英语写作的小说的最有影响力的奖项之一。大家对布克奖可能也有所了解。它是针对在英国、英联邦及其属地发表的小说颁发的奖项,当然美国除外。可以说这是一个英国文学奖,不针对美国。国际上也给予布克奖极大的关注。我对能获得布克奖感到很荣幸,因为从某种一定角度来看,获奖是相当偶然的。也许五位评委的爱好口味都大相径庭。有一百三十部小说参与评选,评委们得达成一致意见从中选出获胜作品。因此获奖机会是非常小的。我认为能够进入布克奖的最后角逐已经非常满意,当然最后赢得奖项是我的荣幸。不过,我认为不能将赢得这项奖看成是一件至高无上的荣誉,不能把布克奖看成一个有魔力的词,这个态度非常重要。当然,如果我没赢得布克奖,我今天便不会来到上海跟大家见面。但赢得布克奖仅仅意味着我成为了人们新近关注的对象。我的前几本书卖得都不错,但一旦你能进入某一图书奖的最后角逐,书的销售量就会翻上三番,甚至更多。我还不了解我小说的销量情况,但是人们说布克奖会把一个作家捧至完全不同的层次。不光靠英语版本,也靠小说的各种翻译版本。不过,现在切断言尚为时过早。会发生什么我无法预测。不过,获奖至少让一个作家有了一个比较舒服的“栖息地”。
陆:1994年的布克奖颁给了詹姆斯·凯尔曼(James Kelman),而他的书里面因为有很多脏话粗话而引起不小的争议,而今年获得布克奖的这本小说涉及到比较敏感的话题,而且一些描写也比较直露。以此观之,我们想问当代英国文坛的鉴赏品味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
霍:这些年来,英国文坛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1994年,我的小说也曾进入布克奖的最后角逐。那年的评奖就像一潭浑水,评委们意见极不统一。当年评委主席是约翰·贝雷(John Bayley),他是我在牛津大学的导师。那时有传闻说我会最终得奖,但最后还是没能得奖。其中一个原因,有人分析,就是因为我的小说涉及同性恋的内容,那在当时还是有些惊世骇俗的。这些年,情况有很大变化,人们的观念、态度改变了。年轻的几代人变得更开放,更宽容,人们更适应“同性恋”这样的概念,过去存在的歧视态度也没有了。尽管现状还不算完美,但和十年前比起来,已经有了很大改观。立法上的改变也是促进这一变化的一个原因,同性恋者在法律上的地位改变了,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自然也得以改善。现在内阁大臣如果是同性恋,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被迫引咎辞职。今年获奖的这本小说若放在十年前也许处境就不同了。
陆:保罗·莫内特的作品《成为一个男人》,关注了一个同性恋男子成长的困惑抉择,该作品在1992年就荣获了美国国家图书奖。而今年您的获奖标志了布克奖三十六年历史上第一次以同性恋为题材的小说获奖。这意味着什么吗?
霍:在美国,同性恋这一话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更为政治化,我认为在美国,人们为同性恋的权益等问题进行了长期斗争,而且要远远比其他国家规模来得大,更戏剧化。而且在美国,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也都更为政治化,这也许是由他们的性格、宪法和社会生活方式决定的。英国是个独特的王国,它是个岛国,它的宪法也不同于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一讲到权益问题,对美国人来说它们立即变得无比重要。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便发生过许多为同性恋争取权益的斗争。而且美国有许多以同性恋为主题的作品,它们都要比在英国发展得早,而且更完善。
陆:英国著名作家福斯特(E.M.Foster)1913写的颇具自传色彩的小说《莫理斯》(Maurice)也是关于同性爱,阶层等主题。这部小说对您有影响吗?
霍: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以前没有人问过我。当我还在牛津读研究生时,研究过一些同性恋作家,他们当时都无法公开描写或发表关于同性爱主题的作品,并在此基础上写了我的论文。福斯特就是其中之一,大约在二三十年前,我对他很感兴趣。《莫理斯》是一部很勇敢的作品,尽管我不认为它写得特别出色,但是小说非常有意思,很能给人启发,而且我认为故事相当感人。在这部小说中,一位相当严肃的英国作家试图公开地就这一题材进行写作,这是文坛上的第一次,不过他当然无法发表这部作品,至少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莫理斯》的发表。也许从一定程度上说,这部小说一直存在于我的潜意识里。我是指,在我的前几本书中,我已经涉及到了同性恋的主题,我仍记得在我写第一部小说《游泳池图书馆》时,我试图以作论文时的主题为基础,我有意识地想谈谈当一个人无法公开谈论某话题以及能够谈论该话题时的意义。我当然也知道我无法完全无限制地描写同性恋,他们的作品,挣扎和喜好。当人们可以恣意写作任何他们喜欢的主题时,那些主题同时也就变得不那么吸引人了。在我的第一本书中,我试图拼凑出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年轻人的生活,有些享乐主义似的生活。他在生活中经历了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遇到的各种问题,各种压力,又都是非常苦涩的。我试图探索莫理斯的世界和现在这个世界的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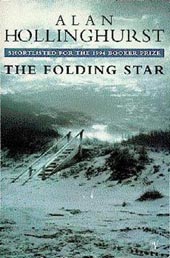
陆:在过去,如果同性爱在小说中被涉及到了,那它或是被抑制住,或是像编码那样隐藏在小说中,但是您的写作环境已经大为不同。比如奥斯卡?王尔德和您读的是同一所学院,但是您能够比他更公开地选择写作的主题。您对这一变化是如何看待的?
霍:我认为这一变化非常好,十分受人欢迎。奥斯卡·王尔德就像一名同性恋的烈士那样声名不朽,当然作为一位作家,他也永远为人铭记。他那时处于一个很困难的时期,而且一直到二十世纪后期,同性恋在英国的日子都很艰难。当然我是指在法律上合法化的这一方面,直到1977年局势才得以改变,因此1977年是个转折点。不过在那个年代,文学上并没有多大变化。当我在1984年开始创作我的第一部小说时,我的题材还是一个全新的主题,对我来说,更可贵的是这一题材并没有被文学理论讨论过。那一时期注定要产生变化。在多年来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看法有很大的改变,而且在那以后的二十多年来同性恋在英国的法律地位上也有改变。每个人都更习惯这一概念,很多人都生活在这一新的时代,而人们的态度都得以改变。因此,现在这一主题没有以前那么吸引人,但是对于我来说,二十年前我还十分兴奋能就这一主题进行创作。现在人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与这些变化相比,在文学中这一主题占的分量还是很小的,也许那些争取权益的运动也产生了一种迫切性,让它能以文学的形式发展起来。
陆:我看了一些评论性文章,许多都将小说简单化地说成是同性恋小说,由此为您的小说贴上了这一标签。但是我读了以后,我看到书中大部分内容是关于文化,社会阶层,美学等主题,并不单纯的是关于同性爱。您为何选择同性恋这样一个切入点,您将这么多层面的内容融合在一起想传递给读者什么信息呢?
霍:选择这一切入点,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与生俱有的。在早期我就决定了我要从这一个位置来进行创作,我不必为此向任何人道歉,也不必做任何解释,因为这就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是我希望进行创作的一个角度。但是我还是得承认,当我读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时,我觉得以这一角度写作在当时的确有些不俗。于是,我就延续了这样一种创作的角度,而且我一直希望从这一角度写作能像从异性恋的角度写作一样让人感到自然。不过我很高兴听到你说书中还有其他许多有趣的元素。当媒体开始关注一本书时,就像这本小说获奖后那样,贴标签的现象就难以避免,因为批评家们得用一个短语概括一本书,而且人们都会使用那个短语,就像他们评论我的小说时说的那样:“同性恋小说获布克奖”。他们不会说“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为背景的小说”或者“关于古典音乐的小说”,因为这样的短语不够醒目,无法娱乐读者。我总是想让同性恋的主题成为我写的每一本书的前提。当然,在同性恋者的生活中,许多方面都具有“同性恋”的特征,在其他人眼里也许是非常特殊的。我在写书时,总想写关于历史,文化,艺术,音乐,阶层,种族的话题,我感兴趣的话题数不胜数,但是我从来没有,至少我认为我没有通过我的书为读者传递任何信息,我更希望让我的书成为一幅复杂的图卷,读者看了以后能进行独立思考,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我不想去影响读者的判断。
陆:当您写这部小说时,您有没有担心读者会有何种反应?因为小说涉及到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当您写作时,您有没有想到过小说会引起怎样的反响?
霍:我从没认真考虑过这方面。我不喜欢为了迎合某种特别的期望而写作。我在写作时,非常努力地排除杂念,我完全不会去理会人们希望从我的小说中或从我这儿看到什么。我写作是为了让自己满足,是为了解决我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无可否认的是,一个人的思想肯定或多或少地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但至少那些影响还没有大到让我能意识到的程度。
陆:有些作家很在意文学评论家的看法,他们也会受文学理论的牵制,您是怎样的呢?您写作时会不会受文学评论家看法的影响?
霍:我从来不会受文学理论或评论家的影响。我一直很庆幸自己大学毕业的正是时候,因为我读书时还没有刮起学习文学理论的风,我们从来不讲解构主义等理论。我生性就不适合研究那些概念,我从来不对那些抽象的想法或理论感兴趣。我当然不光对物质层面感兴趣,我也对情感或心理上的层面有兴趣,但我从来不爱理论。我同意你的说法,是有一些小说家,有些人也有学术背景,过多地受到了理论的影响,不过我从没对此妥协。
陆:我想知道您是否将自己的经历融入到小说中。当人们评论一部小说时,有时会说小说是自传性的。在您的小说中,主人公就读于牛津大学,论文是写亨利?詹姆斯,这跟您有相仿之处。那我们是不是能说小说中有您自己的影子?
霍:我一直认为作为小说家的一大乐趣就是你能创作一个你的世界,你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你能写你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你能抒发你的热情。我的确有这个倾向,我喜欢让我的主人公继承我的兴趣喜好。我年轻时非常喜爱音乐和建筑,我曾想成为一名建筑师,尽管没有继续沿着那条路继续走,但我仍然非常喜爱建筑,我爱为我的小说设计房屋。也许你读我的作品时,有时会感到厌烦,因为连续三页都是关于建筑物的描写。因此我会让笔下的人物体现我的一些兴趣。不过,我认为创造人物和表达自我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文学中创造的人物总会和现实有些距离,我是要为人物创造一个独立的位置,而不是完全对我自己的模仿。我从没有写自传的感觉,我也从来没写过我自己的生活。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的生活和主人公完全不同,当然我也庆幸我过着不同的生活。我那时非常忙碌,也很勤奋,白天工作一天后晚上写些东西,虽说我的生活也不算无聊,但绝对不像尼克那样生活中充满了狂乱的刺激。也许其他小说家也是这样,至少我写作时,我自身的一部分进入了另一个角色,有点像把自己戏剧化的感觉。因此我认为讲到小说时,自传性是个非常难以界定的概念。
陆:在《美的线条》中,艾滋病是其中的一个主题,为什么您在这部小说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但在前几部作品中,比如The Folding Star和The Spell,都没有涉及到这方面?
霍:那时艾滋病刚开始蔓延,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那时我不知道我在小说中该如何谈论这一问题,因为我没办法保证对这个问题在写作时用艺术手法来处理。当时一下子涌现了许多书,都与这个主题有关,不过说实话,并不是每本书都写得那样好。我坚持直到我有合适的构思,合适的主线,我才会在小说中融入这一主题。我感觉到有许多人期待我会写关于艾滋病的小说,但是我一直拒绝这种外来压力。
陆:您并不想单单为了宣传预防艾滋病而写一本书,对不对?
霍:对。我的看法,或我的小说并不是宣传的媒介。也许有些作品,甚至有些小说的确有政治效应,但我认为我没有天赋写那样的文字,我无法像一位报纸撰稿人那样写作。在我眼里宣传性的文字和小说是判然有别的。因此,在早先我写的两本小书中,我没有涉及艾滋病的问题。我认为有些事情得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得过了十五、二十年再回过头来看,而不应在当时就简单地描写那些事。我现在能够坦然地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末期艾滋病爆发的那个阶段对英国有很大的影响,我能够将这一问题和历史建立起联系。我感觉到那一历史时期,或那个主题能够自然而然地融入我的故事主线,无需我的解释,大家都会自然地接受这种安排。我相信许多读者本身也很了解那一时期存在的社会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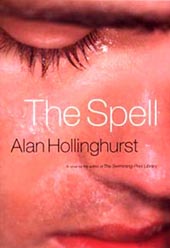
陆:这部小说很特殊的一点,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社会政治背景贯穿了整个故事。撒切尔夫人对故事里的人物和故事发展从始至终都有着很大的影响,甚至她本人都出现在故事场景里。许多中国读者也许对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的政治社会不那么熟悉,有些人只能将撒切尔夫人和香港回归联系在一起。您能告诉大家为何选择那段历史和人物作故事背景吗?
霍:选择那段历史作为背景主要是因为在那个时期,英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每个方面来看,那都是一个充满活力,变化迅速的时期。那个时期,包括它的新经济政策,都对后来的英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那时,新财富,或说是新兴财富势力的出现是爆炸式的,这也造成了社会组织构成的变化。新财富出现的代价是上百万人的失业,新财富带来了新贫困。从一定程度上看,原来的社会机构开始瓦解。那也是一段社会非常多元化的时期。那段时期对英国现在的社会生活仍有很大的影响,那是一段能让人好奇的日子,至少这是我的感觉。我的第一本小说背景设在1983年,那比这本小说故事发生的年代稍早几年,我总是忍不住想回过头去看看那时发生了什么,我十分迷恋那段历史。
陆:在您的前几部小说中,您有没有写到政界人物或者公众人物?
霍:没有。
陆:那么这部小说为何会涉及到那么多政界要人?您的小说是否受到过托利党人的抗议?(大笑)我这么问,是想知道作家的写作自由会不会因为小说中涉及了真实人物,尤其是政界要人而受到限制?我猜想这要比写纯虚构的人物压力大得多。假想您笔下的议员是当今工党的要员?
霍:其实,小说中除了撒切尔夫人,其他政界人物都是虚构的。我以前从没写过直接与政治相关的小说。我的第一部小说的背景是1983年的夏天,但是,小说中找不到任何当年大选的痕迹。这部小说中是有一些政治元素融合其中,实际上,也是非常含蓄的。之所以涉及政治,也是因为写的这个同性恋题材涉及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且,在写这本书时,我想公开描写这些性恋者同生活、社会以及政治力量的关系,但与此同时,就像亨利?詹姆斯那样,他虽然喜欢写有钱有势的人物,自己对却金钱、权利丝毫没有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那些东西,那些人对他笔下的人物产生的影响。同样也是这个原因,我在小说中涉及到些政界商界的人物。我当然不是要写政治或者股票市场是如何运作的,我感兴趣的是在那些世界里的人物,他们的想法。另一位对我有影响的作家是屠格涅夫,比如在他的小说《父与子》中,他很直接地描写有政治思想的人物。当然他写很多政治小说,他也很擅长描写特定的政治气氛下的人物。
陆:小说《美的线条》的卷首语用了《爱丽丝漫游奇境》第十二章里的一段话,为什么您选择那段话开始您的小说?您想对读者造成何种启发?
霍:说实话,我不知道卷首语的作用是什么,几乎每本书都有,但我不知道它们的目的是什么。也许共有的一个目的是迷惑读者,让他们不得其解。我认为我的故事带点爱丽丝进入奇境的色彩,爱丽丝的故事里,她进入了一个奇怪的世界,那个世界只根据它自己的法则运转,而爱丽丝也琢磨不透那些特有的法则。我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尼克也像那样,他寄宿在同学家,而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政要,他们的社交圈在尼克眼里也是光怪陆离的,有他们自己的法则,尼克根本无法把握他们的法则。而且引语中关于“什么是重要的,什么又是不重要的”问题也非常有意思,这个问题出现在对爱丽丝的审判中。我认为这非常有哲理。国王说那是很重要的,经白兔子提醒后他又改口说是不重要的,结果他也分不清到底那重要不重要。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非常适合我的小说。一些尼克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事,在他的房东和其他人眼里丝毫没有意义,但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对尼克来说又是无关痛痒的。生活中究竟何为重要,何为不重要,我想通过卷首语来提出这个问题,也希望读者能为他们自己考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