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德烈·马尔罗、杜拉斯、奥威尔、奈保尔,四位的品性和人生履历差异很大,甚至完全不同,将他们归类并列有点滑稽。但,他们有相同之处,他们同是作家,欧洲作家,前两位法国,后两人英国(只是奈保尔的身份有点暧昧),他们又都来过远东,或旅游或生活,或探险或谋职,或一别不再或三番四次恋恋于此,为此,他们都作了著名的文学陈述。
有很多世纪,远东对于西方人是难以挥却的梦,是神秘的土地,是深邃玄妙的思想之井,是乐土,也是战场。借着坚船利炮,西方冒险家们蜂拥而至,索取、拥有、享乐、糟蹋,跟着而来的是文化使者,他们的目的与手段,似乎比较高尚,他们带来文化,也汲取文化,他们是文化考察者与传播员,他们力图做文化杂交的实验,他们的名字是吉卜林、康拉德、福斯特、毛姆、黑塞……
我选择的四位也应该在这个名单里面,不过,我觉得他们更特殊,他们与远东纠缠得更深,他们的生活和文学语境更复杂,他们离我们更近。
马尔罗:从偷盗文物到办报纸
安德烈·马尔罗:诗人,小说家,新闻工作者,艺术家,史学家,文化官员,对了,他还有个头衔:冒险家。马尔罗是颠覆者,不仅勇于颠覆传统的资产阶级的习俗和观念,他还敢于开自己的玩笑,将个人的前途押上命运的赌桌,他常常以天真的姿态戏弄命运!他的一生,一半是文学,另一半是传奇,即便是文学,也淋漓尽致地染上了传奇的色彩,他的很多作品都来源于冒险的经历,冒险是写作的灵感。因此,我们可以略带夸张地说,马尔罗光辉的文学事业起步于远东,在此之前,他还只是文学学徒,正是在远东的历险,在远东所遭受的东西两种文化的挤压撕扯和政治波澜,使他这么一颗年轻的浆果愈加成熟,愈加饱满,充溢着思想与文学的汁水,浆果终于爆裂……
1923年,22岁的马尔罗和年轻美貌的太太克拉拉出现在印度支那。他们的目的不是旅游,不是很“秀”的“文化苦旅”,也没有公干,他们的企图有点卑鄙,与崇高的文学无涉,听听克拉拉的自白:
“那么从暹罗湾到柬埔寨,沿着从扁担山脉到吴哥的‘王家大道’,有一些很大的寺庙,它们都上了文物保护的清单,但一定还有一些寺庙如今尚不为人知……我们到柬埔寨的某个小寺庙里拿走几件雕塑作品,然后在美洲把它们卖掉,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安静静地生活上两三年……”
这岂不是偷盗文物?事实就是如此!这对结婚不久的夫妇能够扮演各种反差极大的角色:他们能为卢浮宫学校做讲座,能讲酒吧里的语言,能下愚蠢的赌注,能摆设圈套。现在他们居然要偷盗异国文物去了,真是敢想敢为。不过,他们之所以出此“劣”策,也实有苦衷。此前两年,两人投身于股票交易,将全部财产都变成了证券,他们冀望财产像正在充气的球一样迅速膨胀,为他们漂泊的艺术家生活和从容的环球旅行提供结结实实的保障,这也是投机和冒险,马尔罗喜欢这样,有时候,他觉得自己真有点像个百万富翁。

打击,沉重的打击!覆水难收!他们破产了。
于是,他们把淘金的目光移向了神话般的远东,这对夫妇还是老脾气,总想一鸣惊人,又没耐心做持久的努力。
《王家大道》有着明显的自传色彩,马尔罗通过其中的克洛德说话。
克洛德:在从老挝到大海途中的森林里,有不少欧洲人不知道的寺庙……一尊小小的浅浮雕,随便一尊什么雕像就值三万多法郎……一尊浅浮雕,只要漂亮,比如说一尊舞女雕像,就至少值二十万法郎……
佩尔肯:你肯定能卖掉它们吗?
克洛德:肯定,我认识伦敦和巴黎最有名的行家,搞一次公开拍卖并不难。
佩尔肯: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危险的尝试呢?
克洛德:我可以回答您,因为我几乎已经没钱了,这是真的……在贫穷的重压下,我已别无选择。
贫穷是一个难以驳倒的借口。10月13日,这对夫妇登上了“吴哥号”轮船,驶向柬埔寨。1923年底,马尔罗和克拉拉出现在“王家大道”上,他们戴着头盔,身穿粗布衣,背着像机和水瓶,骑着矮小的马,四辆由水牛拉着的车笨重地跟在他们后面,十二个苦力陪伴他们同行。马尔罗觉得自己的好运气来了。三十个小时跋涉之后,他们果然在荒芜的山林里发现了一个倾颓圮的寺庙,梦寐以求的石雕就在眼前。
到处是石头,有的平躺着,整个一角几乎面朝天:这里荆棘丛生。一些紫色的陶土墙面上或者饰有雕刻或者没有,上面悬吊着蕨草;有的墙上有烧制时留下的古红色……坍倒的石墙下面是一些远古时代的、印度风格非常浓厚的(但非常美的)浅浮雕。
装车,赶快装车,然后,踏上归途。他们雇了一条船,准备将文物运出湄公河。12月24日子夜,马尔罗正在酣睡,一定是一场好梦,突然间,他被人粗暴地叫醒了,是三个警察,他们带了逮捕令。马尔罗被扣押了,这时,他对妻子说了这样一句话:“有了这次教训,下一次就有了成功的一切保证。”
马尔罗还算是幸运的,克拉拉迅速回到巴黎,运动了文学界的著名人士,他们愿意为马尔罗的聪明才智和文学价值作担保,1924年11月,马尔罗自由了,他回到了法国。
但是,仅仅过去几个月,人们又在印度支那看到了马尔罗桀骜不驯的身影,是的,他又回到了印度支那。这就是马尔罗,百折不挠的马尔罗。不过,这次他不是为文物而来,而是为了一项正义的事业,他要在西贡办报纸,传达公正的声音。当时的印度支那是法属殖民地,法国统治阶层不仅专制,而且腐败,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充满了苦难和灾难。偷盗文物应该看作是马尔罗一时误入歧途,当他归正的时候,胸中又涌动着勃勃然的正义感。在过去一年的官司中,马尔罗已经感觉到了统治官僚的愚蠢、冷酷、腐朽。其实,在马尔罗自己看来,前后两次的历险并不像表面看来那么反差巨大,窃取文物是为了赢利,有了钱能够从事艺术和公正的事业,两者是鸡和蛋的关系。
马尔罗的报纸办出来了,名叫《印度支那报》,犀利是马尔罗的一贯风格,他大声疾呼,慷慨陈词,为“土著”的印度支那人讨公道。他向总督科尼雅克发起猛烈进攻:“您想独揽大权,为所欲为,这是办不到的。你只不过是孤家寡人,法国人民同印度支那人民站在一起,他们将审判您!”也就在这个时候,马尔罗接触到了印度支那的共产党人,这种接触在不久以后就有了文学和思想的果实,《征服者》和《人类的命运》两部小说的灵感就来源于此。马尔罗曾夸张地说过,这两本书是“亚洲革命的新闻报道”。当然,马尔罗的这次历险又失败了,在总督的压迫之下,报纸办不下去了,马尔罗只得又启程回国。

杜拉斯:湄公河上的““情人”
玛格丽特·杜拉斯出现在越南,不能说是自觉的选择。是的,她就出生在这里,时间是1914年4月,她的父亲是中学数学教师,母亲是位不引人注目的小学教师。他们是法国子民,在这里,他们是入侵者,享受着入侵者的优厚待遇。
然而,在杜拉斯7岁的时候,父亲病逝,大厦的顶梁柱折裂,风雨飘摇。小孩子们却觉得并不坏,他们不需要维持资产阶级装模作样的面具,可以自由、野蛮、冒失而无拘无束地生活。他们同土著的孩子一样,爬树、摘果子,撕破了衣服,尽管母亲责打、训斥他们是“肮脏的小越南人”,可他们依然我行我素。杜拉斯的童年就是这么度过的。
母亲是倔强的,她要自立,要有自己的土地养活孩子。她投入了全部积蓄,向殖民总局提出购地申请,她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她们家在海边有了一块二百多公顷的土地。平房盖好了,水稻种上了,绿浪滚滚,一望无际,收获在望。不曾想,太平洋的潮水涌来了,毁坏了稻谷,冲走了房屋。母亲不认输,又种上了稻子,可潮水像甩不掉的噩梦一样,又来了。很显然,他们家是受骗了,殖民当局里的坏蛋卖给他们的是一块根本无法耕种的土地。很多年之后,杜拉斯写了《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表达了对母亲的复杂感情,有敬意,也有埋怨,母亲带给他们的是一种动荡不宁的生活,她不喜欢母亲的“专制”。
杜拉斯长到17岁上,顺利通过了中学会考,她要到西贡读书去了,她跨出了门槛,自由了。自由带来了遐想,带来了可能,她期望用女人的心思和肉体,邂逅种种可能。
生命中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她度完假回学校,在轮渡上,湄公河是古老的,怪异的,也是丰富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与湄公河热闹无比的景象相比,这里的场面是独一无二的,黄种人和白种人,富人和乞丐,汽车和手推车,都装到同一条船上。对比与混杂产生了奇异的趣味,杜拉斯知道,她一生都不会再看到如此神奇的河流,她没想到的是,这一次旅行对她一生有多重要。一个男人从黑色轿车中走了出来,他是中国人,手上戴着钻石戒指,一个百万富翁。他走上前很自然地跟杜拉斯攀谈,谈巴黎,是的,他在巴黎学习过,他怀念法国的生活。他是杜拉斯期望中的男人吗?可能是。他姓李,李云泰,一位达官贵人家的三公子,继承了父亲的全部财产,他的居所如王宫一般,却又没有纨绔子弟的轻浮,他文质彬彬,是绅士。这个人会给杜拉斯期望的一切:金钱和做女人的体验。命运已定,在所有的人选中就选择他吧,她跟随着李,无需再去等待,无需在踌躇中感到不安,终于盼到少女时代的结束。他们在堤岸一个无名的包房里做爱,杜拉斯对此感觉很好,但又无法理清这种错综复杂的情感,几乎没有语言交流,没有誓言,没有许诺,正是肉体的力量使他们完全沉浸于享乐中。爱情在一年半时间里秘密进行,没有节外生枝,保持着原始的朦胧状态。
这段故事是刻骨铭心的,杜拉斯永远也没有摆脱它,也不愿意放弃,她始终珍藏着,她反复用文字呈现这个故事,久久回味。到了1984年,杜拉斯70岁了,她仍不忘记朝花夕拾,写出了《情人》,回忆与情感的闸门彻底打开,她不再需要隐瞒,不再需要文学的矫揉造作,杜拉斯说:“这时没有任何编造的东西,甚至没有编造一个逗号。”
童年,少年,印度支那,是杜拉斯一生的灵感。

奥威尔:缅甸的警察生涯
奥威尔19岁,从伊顿公学毕业后,去缅甸做了五年警察。在当时,这还算是比较体面的职业,年薪444镑,另有奖金。年轻的奥威尔对缅甸之行满怀憧憬,他以为这将是精彩的冒险经历。(虽然,他出生于孟加拉,但,一岁多的时候就离开了,几乎没有任何记忆。)
没想到,等待他的是孤独、痛苦和内心的矛盾。
1922年10月27日,奥威尔乘坐“赫里福德郡”号轮开始了从肯伯郡到仰光的30天航程。这对于他并无任何浪漫,更无艳遇,他的目光偏向了另一面,船是一个微型的殖民主义世界,他看到了工人的悲惨状况。有一天午饭后,他惊讶地发现一个低级工人在甲板上疾跑,为的是藏起一块偷来的奶油布丁。这一幕就在眼皮底下发生,是那么具体,那么触目惊心,“这比我从六七本社会主义小册中学到的更多”。
船到达锡兰后,冲入视野的是野蛮的暴行:
我乘坐的班轮停泊了,照例有一大群苦力拥上船搬行李。几个警察——其中包括一个白人警官——在监督他们工作,有个苦力笨手笨脚地搬起一个长长的铁皮标准箱子,以至于险些碰到人们的头,有人因为他不小心骂了他,那位警察眼一扫到这个人的动作,就在他屁股上狠踹一脚,踹得他从甲板这边摇摇晃晃冲到那边。有几个客人——包括女乘客——低声表示赞许此举。
奥威尔心生同情。他苦涩地预先感受到了他的警察生涯将是如何,他也看到了英国官员和平民的道德蜕化,他能避免这种蜕化吗?他没有很大的把握。
当时的英国虽然控制了缅甸,但这是武力控制,毫无民众与社会文化基础,一柄剑孤独地插在广袤的土地上。白人在这里孤立、无聊,他们被迫挤在白人俱乐部里打发时间。奥威尔后来在《缅甸岁月》中写道:“彼此极看不顺眼的人们夜复一夜地碰头,不顾一切地努力忘掉他们自身生活中的无聊……这间俱乐部不止是个娱乐的场所,而且是一种团结的象征。”奥威尔的笔调明显带着嘲讽,他不喜欢这种相互安慰的方式,讨厌虚伪的社交,他常常郁郁寡欢,一人独处。
毛姆先生,这个有钱名流于1930年途经仰光,他不像奥威尔那么偏激。他在这里完成了一次愉快的社交活动。他觉得那“是一种惬意的生活,在这间或那间俱乐部用午餐,在宽阔齐整的道路上驾车,在这间或那间俱乐部打牌,喝杜松子酒或苦啤,很多人穿着粗斜纹布或茧绸衣服,愉快欢畅地交谈,然后又在夜声下回家穿好赴宴服装再出去,再跟某个好客的主人一起用餐,喝酒后酒,用丰盛的大餐,放唱片跳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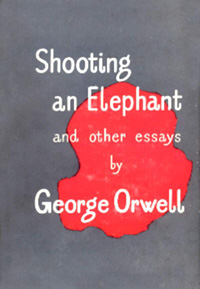
同是作家,想法却是如此不同。不过奥威尔也有“蜕化”的迹象。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学会了毫不客气无节制地使用缅甸仆人。他把衣服和烟蒂都往地板上丢,让仆役捡,还让他们为他穿衣脱衣(吉卜林甚至训练其仆役学会在他睡觉时为他刮脸)。后来,奥威尔写过一本书:《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他对“我在暴怒时用拳头打过仆人和苦力”表示悔恨。
去缅甸前,奥威尔肯定是处男,到了缅甸后,虽然他一再念叨“社会良心”,但他一定去过码头区的妓院,排遣孤寂,他跟一个缅甸女孩有过一段私情。奥威尔喜欢虐待自己的肉体,可他不是寡欲的清教徒,在不长的一生里,交织着不少女人的故事。
关于在缅甸当警察的经历,奥威尔写过两篇重要的随笔:《绞弄》和《杀象记》,这两篇文章相当坦白,是自传性的,是对五年警察生活的反思与总结,也是政治告白:表明他与殖民制度脱离了关系,为他认为是自己罪咎之事赎过。
《绞刑》是奥威尔的第一篇出色作品,它记叙了一次讲究仪式的处决。描写很细致,从被绞者表情动作的细微变化到行刑者的紧张不安都一一毕现,奥威尔说“我认识到看到将一个生命正当盛年令其中断一事的不可理解及错得可怕之处”。他明确地表现了人道主义观念,并以此成为他所有作品的特点。
《杀象记》也是关于一次未必正常的杀戮,但此次的受害者是头大象。正是奥威尔向它下的杀手。在缅甸,发情的大象有时会在街上及市场上乱跑,当地警察必须将其打死。那是一头4吨重的大象,已经因发狂而闯了祸,将一个苦力踩到了脚下,年轻的警官带着恐慌与负疚,取了杆猎枪,第一枪就击中,然后一直开枪,直到把子弹打光。这场杀戮是勉强的,很大程度是为了显示英国警察的权威,奥威尔感觉到自己已成了“野蛮人”,是粗暴的殖民主义政策的执行者,这么做对吗?
1927年,22岁的奥威尔回到英国,他辞去了待遇优渥的警察职位。
奈保尔:离印度很近又很远
奈保尔是西方作家吗?不是,也是。
说不是,理由很靠得住,奈保尔祖父以上都扎根于印度,是纯粹的东方人,1880年,祖父作为契约劳工才从印度北部漂洋过海,移民加勒比地区的特立尼达岛(位于向风群岛最南端,委内瑞拉东北部海岸外),奈保尔是在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长大的。如果奈保尔像我们一样,要在官方文件上填写“籍贯”的话,他只能写上“印度”二字。

但,奈保尔又是难以质疑的西方作家,至少他是用西方(更准确说是英国)的眼光观察人、物、事件,他的作家梦是在英国实现的,他所装备的文学武器也是从西方的文学仓库里挑选来的。在13岁之前,他就已经记得很多英国文学中的片断,它们主要来自莎剧《裘力斯·凯撒》、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和《大卫·科波菲尔》、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印度的记忆和理解得自于童年时代家里的一些物件摆设和游戏般的宗教仪式,这只是些碎片,是一些七零八落再也拼凑不出一幅完整画面的碎片。其实,他更多的印度印象来自于英国作家(毛姆、艾克利和奥尔都斯·赫胥黎)笔下的印度,这是苦涩的荒诞:一个印度的后裔,居然要借助西方的透镜去观察自己的祖国!这种透镜是有偏差的,歪曲的,所以,1964年奈保尔在访印游记《幽黯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中承认,印度对他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个有形的世界,因而从来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它远离特立尼达,是个存在于虚空之中,没有具体历史的国度”。1956年,他与牛津同学英国姑娘帕特里夏·黑尔结婚,这个婚姻是有象征意味的,是一种姿态,奈保尔背向印度,面朝英国(西方),虽然他的心仍在漂泊,但我们不得不把他看作是一个“西方作家”。
1962年,奈保尔已在英国确立了作家的地位,他不再需要心无旁骛地盯着一个目标埋头苦干,他要放松些,要走走看看,拓展视野。他“寻根”去了,从孟买、德里、加尔各答,再到他外祖父的故乡。他是不是有点锦衣归乡的感觉,可能有点,一路上,他都是以作家的身份(英国来的作家!)同人打交道,是的,他还有个漂亮女伴,这多少有点炫耀的成份。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他走的是“寻根”之旅,他说:“如今,在我个人的这趟印度之旅中,我会发觉,我们家族的迁徙和转变——从印度北方邦东部,漂洋过海来到特里尼达——到底有多彻底,究竟能不能再回头。”看来是不能回头了,风筝已经断线,英国文化将奈保尔武装到了牙齿,他的目光是西方式的,这种目光又与康拉德、福斯特、毛姆等人不同,后者自然是坚固的西方中心观念,可他们又痴迷于东方的神秘,而奈保尔的血缘来自印度,他对印度文化没有起码的好奇与惊诧,他的目光赤裸裸的尖锐,如利剑一般斩断回归之路。
真是不凑巧,奈保尔刚到孟买就遇上了糟心事,他带的两瓶洋酒被海关扣押了,孟买有禁酒令。于是,他费了几天时间,同臃肿、懒惰、推诿的印度官僚部门打交道,这两瓶酒总算索要了回来。这就是印度,奈保尔刚刚与之打交道的印度,一个不好的兆头。
然后,奈保尔看到的是一连串的贫困、丑陋、腐败、堕落、肮脏。他感到的是震惊、愤怒、疏离、鄙夷与失落。在外祖父的故乡,他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但这种热情是有企图的,他们希望从奈保尔那里得到各式各样的帮助。所谓的乡亲也是这么功利。奈保尔受不了,他开始奔逃,匆匆地、草草地结束了第一次印度之旅。这次旅行的记录《幽黯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是尖酸刻薄的,缺乏同情与体谅,可以归入丑陋系列,他写的是“丑陋的印度人”。
奈保尔就这么简单地逃离了印度吗?没有。1975年在甘地夫人颁布“紧急状态”令前后,他又来了。他愿意稍稍深入一步,不再是仅仅看风景,他要揭开现实的表象,去看看真实的印度。他交结朋友,走进当地人的家庭,考察政治经济制度和科技状况,他发觉这个印度是几千年的宗教文化、种姓制度、甘地主义等因素共同影响塑形的结果,它有独立、政治民主、现代技术的外壳,但内部还是很空虚无力。
第二次的探访也没枉费,他写了《印度:受伤的文明》,他写道:“印度于我是个难以表述的国家。它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为我的家,而我对它却不能拒斥或漠视,我的游历不能仅仅是看风景,一下子,我离它那么近又那么远。”面对印度,奈保尔不断在调整焦距。
1988年,奈保尔把焦距调得更近了。他又一次走上印度的土地。在孟买一下飞机,他看到了一场庞大的集会,是一群贫穷人的聚会。敏感的奈保尔立即判断出这是印度的新风景,是低级阶层的民主自觉。以后的日子里,他聆听记录了各方人士的叙述,他感觉到印度的弱势群体也发展出了集体归属感和政治意识,虽然,各阶层之间有矛盾有斗争,但,正是这种多样性使印度开始出现活力。
奈保尔越来越耐心,越来越善于倾听,越来越抵达印度人的心灵,《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是他的第三次游印记录,也是一部由印度人口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