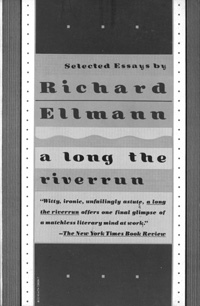
像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 那样沉默寡言的小说家很少见。尽管他在写给一位青年雕塑家的信件中透露出同性恋的倾向,但我们无法肯定他们是否真的有过通常意义上的性生活。许多作家以放任著称,詹姆斯则似乎因谨慎而扬名。相比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作家,例如英国的拉斐尔前派及其后继者,法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和颓废派诗人,詹姆斯鹤立鸡群,因为他从无绯闻缠身。谨慎不但是他个人生活的最大特点,而且也体现在他的文学自信心上。他那洋洋洒洒达数卷的自传、他的信件和他撰写的前言只是隐隐约约地透露出自身艺术的主要动力和源泉。
1873年,亨利·詹姆斯迎来了诗意的人生的第三十个年头。他决定做一点以前从未尝试过的事情。他准备写首部长篇小说了。正因为如此,他酝酿这第一部长篇——《罗德里克·赫德森》(Roderick Hudson)—— 时所花的那几个月时间具有特殊意义。詹姆斯相当直率地承认,叙事的“萌芽”源于一次晚宴上偶遇的安斯特鲁瑟-汤姆逊夫人(Mrs. Anstruther-Thompson),但他不肯透露是什么学究式的冲动促使自己着手创作。要了解这个,些微的暗示都可能有用。而在他于1873年5月31日写给哥哥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的信件中就有这样一个暗示。当时他住在佛罗伦萨,那天在一家书店的橱窗里看到了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的新作《文艺复兴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就在那一刹那间,他像被“火焰烧灼一般”地想买下这本书,然后写上一份短评。然而,他又写道,他意识到自己对该书所讨论的一些问题一无所知,所以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他表示,无论如何,自己都会写些不同的东西。
亨利·詹姆斯的回信给人的印象是他从未读过那本书,只是透过橱窗瞄了它一眼。但事实上他一定进过书店并且翻阅过它,否则他不可能知道其中的内容对他来说是陌生的。既然有证据表明,他要么当时当地就买下了该书,要么后来才买,甚至还写过短评(尽管这份短评从未付印,并因此佚散),他的沉默就暗示了作家的“国家机密”,一种避免承认该书对自己的震撼的习惯性谨慎。我认为,这本书对《罗德里克·赫德森》的成文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也把亨利·詹姆斯引向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后来被证明是他的伟大主题之一。
我们怎么知道他读过这本书呢?1874年,在创作《罗德里克·赫德森》的同时,他连续数月在纽约一家名为《独立者》(Independent)的周刊上发表“佛罗伦萨札记”(Florentine Notes)。札记中明确引用了佩特著作中的谈论波堤切利(Botticelli)的一章。詹姆斯提到了“一位天才的评论家(《文艺复兴史研究》的作者佩特先生)”对波堤切利的评论“与其说是条理分明,不如说是能言善辩”。詹姆斯在1894年佩特去世后给埃德蒙·戈斯 (Edmund Gosse)写了一封信,信中他称佩特为“微弱的、苍白的、尴尬的、精美的佩特”,还将他比作“一点磷光,而非火焰”。“精美”同“过分讲究”一样,是一个两面都说得通的词汇。当詹姆斯告诉哥哥自己刹那间“像被火焰烧灼一般”想读佩特的著作的时候,正如他称佩特为“一点磷光,而非火焰”时那样,他是在取笑佩特书中最著名的字句 :“用耀目的、宝石般的火焰燃烧,就是生命的成功。”
詹姆斯拒绝用这种方式燃烧。没有其它任何信条能激起他更大的反感。他似乎把自己的热情都注入到笔下角色的生活中去,而不在个人生活里表露。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詹姆斯——依照佩特的标准——没有获得生命的成功。他的内心火焰都被引向虚拟人物。然而,考虑到他的同性恋倾向,他不可能不注意到佩特的著作在暗地里颂扬这样一种倾向,因为后者为列奥纳多(Leonardo)、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和温克尔曼(Winckelmann)倾注了许多笔墨。我想詹姆斯受到了警示,不希望落下一个唯美主义者或同性恋者的名声。与此同时,他了解同性恋者,也想刻画他们。他可以假借唯美的名义对他们进行负面刻画。普鲁斯特(Proust)就会这么做。佩特昭显男同性恋者的兴趣也可能导致了詹姆斯在同期撰写的艺术评论中强调“男子气概”这一对立面。在这样一个情境中,“男子气概”意指除同性恋之外的一切。
可是,他对佩特的反应并未止于警惕。我们必须想象一下他是用什么样的眼光来阅读《文艺复兴史》的“结论”部分的。他之所以认为佩特对波堤切利的论述雄辩胜过条理,是因为他觉得文中对某种风格的偏爱胜过了内容实质——在后来的《一位女士的肖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里他指责唯美主义者和唯美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他在《佛罗伦萨札记》中写道:“有时候人们有种冲动,想对那些在这样一个饥饿和罪孽的世界里过于钟情纯唯美的人提出无言的抗议。”( 詹姆斯本人对罪孽的兴趣浓于饥饿。)尽管他在文中承认“对艺术的一知半解有其豪壮之处”,但豪壮行为不等于英雄行为。
佩特主张在艺术和生活中强调品味和风味。他博学地引用了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话语(其实引用赫里克[Herrick]即可),强调万物的瞬间即逝性,尤其是它们的“流变”——他对此的称颂多于感伤。万物如流水——这是一个常用的意境——抑或(用人体作比喻)似脉搏。在这个流动的过程中,我们只能寄情于对情感、印象、感觉、搏动、瞬间的追求—— 这些词语对佩特来说都有双重含义。“脉搏次数只是丰富多彩、激动人心的生活对我们的赐予。”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体验的结果,而是体验本身。”佩特说:“一切都在我们脚下化解,我们应该抓住任何细致的情感,或者任何能让精神获得瞬间自由的知识,或者五官受到的任何刺激,不同寻常的颜色、罕见的花朵、奇妙的气味,还有朋友的脸……情感使人对生活更敏感、更能感受随爱而来的喜悦和悲伤、更有政治或宗教热情,抑或是对人类的热情。”……“但一定要确保它是情感,”他加了一句告诫性的后话。这段名言不但为唯美运动指明了目的,也为其提供了词汇。
佩特的言语好似爱抚,詹姆斯对此退避三舍。他所钟爱的角色可不是随波逐“流”的人物。他详细铺垫他们情感的来龙去脉,求爱几乎绵延不断,订婚期长达数年,对另一方真实面目的了解被无限期地延迟。延迟对詹姆斯来说就像即刻满足对佩特来说一样重要。詹姆斯对“结论”的最直接的评论体现在艺评里,他反对印象派,坚持认为(见《格罗夫那画廊》[The Grosvenor Gallery])“画作不是印象,而是表现。”就好像他预先知道叶芝(Yeats)会在《人物》(Dramatis Personae)中写道:“佩特所表达的文化理想只能催生阴柔——灵魂成了镜子,而非火盆。”詹姆斯还在各篇文论中批评了那些被佩特冠以情感美称的自恋念头。
我们只要仔细推敲就可以认定,詹姆斯的小说《罗德里克·赫德森》的中心主题正好同佩特唱对台戏。小说的情节几乎就像一个寓言:大有前途的美国青年雕塑家罗德里克·赫德森获得艺术爱好者罗兰·马利特的赞助,可以去欧洲游历三年。这份赠与的动机看上去再纯洁不过,而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这两个人都爱上了同一名妇女。游历的目的是让他开拓视野,提升艺术表现力。罗德里克·赫德森一到罗马就开始发表佩特式的、而非罗马式的言论。赫德森问:“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印象怎么了?……一个星期里有二十个片断……看起来是终极性的……还有二十个看似极致的印象……可是其它片断和印象接踵而来,挟卷它们一同前行,然后它们全都化解了,如同水化解在水中一般……”这就是佩特所说的片断、印象、花、化解和水的意象。罗兰·马利特对赫德森的言论表示不以为然,他想:“他对新鲜事物的追求永无止境,而对一切看似异类的事物,他总会付出额外的情感;但半小时过后,新鲜感消退了,他猜出了秘密所在,他挖掘出了秘密的核心,就吵嚷着要求更多的感官刺激……”“异类”在此等同于佩特爱用的“不同寻常”和“罕见”。罗德里克·赫德森宣称:“我们必须像脉搏跳动那样生活,” 这是对佩特所言“脉搏次数只是丰富多彩、激动人心的生活对我们的赐予”的呼应。无怪乎罗德里克在罗马度过的最初两周被他的朋友称为“一次高度唯美的狂欢”。他已经陷入到对艺术一知半解的非英雄行径中。
不幸的是,这场狂欢很快变成了一种“流变”,而“流变”这个生动并受佩特赞许的词汇在詹姆斯那里不受欢迎。罗兰·马利特告诉罗德里克:“你蹒跚过,漂流过,你从一件事漂向另一件事,而我确信此时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佩特曾经颂扬过米开朗琪罗所创作的亚当的不完美;而罗兰则用遗憾的语气说“这可怜的家伙(罗德里克)不完美。”罗德里克沉浸其中的“无限试验”只是一种“有害的幻想”。“最终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流变不仅仅是流变,而且变成了坠落。罗德里克后来真的从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脉上摔了下来,而这一摔也有象征意义。他的崩溃由于试图从对克里斯蒂娜·莱特的追求中获取新的感官刺激而加速了。注定将成为卡萨马西玛王妃的克里斯蒂娜对他来说是一个合宜的目标,因为她比佩特笔下的蒙娜丽莎更有道德上的模棱两可性;同佩特对“希罗底的女儿”的秘密崇拜遥相呼应,克里斯蒂娜·莱特被描写为“能与希罗底媲美”。詹姆斯后来觉得自己给了罗德里克太多不利的筹码,以至于这位年轻人迅速崩溃。这也许是因为詹姆斯对佩特的公式过于恼怒。通过罗德里克,他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人物,一个被他嘲弄、讽喻和从道义上批判的唯美主义者的形象。对罗德里克的刻画并非全无同情:他在阿尔卑斯山区险崖的死就相当雄辩。
《罗德里克·赫德森》是詹姆斯精心策划并持续三十年之久的拿破仑式战役的第一阶段。四年后的1878年,他写了一个题为《一束信件》(A Bundle of Letter)的短篇小说。其中的一个“唯美型”人物谈到:“除了艺术,生活还能是什么?佩特在某处已经讲得再透彻不过了。”我无法肯定那时佩特是否有如是的言语,但他一定有所暗示。在《一位女士的肖像》(1881)中,詹姆斯演化出了一个明确发表此种言论的角色。吉尔伯特·奥斯蒙德提醒伊莎贝尔·阿切尔:“你难道不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一个人应当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件艺术品?”奥斯蒙德身上渗透着佩特式的异端邪说。他说自己是“在世的最最过分讲究的青年绅士。”他的确过分讲究——他有品味,他有感觉;他缺少的是同情心和对妇女的爱。他爱摆姿态,他只求形式而不关心内在实质,正如拉尔夫·杜歇所言,他是“一朵褪色的玫瑰花蕾”,也因此是“一名毫无生气的艺术半吊子”。佩特在他的“结论”里说,个体是孤立的,“每个头脑都囚禁着一名孤独的犯人,那就是对世界的梦想。”同这个比喻相呼应,奥斯蒙德把家当成囚禁妻子的地方,把女儿送进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监狱——修道院。作为生活艺术家的奥斯蒙德,还有作为艺术家的赫德森,都为自我所困。奥斯蒙德的情妇默尔夫人同他们气味相投,因为她把“生活的艺术”当作“被她猜透的某种花招”。通过对照,詹姆斯呼吁少谈艺术,多关注心灵。

詹姆斯一看到佩特的书就觉得厌憎不迭。其他人对佩特的态度没有这么激烈。奥斯卡·王尔德比詹姆斯稍晚一些阅读了《文艺复兴史研究》;当时他只有二十一岁,正急于依附于某种令人向往的信条。对他来说,这本书一直是他的“宝书”,“一本对我的人生有着如此奇妙影响的书。”他在1877年给同班同学写了一封信,劝告他“充分发挥你天性的每一部分”。在他不知道自己人生何去何从的情况下,他认为佩特为自己指明了方向。
同《罗德里克·赫德森》里的克里斯蒂娜·莱特一样,王尔德尝试过天主教——这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新的感官刺激”;而《一位女士的肖像》中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写给伊莎贝尔的题为“重访罗马”的十四行诗之所以得名,可能是因为王尔德在1881年发表了“未曾拜访的罗马”一诗。然而,吸引王尔德注意力的并非只有罗马天主教;他同时还从共济会得到新体验。如果说,他对佩特的诱人论调有所反应,那他同时也对罗斯金(Ruskin)的讲座和谈话里的道义斥责作出反应。有时候,他为自己的善变感到不安:他曾经写信给一位朋友说:“然而,我随着思绪的改变而千变万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软弱、更自欺欺人,这一点我就用不着详叙了。”他就是在这种情绪中写下了诗歌《哎呀!》(Helas!)。诗中的他像佩特和罗德里克一样随波逐“流”:
追逐每一种情感变化,直到我的灵魂
变成一具上了弦的诗琴,随风而鸣……
但1886年,他怀着另外一种心境为自己辩护:“我愿意为了某种感觉去上火刑柱,一辈子做个怀疑论者!只有一样东西令我无限神往,那就是变幻无常的情感。控制这些情感让人愉悦,但被这些情感控制更让人愉悦。有时候我觉得艺术生活是一个漫长而美丽的自杀过程,而我对此一点都不遗憾。”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王尔德试图同时扮演多个角色——想身兼艺术和生活的鉴赏家二职——而佩特在《文艺复兴史研究》里对这样一种人的性格进行过详细刻画。
早期的王尔德忠于佩特著作的“结论”部分,因此他不可避免地站到了詹姆斯的对立面。1877年4月30日,两个人都参加了位于新邦德街的格罗夫那画廊的开业典礼,因此可能见过面。这两位作家分别就此为不同的杂志撰写了短评,称颂伯恩-琼斯(Burne-Jones),但亨利·詹姆斯认为他在男子气概方面有所欠缺。凑巧的是,两个人都描写了画展上最重要的画作,G.F.瓦茨的《爱与死》。詹姆斯的文笔优雅中肯:
大块的画布上有一个身披白袍的人形,背对观众。他的身姿和衣褶的流动都带着不祥之兆。他正准备跨过一道门槛。门槛里面,凋败的玫瑰花丛旁,小爱神冲了出来,头部和身体因恳求而扭曲,徒劳地试图阻挡他的进入。
同样一幅画引得王尔德感情勃发;他看到的是:
一个遍植开满星星点点白花的茉莉和散发甘美芳香的玫瑰的大理石门道。蒙着灰袍、身躯庞大的死神,带着无可避免的神秘力量,践踏着花丛前行。一只脚早已踏上了门槛,一只无情的手已经伸出。而爱神,一个长着轻盈的褐色小腿和彩虹般双翼的美丽小男孩,像一片枯叶一样瑟瑟发抖,双手无助地试图阻挡他的入侵。
审慎的詹姆斯认为这幅作品的“优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唯美而不拘小节的王尔德认为它能同米开朗琪罗的《上帝分光暗》(God Dividing the Light from the Darkness)媲美。谈到那个美丽的小男孩,王尔德全身颤抖,詹姆斯则侧目斜睨。在1888年写成的评论乔治·杜莫利尔(George Du Maurier)的文章中,亨利·詹姆斯指责说,唯美主义者“欠缺真正的审美能力”,因而才会“热情过度”。当时詹姆斯同罗斯金一样较为侧重道德;他们俩都极不喜欢惠斯勒(Whistler),詹姆斯从其身上看到了佩特的印象主义。而王尔德尽管略微取笑了一下那幅开裂的岩石的画作,仍然承认惠斯勒是位伟大的艺术家。二十年后,亨利·詹姆斯也回心转意。
也许詹姆斯和王尔德都没有互相拜读过对方有关格罗夫特画廊开业典礼的评论,因为詹姆斯的评论在美国发表,而王尔德的评论在爱尔兰见报。但是,整个1882年王尔德都在美国游历,他们将在詹姆斯的故乡正面接触。这时候的王尔德同佩特一样,尽管仍然是感觉论者,但已经不那么天真了。他的唯美主义观点在经历了他人的攻讦后日趋成熟。王尔德在考虑怎样反驳那些认为他荒谬的人自身的荒谬之处。此时他形成的思想可以被称为后唯美主义,或重构唯美主义。在一篇文艺批评中,他坚定地否认一个观点,即为艺术而艺术是艺术的终极源泉;而是视之为“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创作公式”,也就是创作期间的思考状况。至于美,他继续颂扬它,但是认为不仅仅应该由艺术家或他的赏识者来追求,还应当为整个社会所承认。后来他的思想最终会演变成某种社会主义的形式,而这种信条被佩特唾弃。在美期间,王尔德发表了题为《英国文艺复兴》的演讲,对英国文艺复兴大加赞赏。这时候的他已经从很大程度上挣脱了佩特所向往的对孤立的片断的追求这一禁锢。这种文艺复兴完全异于佩特的概念,它不但是鉴赏家的文艺复兴,而且是每个人的文艺复兴,涉及衣着、建筑和家庭装饰。
王尔德来到了华盛顿,在这里,在1882年1月,他遭遇了已在此逗留了一个月的亨利·詹姆斯。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法官爱德华·G·洛林(Judge Edward G. Loring)家,当时王尔德身穿及膝短裤,衣袋里插着块大大的黄色丝绸手帕。詹姆斯避开了他。但出乎他的意料,王尔德在接受报家采访时宣称没有任何英国小说家比得上霍威尔斯(Howells)和詹姆斯,很是让他高兴。于是他去王尔德下榻的旅馆致谢。这次拜访不成功。詹姆斯说:“我想念伦敦。”王尔德忍不住要奚落他。“是吗?”他说这话的时候毫无疑问地使用了他那最最有教养的牛津口音。“你在意某些地方?世界是我家。”他觉得自己是位世界公民。对詹姆斯这样一位把国际主题看得很重要的作家来说,这话很唐突。王尔德还对詹姆斯说:“我要去波士顿;我要替我最亲爱的朋友伯恩-琼斯(Burne-Jones)向他最亲爱的朋友查尔斯·诺顿(Charles Norton)转交信件。”詹姆斯同这两人都很熟悉,熟悉到不会为了听到他们的名字而感到高兴。我们必须这样想象,亨利·詹姆斯被王尔德的及膝短裤激怒,对后者的自我标榜和毫无意义的流浪生活不屑一顾。他告诉因为不喜欢“傻子”而拒绝同王尔德见面的亨利·亚当斯(Mrs. Henry Adams)夫人说,她的看法是对的。“王尔德是个愚昧的傻瓜,百分之百的无赖,不洁的畜牲。”这些极端的形象说明詹姆斯在王尔德身上看到了佩特不具备的威胁力。佩特掩盖自己的同性恋,而王尔德则四处张扬。佩特可以用“微弱的、苍白的、尴尬的、精美的”来概括,但詹姆斯对王尔德的表述覆盖了他的思想、举止、可能还包括性取向(“不洁的畜牲”)。就好像亨利·詹姆斯生怕卷入丑闻,于是要明文记下他对王尔德毫无好感。
1884年,他再次触及了唯美主题。那是在他杰作之一,《“贝尔特菲奥”的作者》(The Author of “Beltraffio”)里。《“贝尔特菲奥”的作者》里的文艺批评成分远远多于詹姆斯此前的作品。马克·安比安(Mark Ambient)写的《贝尔特菲奥》被称为“迄今为止最完善的艺术福音书;它是唯美主义的战斗口号”。但是,就在詹姆斯创作这部小说之前,的确有这么一本书问世。那就是于斯曼(Huysmans)的《逆天》(A Rebour)。尽管《逆天》意在讥讽——其中部分内容的讥讽意味彰然若显——但它在1884年5月出版后立即成为唯美主义的圣经。詹姆斯的朋友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认为它很棒,惠斯勒在该书出版的第二天就向作者表示祝贺,王尔德觉得它是几年来最好的作品。詹姆斯有一本该书的初版,但他认为它荒谬。他为《“贝尔特菲奥”的作者》创造了欺骗和病患的氛围,这似乎说明他在《逆天》出版后马上阅读过该书。要记得,于斯曼笔下的主人公德·伊桑戴在试过看似真花的人造花后又喜欢上了看似人造花的真花;詹姆斯告诉我们,在马克·安比安的花园里,“某些褐色的旧墙上缀满了爬藤,在我看来像是从拉斐尔前派的杰作里抄来的。”(于斯曼也提到过拉斐尔前派。)安比安的家宅似乎同安比安书里的家宅如出一辙。安比安的妹妹长得像一幅具有象征意义的画里的人物,他的儿子“像一件完美的小艺术品”。只有安比安夫人不愿被唯美化:“我根本就不认为我是生活在他的某部作品里”。安比安的唯美化的儿子病了,他把死亡带进了这个本来就没有什么生气的场景。在于斯曼的作品里,一只嵌着珠宝的乌龟因为过于不自然而死去,而最后德·伊桑戴必须摒弃人工才能生存。詹姆斯铺陈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但显然他从《逆天》中得利,就像他当年从佩特的《文艺复兴史》中获益那样。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即从1884年到1888年,詹姆斯、王尔德和佩特很难避免在伦敦排外性很强的社交圈内碰面。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些可能促使詹姆斯改变对王尔德看法的事情。其一是王尔德不再穿短裤,结婚成家了。其二是他开始发表除唯美派诗歌以外的作品——开始是书评,后来是童话集。王尔德极可能赢得了詹姆斯的首肯,就像他赢得其他反对者的青睐那样。这种说法的证据是,当1888年王尔德申请加入萨维尔俱乐部的时候,亨利·詹姆斯签名同意他的申请。
对王尔德而言,他批评詹姆斯的小说时一直心怀崇敬。他在八十年代晚期的文评中隐隐约约地提到一个新的小说流派,它“非本地出产,亦无意模仿任何英国大师。它可以被描写成为巴黎的现实主义经由波士顿影响的精雕细刻后的产物。分析,而非行动,是它的目的;它重视心理胜过情感,而且对某一根弦的拨弄非常巧妙,那就是寻常之物。”后来,在1889年1月他又在《谎言之衰亡》(The Decay of Lying)中提到了詹姆斯;这次他说詹姆斯“视小说创作为痛苦的责任,把他那简洁的文学风格、妥帖的用词、机智而尖锐的讽刺都浪费在了卑微的动机和难以觉察的‘视角’上。”这听起来可能不太客气,但在王尔德对当代小说家的评论里已经算得上不错了,而詹姆斯对此也没有什么憎恶之情。可是,也可以这么说,这促使他在同年创作的《悲剧缪斯》(The Tragic Muse)里再次塑造了唯美主义者的形象。
在这部小说里,加布里埃尔·纳什对唯美主义者的称号嗤之以鼻,但他的确是唯美主义者。比起罗德里克·赫德森、吉尔伯特·奥斯蒙德或马克·安比安,他这个唯美主义者更容易被人接受。他没有必要从悬崖上坠落,也不必独身,更不必虐待妻子。可他仍有自己的惯用语:对他来说,生活的唯一“责任”是辨认“我们独特的形式,我们每个人所携带的乐器”,是“完美地”演奏那样乐器。(佩特和王尔德都用音乐来比拟心灵。)纳什有种流浪气质,更适合做王尔德,而非扎根在家的佩特。所以,当尼克·多默问纳什“难道我们不都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的伦敦吗?”时,纳什会答道:“啊,我亲爱的多默,请原谅。我不生活在十九世纪。这辈子从来没有!”“那你也没在伦敦呆过?”“没有——当我不在萨马康德的时候。”加布里埃尔总是被描写为在“去某处”的途中。
或许,在这里,詹姆斯回想起了他在华盛顿同王尔德的交谈,记起了他曾坚持说自己是世界公民。但詹姆斯没把加布里埃尔·纳什当作无赖、傻瓜或畜生来打发,而是将他视为多默走向绘画生涯的催化剂,并且承认加布里埃尔的品味超凡脱俗。加布里埃尔的职业生涯如同王尔德当时那样难以确定。他写了一部据传有不错内容的小说,但大部分时间都无所事事。据说他的想法“与其说机巧,不如说合乎时宜”。尽管加布里埃尔可能在真实生活中有其他原型,当时显然还有别的无所事事的人,但没有一个在1889年写到同唯美主义有关的东西的人不会想起王尔德这位无所事事到极致的人士。更何况,詹姆斯明确指出,他不是“英格兰人”,既然他显然不是美国人,那他很可能是爱尔兰人。詹姆斯还确切地指出,纳什的说话方式显现出“一种刻意而富有侵略性的完美”,叶芝和其他人都在王尔德身上看到了这个特点。此外,纳什跟王尔德一样,即使不在场也是谈话的中心。詹姆斯给他笔下的角色机会,让他热烈地还击两个经常针对王尔德而发的指控。第一项指控说他只是个笑剧演员;当加布里埃尔受到同样指责时,他回答说:“人尽其能,何况我的能力是我自己小小系统中的一部分。”另一项指控是,王尔德宣扬唯美主义,却举不出日常适用的唯美主义成就的例子来(后来他会举出例子来)。针对这一点,加布里埃尔说:“喔,举例是桩可怜的事儿。就好像承认自己的失败。”就在这个时期,王尔德告诉安德列·纪德(Andre Gide):“我把天才都用到了生活里;我只是把天分用到了作品里。”
加布里埃尔·纳什的唯美理论是佩特式的,没有迹象表明他受了王尔德后唯美主义的影响。“我们必须体验一切,体验一切我们可以体验的东西。我们为此而生。”加布里埃尔经历各个“阶段”,“印象的各个层次”、“我的感觉指引着我——如果说我的生活有方向的话。只要有东西可以体验,我会尽量去体验!”结果他成了没有镇重沙袋的气球,“我流浪,我漂流,我漂泊”。他加入了佩特、王尔德和詹姆斯早期小说中其他漂流者的行列,但对此毫无歉意,更没有在小说中受到惩罚。
詹姆斯对加布里埃尔的背离在小说结尾处变得明显起来。加布里埃尔接受劝说,坐下来让多默给他画像,但画了一次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然后怪事发生了。不但他的形象从小说中消失,他的画像也神奇地从画布上消失了。詹姆斯的意思是,纳什这个不论情境就追逐感觉的人其实根本不存在。那个从虚无中看出层次来的人逐渐隐去,世界公民无处落脚。
王尔德不可能没读过《悲剧缪斯》。他一辈子都在读詹姆斯的作品;他最后一次购书的账单上列有《大使》(The Ambassadors)。事实上,王尔德在接下来几个月里创作的小说显示,他得益于亨利·詹姆斯的作品。同《悲剧缪斯》一样,《道连·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里的三个主要角色分别是一名画家、一名唯美主义者和一名悲剧女演员。加布里埃尔·纳什的画像同道连的画像一样发生象征性的变化。詹姆斯笔下的悲剧缪斯米里亚姆·劳斯曾用过格拉迪斯·文的艺名;王尔德笔下的女演员叫西比尔·文,这很难说只是个巧合。米里亚姆·劳斯是犹太人,西比尔·文不是,但是(如果一定要加进这一笔的话),西比尔的经理是犹太人。
《道连·格雷》常被误解。这本书就像詹姆斯创作《悲剧缪斯》时一样对唯美主义持批评态度。佩特的格言被拭去尘埃,重见天日,只是这一次它们被推翻了。亨利·沃顿勋爵的嘴边常常挂着这些格言——他在书里最大的过错不在于他从未犯过的放浪不羁,而是抄袭佩特早期的言论。佩特本人在评论该书时说(清醒的佩特这样警示醉酒的佩特),亨利勋爵没有认识到,仅仅把生活视为感觉是无政府主义,会导致自我摧毁。道连·格雷是他的实验,实验失败了。王尔德创作小说的意图被人忽略的原因是,书中的反面人物说出来的话像他本人,而正面人物像你我。其实他想通过这本书向人说教,按唯美主义准则生活是不可能的。道连不能绝世独立。自我放纵最终让他毁掉了自己的画像,而毁掉画像这一行动的本身同他的原意相反;不管他有多不愿意,他还是通过死亡表现了自己较好的那一半。他已经突破到两个极端的交汇点。自杀使道连成为唯美主义的第一名烈士。
对詹姆斯来说,尽管他没有对《道连·格雷》发表过公开评论,但这本书只不过是他周围的人坚持要写的书里面的一本。王尔德把书写得既优雅又随意,好像写小说是消遣,而非“痛苦的责任”。没有人会误以为它是一篇有斧凿痕迹的作品。其中深层的传奇,也即浮士德试图向生活索取多于自己应有的那一份的情节,激起人们内心深处罪恶的渴望;这和在言语造诣上登峰造极的英国文化之间的对比导致了远比故事情节来得多的紧张状况。
令詹姆斯恼火的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发展成为一个道连的时代。他为此再次对王尔德表示不屑。但他发现自己在同后者竞争。尤其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同时开始创作剧本。王尔德写的不是唯美主义的剧本,可詹姆斯依旧不看好它们。他声称,《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无论从主题到形式来看都很幼稚”。他承认,该剧含有“许多有趣的情节——其中的对话‘俏皮’机智”。他甚至还在自己的信件中引用了一些警句。在给他和王尔德共同的朋友,巴黎的亨利埃塔·鲁贝尔夫人(Henrietta Reubell)的一封信中,詹姆斯写道,“某某人(他不愿意提他的名字)”谢幕的时候“在钮孔里插了一朵闪烁着金属蓝光的(其实是绿色的)康乃馨,指间夹着根香烟”。他觉得王尔德所言“我过得非常开心”不符合场上气氛,但观众们似乎都被他逗乐了。“这位先生总算触动了我的神经,”詹姆斯私下里承认。他没有提到王尔德的名字,后来在同艾德蒙·戈斯(Edmund Gosse)的通信中也未曾提及。这可能说明,他再次意识到,跟王尔德搅在一块儿可能会出问题。
王尔德的下一个剧本《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A Women of No Importance)也没能博得亨利·詹姆斯更多的欢心。他觉得它“无知到了无助的地步”。可他也并非丝毫未受王尔德的影响。在他接下来创作的剧本《盖伊·多姆维尔》(Guy Domville)里,一些对话听上去有那么一点王尔德的味道。人们常常谈论《盖伊·多姆维尔》一剧上演的典故,但如果他们能把王尔德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就更好了。它是詹姆斯最重要的剧作。亚历山大(Alexander)决定将其搬上舞台,而首次演出的当晚,过于缺乏自信的詹姆斯前往附近另一家剧院观看了王尔德创作的《理想丈夫》(An Ideal Husband)。他先入为主地认为王尔德的剧本有所欠缺,观剧之后也的确找出了它的不足之处。它是“如此地无助、粗糙、低劣、笨拙、无效、庸俗”。可是它大受观众的好评。那么观众也有问题。然而,《理想丈夫》的某些地方让他犹豫不决。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剧本都触及了弃绝这一主题。盖伊·多默维尔想要弃绝尘世,成为罗马天主教的教士。可就在关键时刻,他的一位亲戚去世了,他成了多默维尔家族最后一位传人,结果他接受劝说,决定娶妻成家,传宗接代。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新娘的人选换了一个又一个,他却再次决定弃绝尘世。再没有比这更高超的情操了。
最让詹姆斯恼火的是,在《理想丈夫》里,罗伯特·奇尔顿爵士——即剧名中的理想丈夫——也面临着一个类似的抉择。他年轻时曾经出卖过内阁机密,尽管外界无人知晓,但他妻子说服他,要他出于道义宣布放弃从政。可是最后两个人都转而认为,没有必要放弃。王尔德用喜剧来纵容观众,而本身就擅长弃绝的詹姆斯只是教育人们去坚定地实现目标。王尔德轻而易举写出的剧本胜过了詹姆斯的呕心沥血之作。更糟糕的是,亚历山大决定停演詹姆斯的作品,转而上演《欧内斯特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亨利·詹姆斯的剧作只上演了一个月就被唯美主义代表人物的作品取代,他蒙受了奇耻大辱。
传记作家们告诉我们,亨利·詹姆斯在目睹了观众对《理想丈夫》的热情之后,步行去观看自己剧本的上演情况。乔治·亚历山大有点恶意地将他从后台引出,要他谢幕。一开始詹姆斯以为观众是在欢呼,但很快他发现他们是在取笑他,以至于他不得不狼狈地退场。据说,这一事件让詹姆斯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但我们不应该低估他的自我认识。这之前他刚刚看到那些“无知的观众”为一出他认为低劣的戏大加喝彩,这时候他为什么要屈服于同样一批人对他自己的作品喝的倒彩呢?毕竟,他是一位五十二岁的聪明绝顶的名人。演出结束后,他的表现非常坦然:他曾经许诺要请全体演剧人员吃饭,他确实这么做了。他给哥哥写信描写了自己所蒙受的耻辱,但又加上了以下一席话:“别为我担心。我是块岩石。”第二天,他招待一些朋友吃午饭,然后观看了《盖伊·多默维尔》的第二场演出,而且目睹了现场观众所表现出的崇敬之情。评论家的观点有所分歧,但是威廉·阿切尔(William Archer)、杰弗里·斯科特(Geoffrey Scott)、H.G.威尔斯(H.G.Wells)和萧伯纳(Bernard Shaw)都对此大加赞赏。这是对他的安慰。艾伦·特里(Ellen Terry)是安慰他的众多朋友中的一位,她请他为自己另写一个剧本。就在所谓的情绪低谷的第三天,詹姆斯同意了这个要求。
事实上,他对自己过于自信,对伦敦的观众和他们所喜爱的剧作过于不屑,所以他根本不可能陷入情绪低谷。几个月后,他答应过艾伦·特里的剧本写成了。该剧名为《夏日柔情》(Summersoft),讲的是求爱的故事。其中的一些对话显示,詹姆斯看过王尔德的《欧内斯特的重要性》:科拉是这样向格雷斯丢夫人描述她的恋人的:“他聪明,人也好,而且我知道他爱我。”“那他有什么不好的呢?”“他的名字不好。”“他叫什么?”“巴德尔。”格雷斯丢夫人想了想,说:“嗯——巴德尔这个名字还行。”这里有点邦伯里的味道,还让人想起有关欧内斯特这个名字的争论——当然,詹姆斯的意图可能不同,巴德尔这个不悦耳的名字显而易见地带着中产阶级的味道。
不管詹姆斯有多憎恨王尔德在剧本创作上的成功,王尔德受审一事顷刻之间就让这种想法变得毫无意义。他震惊于那些“卑鄙的禽兽般的证人”。“好无知的一帮勒索者!”他是这样评论的。但在写给艾德蒙·戈斯的信中,他没有流露出多少同情心:“是的,它带有荒谬可笑的、骇人听闻的戏剧性,真的很有趣——如果我们能用有趣一词来形容如此恶心可怕的事件的话。”
这封信以詹姆斯式的置身事外揭示出他当时卷入得有多深。他在另一封写给保罗·布尔热的信中,认为对王尔德的最终宣判很残酷;詹姆斯提议,把王尔德囚禁在单人牢房里要比法官所裁决的两年苦工更人道一些。事实上,王尔德尝到了这两种刑罚的苦头。只有一次,詹姆斯预想了王尔德“改邪归正”出狱后的情景:“他还能写出伟大的杰作来!”但这看起来像是留作记录用的形式上的同情。詹姆斯后来也没有反悔:1905年在美国巡回讲学期间,他曾说王尔德是“爱尔兰冒险家之一,他们身上有些罗马式的特点——很能干,但很虚伪。”他入狱前后的生活都一直非常“可憎”,他的死很“悲惨”。
佩特死于1894年,一年后王尔德受审,成了行尸走肉。这时詹姆斯又重提唯美主义。在1897年创作《波埃顿的战利品》(The Spoils of Poynton)之时,他可能回想起王尔德1883年在英国发表的一次题为《美厦》(The House of Beautiful)的演讲。起初詹姆斯想把它作为自己小说的题目,而佩特在他的《欣赏》(Appreciations)中也用过这个劣迹斑斑的字眼。书中有部分篇幅被用来反对把高雅品味导致的感受看得比更基本的情感重要。在此,与其说鉴赏力受到了攻击,不如说它被摆正了位置。詹姆斯继续揭示脱离生活的唯美主义的缺点。
詹姆斯1903年创作的《大使》里的斯特赖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沃莱特,戴着清教徒的有色眼镜,可是在巴黎的熏陶下他很快换上了唯美主义的有色眼镜。后来,正当他把乡村景色当成画作一样来欣赏的时候,一对活生生的偷欢男女闯入了他的眼帘。唯美主义顿时失色,他的道德观又占了上风。斯特赖舍曾经鼓励小比尔汉姆“尽你所能地生活;不这样做是个错误”。但在小说结束时,斯特赖舍不得不承认,这种唯美主义的劝诫有所偏颇,基于欺骗的美毫无动人之处,不能因为道德不唯美、过于阴沉就摈弃它。对斯特赖舍本人来说,唯美观和道德感对他的吸引力都大不如前了。这部小说里没有坏人,对唯美主义者和非唯美主义者均表同情。詹姆斯对唯美主义不再言辞激烈。
他最后一次提及唯美主义是在1904年一篇有关邓南遮(D’annunzio)的文论里。文中他友善地回忆起,若干年前,整个社会被从“药物促成的熟睡中惊醒,接受了‘唯美的’生活法则……”但到邓南遮为止的唯美主义代表人物都未能充分传达其中的内涵。唯美主义要的是“不顾代价的美”,但正因为如此,它提倡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品味和性。他用“绝望的敏感”来概括邓南遮的作品,说它最大的缺陷是把性关系从生活中脱离出来,而事实上只有在生活中性关系才能得以“完满和延伸”,否则它只是“动物性的”。詹姆斯希望唯美主义能找到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代言人,好像佩特、王尔德、于斯曼和邓南遮所写的一切言论都无济于事。在这段时间,他已经同青年雕塑家亨里克·安德森(Henrik Andersen)发生了暧昧关系,至少是接近暧昧的关系。他给后者写的信里满是示爱的言词,经常提到爱抚。
如果说,亨利·詹姆斯认为自己是更具说服力的代言人,这一推测不应该是异想天开。他在评论邓南遮的同一年里还创作了《金碗》(The Golden Bowl)。詹姆斯可能觉得自己是在重新组合唯美主义的要素,以向世人显示,当年它们要是这么组合的话,唯美主义的成就该有多大。小说中的四个人物都很精致:他们的味蕾和其它触角都如沃尔特·佩特所愿的那样高度发达、异常敏感。他们的性关系像邓南遮作品里那样居于中心位置,但对性关系的重新组合才是真正的引人入胜之处。女主人公的目标是从自己父亲的妻子那里夺回自己的丈夫。要达到这一目的,只能依靠想象力对生活的影响,靠它变丑陋为美丽,这种美符合道德观念,但尊崇道德不是美的主要目的。作为书名的金碗象征她的追求,但书中的金碗有一道裂纹,必须被摔碎,这样才能重铸一个头脑中的金碗。高雅到极致的品味并非体现在聚集精美的外在物品,而是用爱的名义感召潜在的个人素质。结局很美丽,但该书追逐的不仅仅是美丽。
所以,唯美运动并未终结。它继续吸引历代作家对它进行重新定义。在它成型的初期,它唤醒了亨利·詹姆斯,让他写出了批评它的首部小说。尽管他还有过其它主题,但他从未将唯美主义束之高阁。在他创作生涯结束之时,他比以往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一直在用唯美主义运动当托词,他假借批评的名义代表了同自己趣味相投的人们。在《金碗》里,詹姆斯变得更老练、更大胆,他视唯美主义的过分讲究和对美的坚持为生活的中心,而非其对立面抑或外围环节。也就是说,唯美主义者和同性恋者一样,都是天地万物的一个组成部分。
(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