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群鸟飞过阴霾的天际
人们鸦雀无声
我的血液因为等待而疼痛
——选自《暴雨将至》
不久以前,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国家……
这段话多少有些戏仿《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它出现在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史诗巨作《地下》(Underground,即《没有天空的都市》)的起首。这句简单到不完整的话,却无比沉痛、意味深长。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前南斯拉夫在此起彼伏的残酷战争里分崩离析,正是以库斯图里卡为首的一批导演,用胶片为他们曾经的祖国刻下了一块又一块沉重的墓碑。
但是这些前南斯拉夫籍的导演们并不是在简单地陈列什么“伤痕文学”。他们把刻骨铭心的家国之痛与天才横溢的电影构思紧紧熔铸在一起,使他们的作品具有加倍的震撼力。某种意义上,九十年代的“南斯拉夫”电影,就如同拉美“爆炸文学”,都是一个时代一种艺术形式里最富创造性的杰作。库斯图里卡和他的《地下》,就如同马尔克斯和他的《百年孤独》,他们是星系的中轴,在他们周围,群星闪耀,光芒四射。面对一个共同的主题——一个伟大国家的灭亡,他们用各自独特的眼光、思想和艺术手法,记录了事实,剖析了原因。
献给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
《战火硝烟》(Pretty Village,Pretty Flame)的开头铭刻着这样的墓志铭。其实不管是否写出来,每一部这样的影片,都注定要刻下这样的墓志铭。
杀戮之地,伤心之地
民族冲突、种族屠杀、内战,这是任何一个涉及这段历史的“南斯拉夫”导演无法回避的。而当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陷入仇杀,那些曾经相亲相爱如今却互相杀戮的人们,他们的内心比他们的身体流的血更多。
《惊变世界》(Vukovar)在我看过的南斯拉夫电影里,以最具现实性的手法表现了这一切。多瑙河上迷人的巴罗克建筑风格城市武科瓦尔,是克族与塞族人混居之地,双方人数几乎一样多。1989年,克族的安娜与塞族的托马结婚。新婚不久,南斯拉夫解体,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黑先后独立。时任塞尔维亚总统的米洛舍维奇首先对克罗地亚开战,“内战”爆发。托马应征入伍,怀孕的安娜也搬回娘家居住,等待丈夫回来,但她盼到的是塞军的炸弹与炮火。此时,托马正在塞军中,攻打自己的城市,与儿时的伙伴交火。托马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家看望安娜,可是安娜因丈夫是塞族,已经遭到本族兵痞的轮奸。在战火中,安娜生下了孩子,但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在民族仇恨的强大压迫下,再不可能复合。结尾,安娜和托马分别搭上前往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车,互相凝视的眼中饱含热泪,从此各奔天涯。花腔女高音激越的歌声里,镜头升起,从城市废墟上空掠过。足足两分半钟绵延的长镜头,那大片大片的残垣断壁让我们恍然明白,影片正是在劫后的武科瓦尔真实的瓦砾堆里拍成。
《惊变世界》极为细腻地刻画了内战初起之际,那些曾经是亲人、挚友的人们,当他们的枪互相指向对方时,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就像影片那首动听的插曲满怀忧伤地唱出的:
亲爱的朋友来自贝尔格莱德/斯洛文尼亚已经陷入了战火/亲爱的朋友来自贝尔格莱德/你已经无法到达大海边上/你有人爱你吗/是否有人会为你哭泣/亲爱的朋友我回来时鞋子沾上的怎么竟会是外国的泥土/……/亲爱的朋友来自萨格勒布/你开了第二枪/其实我已经原谅了你的第一枪/现在我放下枪向上苍祈祷/希望我没有打中我贝尔格莱德的朋友/但是如果我真的打中了你/我心中一定为你深深哀伤/当我为你合上双眼/哦,我是多么难过/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
出生于波黑首府萨拉热窝的老资格导演博洛·德拉斯科维奇此前已经十年没有拍片。1994年,他六十岁之际,国家的巨变驱迫他重新执起导筒,把他看到的、感受的和思考的一切用电影来表达。他选择了最朴素的方式。整部片子粗看只是静静地,甚至有些沉闷地讲述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战争如何一步步地将一个家庭、一个城市以至一个国家撕得粉碎。这种看似客观的描述却因为饱含了刻骨铭心的家国之痛,而格外残忍,就像医生当众一层层解开浸血的纱布,让你看下面模糊的血肉。
相比之下,《战火硝烟》(即《美丽的村庄,美丽的火焰》)没有这样全景式地表现内战。它将视线集中到波黑战争期间,一群被穆族武装包围在废弃隧道里的塞族士兵身上。更进一步,影片的焦点被推向一对分属穆族和塞族的好友。令人心痛的不再是夫妻之间的生死离别,而是挚友之间的你死我活。
1980年,当象征南斯拉夫民族和睦的团结隧道落成时,塞族的米兰和穆族的哈里尔还是一对最要好的小伙伴,他们一起读书、打篮球、偷看女教师做爱,形影不离。十二年后,波黑的穆族和塞族开战。米兰加入塞族军队,到处烧杀,可是当他路过家时,却得知母亲已经被穆族杀害。怀着深仇大恨,米兰在战斗中更加冷酷。他所在的塞族部队遭到穆族伏击,余部退入一条废弃的隧道。那正是十二年前米兰和哈里尔亲眼目睹建成的隧道。被围困十天之后,剩下的人冒死冲出隧道。在巨大的爆炸和火光中,米兰看见了哈里尔。他们互相凝视,枪口低垂,心潮澎湃……
而在另一部史诗巨作《暴雨将至》(Before The Rain) 里,普利策奖获得者、著名的战地新闻摄影师亚历山大从伦敦回到自己马其顿乡村的家,想在这记忆里美丽的地方,寻找心灵的宁静。但是令他震惊的是,种族战争已经将这里变得满目疮痍。昔日的情人属于敌对的民族,儿时的玩伴眼神里充满怀疑和敌意,而那些熟悉的邻居们整天互相残杀。就像亚历山大与属于阿尔巴尼亚族的旧情人父亲的几句富有诗意的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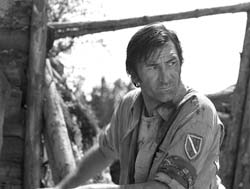
——时局不好啊,空气中都有血了。
——很闷。
——会下雨。
——一定会下,早晚的事。
整个环境处在交战之中,亚历山大的内心也被撕裂。让枪弹射向自己,似乎成了终结这难以忍受的一切的惟一机会。
民族主义:疯狂的泥沼
是什么让相爱的人们互相撕杀,形同野兽?民族主义狂热成为导演们强烈抨击的对象。在《战火硝烟》里,一个塞族士兵面对DV镜头的狂热演说,让我们进入一个大塞尔维亚民族狂热分子的非理性内心世界:
塞尔维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600年前,克罗地亚人、英国人、美国人还在用他妈的手抓肉吃的时候,我们已经会用这个——叉子。我们很文明,我们用叉吃饭,克罗地亚人却是用他们该死的爪子!
在这样一个失去理智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者心目中,从来没有留出反思的余地,想一想为了体现他所谓的“文明”,他用了多么野蛮的手段,杀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村庄。在影片结尾,医院里身负重伤的米兰拖着长长的血迹,爬到另一间病房,怀着满腔难解的深仇,刺向一名素不相识的穆族伤兵的,也正是这样一把吃饭的叉子!
纠缠着塞尔维亚民族的是一种缺少历史根据的宏大幻想,一种扎根于塞尔维亚民众中的神话:它是上帝特造的子民,注定要统治它的邻居——正如《战火硝烟》里,那个塞族士兵用他“生动形象”的语言所表达的。更不幸的是,作为“受害者”的克族、穆族、阿族,他们在战争和种族清洗中得到的并不是正面教训。相反,他们的民族狂热与塞族互相竞斗,互相激发,先下手为强、对敌对民族越残忍越正确,成为敌对行动背后共同的“准则”。如果说战争开始的时候,还有自卫者的概念,那么很快对双方都已经无所谓正义,有的只是残酷的生存斗争。这一点,仔细读一读《无主之地》(No Man’s Land,即《三不管地带》)里的一段精彩对话,就能够深刻体会。
被不分敌我的凶狠炮击赶进废弃地下工事的两个士兵,一个来自塞族,一个来自穆族。求生的渴望使他们暂时抛开仇恨,同处一室。他们居然以炮声为背景音乐,展开一场讨论。
塞:不再轰炸了。
穆:当然,你们的军队从不停止轰炸。
塞:难道你们的军队停过火吗?
穆:不能相提并论!战争不是我们引发的。
塞:那是我们引发的?
穆:是你们,你们只会制造战争。
塞:我们?
穆:对。难道你是和平主义者?大塞尔维亚,直通太平洋,谁说的?全世界都和我一样知道你们的妄想。
塞:什么世界?你们的世界!是你们轰炸我们的村庄,却说是我们干的。
穆:现在外面在开炮的只有我们的军队?你们都是圣人?算了吧,你们甚至让死人死无全尸!
塞:不一样!
穆:是吗?在尸体下面安置地雷、杀戮、强奸,这些是什么?
塞:你在说谁?
穆:你们!
塞:我没见过你说的情况。
穆:我看见了!我亲眼看见自己的村庄被烧。
塞:我不知道。我不在场。
穆:我在!
塞:我们的村庄难道没被烧吗?是谁杀了我们的人?
穆:你们自己,你们互相残杀,就像现在。
塞:他们朝我开炮是因为他们没认出我。
穆:跟你说也没用。你们怎么会想到要毁了这个美丽的国家?
塞:我们?
穆:对!
塞:你疯了。是你们想分裂,不是我们!
穆:因为是你们发起了战争!
塞:是你们引发战争的!
穆:什么?谁引发的?
塞:是你们引发的!你们!你们!你们!
穆:(猛地拉开枪栓,指向另一个的脑袋)谁引发战争的?
塞:(没有枪,只好无奈地摇摇头)我们。
穆:(松了口气,坐下,恶狠狠地)你们制造了战争!别再惹火我,我会冲动的……滚出去,快点,滚出去,妈的,胆敢说是我们……
没有人承认是他们挑起了仇杀和战争,都把责任推给对方,而且这么做是如此轻易。但是谁挑起的就这么重要吗?不管是谁开了第一枪,现在一切已经变成了一场血腥的混战。大家都是魔鬼,天使和上帝已经远离,他们抛弃了这块疯狂的土地。
地下世界:隐喻与历史
巴尔干素称“火药桶”,千年以上的历史里,这里就没有停息过厮杀。但是一度,似乎巴尔干褪去“火药桶”之称的美好前景就在眼前,那就是当铁托元帅将南斯拉夫统一起来的时候。1945年成立的南斯拉夫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它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马其顿、黑山、斯洛文尼亚以及塞尔维亚六个共和国,以及塞尔维亚境内的两个自治省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组成。铁托向南部斯拉夫各族人民和其他种族集团许诺,不论它们的大小、种族和宗教如何,它们将作为平等伙伴一起生活,南斯拉夫的财富和美丽就在于它的各族人民、语言、信仰和文化的多样性。看上去,好像这一历史性的实验成功了。但是当铁托这个富有魅力的铁腕领袖去世后,一切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向灾难滑去。
今天回首这段历史,我们恍然,铁托时代的美好和睦就像种满墓地的草地和鲜花,一旦失去强有力的手每天修剪、整理、维护,那被精心覆盖、掩藏在地底下的死亡幽灵就会醒来,用它狂暴的力量掀去所有美丽的装饰。对此,南斯拉夫导演们有自己惯用的隐喻意象:一个能够容纳所有现实世界所拒绝看到的东西的地下世界。
《无主之地》里,两个穆族士兵和一个塞族士兵躲进战线中间的一个地下掩体。他们在这里演绎了一段相互冲突、争论、寻找活路的共同生活。他们甚至找到了一些能够连接他们战前美好生活的东西——共同的同学和情人。他们尝试相互理解,相互支撑度过这困境。在战争的现实面前,他们从“地下”找到了一些往昔的正常情感。但结局证明这只是假象。如果更深地向“地下”挖,他们作为个人所无力控制的民族冲突的巨大阴影又一次浮现出来。艰难达成的一些相互理解,仅仅因为一些无足轻重的误会就被抛到了脑后,民族主义思维就又一次猛地攫住他们。就在他们眼看要被救出“无主之地”,走上地面的时候,他们互相杀死了对方。没有人能够活下来,就这么绝望。
就像《暴雨将至》里,回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和他的旧友之间充满迷惘和无奈的对话:
——这里没有理由这样你死我活呀。
——他们会找理由的,战争就像病毒,把人们分成两边,我们一村,他们一村,人们露出狰狞的面目。
《战火硝烟》那条作为主要场景的隧道,同样位于地下。作为一个象征,这条被命名为“团结”的隧道,在它建成的时候,连接、凝聚了各个民族。但它不能长久地作为这样一个象征。很快,这条隧道蜕变成后铁托时代南斯拉夫的一个隐喻:仅仅十年间,它就成为一个废弃的黑暗洞穴,一个垃圾坑,一个掩埋罪恶以便外界粉饰太平的地方。所有见不得人的政治和人性的黑暗面似乎被一股脑地塞了进去,囤积、滋长、慢慢膨胀,变成传说中盘踞隧道的“怪兽”、“恶魔”。在传说里,它只是暂时睡着了,而一旦醒来,它就会吃掉村庄、烧毁房屋。很不幸,一切正如传说。
然而,《战火硝烟》有比其他南斯拉夫电影更深刻的地方。除了揭示民族冲突,它也没放过各民族内部的矛盾。不管塞族、克族还是穆族,在小到一小队被包围的人里,始终都是战争强行让这些人临时走到了一起:教授、小偷、农民、修车匠、瘾君子以及前南军队的军官。民族冲突暂时压制了民族内部的阶级、阶层冲突,以及铁托时代和后铁托时代两代人的冲突。但这种压制是暂时的,就如同从前对民族矛盾的压制。一有机会,它们就会冒出来,从“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一首首熟悉的歌,战前无论哪一个民族都爱听爱唱的歌,在被围困的隧道里流过。不管是由被困的塞族人用口琴忧伤地奏起,还是由穆族围困者嘲弄地唱响,都在一瞬间把人带回一个团结和睦的美好年代。每个人的故事在这样的歌声里穿插流淌,让我们看到他们是如何从各自完全不同的路,一直走进这死亡的隧道。每一条路都是民族走向分裂和战争之路的缩影。原来,那些美丽的歌从来就是假象、谎言,它们好像注定要在不知不觉中,把一切带向毁灭。
《战火硝烟》对人类前途充满悲观,即使那些民族冲突能够平息,要解决这其他的种种矛盾,真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同样悲观的是《地下》,它一开始就更关注民族矛盾以外的权力世界的黑暗方面。战后作为铁托政府要员的诗人马尔科以及他的朋友、作为革命先烈的“黑仔”,他们所有得到颂扬的“革命行动”、“英雄事迹”,实际都不过是出自私利的疯狂举动,惟一真正的动机不过是和德国军官争夺情妇,以及互相争夺情妇。革命胜利后,马尔科把所有这一切,连同“黑仔”等一大批了解过去的人埋进了“地下”,似乎所有不光彩的过去都可以因此被埋藏,他从此可以以一个革命诗人、国家领导人的光辉形象赢得世人的敬仰。马尔科甚至以此自欺欺人,就像他和情妇娜塔莉乐此不疲玩弄的语言游戏:
马尔科:我从不说谎。
娜塔莉:(陶醉而又伤心地)你撒谎撒得多么漂亮啊!
对库斯图里卡来说,历史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笑话,一出骗局,一场闹剧,所有的意义都是人们后来臆造出来的,这不由令人想起米兰·昆德拉。
但是埋进“地下”从来不是一个保险的办法。马尔科想尽办法维持了二十年,可他精心构筑的地下世界终于在一次意外中崩溃了。勉强维系的东西,它崩溃的结果,永远是变本加厉的爆发。马尔科终于不再用诗歌掩饰自己阴暗的欲望,他和娜塔莉成了国际刑警通缉的军火商人、战争贩子。而从“地下”脱身的酒鬼“黑仔”,又在二十年后的种族战争中找到了发泄暴力狂的途径。马尔科的武器卖给了“黑仔”,无意中他们又一次成为伙伴、搭档。只是时代变了,他们不再需要“革命”这块遮羞的红布,而是赤裸裸地展示人性之恶。库斯图里卡在电影里杀死了他们,但是他很清楚,他们所代表人性之恶,只要还有人活着,就不可能死光。
绝望的狂欢:暴力之花与人性之恶
前南斯拉夫籍的导演普遍倾向于将暴力诗化,拍得如同焰火般美丽辉煌,如同狂欢节般夸张无稽。《战火硝烟》里有一个塞族士兵原先是教授,到哪里都带着本书。从隧道里幸存下来的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朗诵书里一段美丽的描述:
有一夜,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加农炮正瞄准一个村庄,它正在燃烧。后来的每一夜,同样的时刻,村庄都在我们的视线里燃烧。我们仿佛被一种奇异的庆典仪式所包围,我们眼前所有燃烧的村庄组成了这样的仪式。火舌升腾,直冲云霄……美丽的村庄,燃烧时依旧美丽……
这样的描写会令人想起吴宇森的“暴力诗学”。但是南斯拉夫人要比吴宇森深刻得多,他们这么做,更多是为了直指人心,道出人性深处对暴力的某种崇拜,某种把暴力诗意化的原始本能。南斯拉夫导演们的一大本领,就是在描述本国血腥残杀的时候,总是能够让它的意义超出国家政治的界限,而揭示出某些具有人类普遍性的人性黑暗面。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表达了对人性深深的绝望。
《惊变世界》是以其粗砺的现实性震撼人心的。一种对人性的冰冷的绝望,通过不加修饰的对残酷事实的描述,传染给每一个观众。就在塞军攻打武科瓦尔,而安娜和她的朋友惨遭轮奸的时候,桌上的电视机里正在放映一部纪录片。透过女人们的惨叫,我们听见解说词这样说:
每一场战争都是在重蹈前人的覆辙。眼下我们的星球上正在进行的就有四十二场战争,它们可被分为三大类:内战、国际战争、独立战争……
真是绝妙的讽刺。南斯拉夫同时在打着这三种战争,这证明人类完全没有吸取教训的能力,或者像一位历史学家说的:人类历史的惟一教训,是人不能从历史吸取教训。正因为如此,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充满了暴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斯拉夫只是一个极端,一个缩影。南斯拉夫本身就像是这个世界的一个隐喻。
在《暴雨将至》里,导演米尔科·曼切夫斯基通过巧妙的结构安排,从血雨腥风的南斯拉夫“荡开一笔”,来到发达、安定得多的英国伦敦。但是这里同样无法逃避暴力的威胁。当女友问亚历山大为什么会厌倦战地摄影时,亚历山大深深吸了一口气:
罗马尼亚,啊?萨尔瓦多、阿塞拜疆、安哥拉、波斯尼亚?妈的,和平是例外,不是常规!
当晚,亚历山大的女友及其丈夫,在伦敦的一家餐厅,遭到一个外国怒汉的扫射,血流满地,起因仅仅是付钱时一桩小小的争吵。
《暴雨将至》里三个故事的发生地点,东正教修道院—伦敦—马其顿乡村,三者之间巨大的时空跨度就像一个巨大的拱架,或者说一组巨大的伞骨,人性的邪恶、暴力的泛滥,如同一把大伞籍此撑开,笼罩整个世界,无处可逃。
同样,《无主之地》不仅展示了民族冲突的绝望情景,更通过对蓝盔部队高级将领们种种愚蠢自私的行为的闹剧式描写,表达了对普遍人性的绝望。人类的处境,某种意义上,就像那个被遗弃的躺在地雷上一动不敢动的穆族士兵。再有任何的轻举妄动,迎来的就是粉身碎骨。但是躺着不动,仅仅是苟延残喘,因为没一个排雷专家能够能排除这颗人自己造出来的高科技炸弹。人在自己造出来的种种暴力工具面前等死,这就是导演丹尼斯·塔诺维奇对更宽泛的人类前景的隐喻,一个极度悲观的预言。
能用来抵抗这绝望的,只有狂欢。在醉生梦死的狂欢里,所有的忧伤和悲哀都被暂时遗忘。狂欢是毒品。再经不起现实的钝刀反复切割的神经,在狂欢中麻醉,寻找高潮的替代品。那美丽的燃烧的村庄,那哼着情歌进行的枪战,那在敌方的扫射下不顾死活的狂舞,那地下世界酩酊大醉的婚礼,那像火把一样被点燃的战争贩子夫妇和载着他们在广场上绕着圆圈一起燃烧的轮椅……一切都是狂欢,虚无的狂欢。
《地下》的结尾是天堂里的狂欢。所有死去的人,来到这美丽的地方,原谅了互相之间一切的出卖与欺诈,沉醉在疯狂的舞蹈和尖利的小号声中。这小号声与影片开头那醉生梦死的小号声如出一辙,但是经过近三个小时的实际电影片长和四十年的故事时间跨度,相同的小号声已经天人两隔。小号声中,大陆裂开。天堂小岛渐渐远去,留下现实的大陆继续经受血与火的煅炼。这大地的分裂不仅隐喻了一个国家的解体,更隐喻了一个世纪里实现人间天堂的美好理想和伟大创举的彻底终结。原来,一切都只不过是狂欢,个人的狂欢、民族的狂欢、世界的狂欢、人类的狂欢(一个朋友对摄影师亚历山大说:全世界都像看马戏团演出一样,兴高采烈地看我们你死我活)。狂欢之外一切皆无。狂欢是惟一的存在,狂欢是最硬的道理。看着狂欢中远去的天堂之岛,我的脑海中反复闪现两个字:幻灭。
轮回与错乱:结构的力量
很多人注意到《暴雨将至》特别的三段回环结构,在表现主题时的巨大力量,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暴雨将至》在结构上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圆圈。“要穴”是第二段“脸”里的一个镜头:亚历山大的女友在工作室的一堆照片中,看到了第一段“词”里那个被杀死的女孩和救女孩的年轻神甫。如果是一个封闭的圆圈,那第一和第二段之间应该是倒叙关系,而第二和第三段之间应该是顺序关系。女孩被杀应该发生在第一段之中,或者第三段之后,但无论如何关于这一事件的照片不应出现在第二段里。
因此第二段里出现的这组照片打破了影片所有时间上的逻辑顺序。时空在这一点上,就像爱因斯坦相对论,发生了弯曲,插入了其他时空的碎片。也就是说,《暴雨将至》的结构及其蕴含的时空观念,只是表面上像一个平面上封闭的圆圈,实际上它是立体的,就像在一个椭球体的表面,因此会有无数其他可能的圆圈与之交错而过,留下无数其他时空的碎片和痕迹。这组不可能的照片就像时空中的一个奇点,一个黑洞,一个神秘的伤口。时间不再是循环的河流,但它同样无始无终,充满分叉、断裂、开口,与被分割的空间交织在一起。轮回依旧,但它不再是单循环的,而总是存在从其他的路回到起点的可能性。这是一种更加丰富的错乱的轮回。如果只是平面的圆圈,那它不过是一种叙事策略,玩了个讲故事的花招而已,轮回并不真的存在。而用这种方式解读,轮回才是真实存在的,宿命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影片中反复出现的那句意味深长的箴言:
时间不逝,圆圈不圆
但是这样的时空并不意味着希望,毋宁说,它暗示了更大的绝望。总有人想打破封闭的圆圈,但如果无论你怎么破,你都依然只是停留在椭球体的表面,早晚要与起点相遇,那简直是暗无天日。《暴雨将至》用它极具创意的结构,仅仅靠三个支点和一个奇点,就轻巧地支起了整个人类生存的时空框架,把人类封闭在一个椭球状的时空上,充满这个时空的,是暴力。这样的想象甚至带有宇宙论的色彩,想一想宇宙和时空是如何诞生的?——答案是:大爆炸。人类用无数大大小小血腥的爆炸事件所制造的效果,只是在小得多的尺度上,对宇宙起源的模拟而已。暴力是宇宙的创生力,也是人类背负的原罪,这是暴力的辩证法。
与《暴雨将至》相反,《战火硝烟》的结构是一种轮回的错乱。全片一共有五条主线:
1.从1971年建成到1999年波黑战后重建,这条“团结隧道”的命运。
2.1980年波斯尼亚两个分属塞族和穆族的小男孩的友谊。
3.1992年波黑战争爆发第一天人们的种种行为和心理状态。
4.1994年贝尔格莱德军方医院,从隧道幸存的米兰和教授,如何再一次走上与穆族伤员同归于尽的不归路。
5.波黑战争期间,米兰所在小队被哈里尔所在的穆族军队围困在隧道里的十天。
所有这五条线索全被打碎,加上被围困在隧道里的每一个人,都插入他的生活片段,大量碎片和断线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就像南斯拉夫的民族矛盾与战争本身,精神分裂,神经错乱,难以理出头绪。但是你再仔细看去,这里分明到处有呼应,情节不断回到过去,既有回忆的忧伤,也有理性的探究——试图从表面上宁静的过去找出现在动乱的根源。最大的轮回来自首尾:二十八年过去了,隧道的建成和重建场面竟如此相似,甚至剪彩的官员都一样剪了自己的拇指,甚至从那拇指伤口流出的血都一样的浓烈、粘稠、令人恶心。
但这不是《暴雨将至》式的时间轮回。经过了二十八年,太多错乱的历史被容纳进来。这是意义的轮回,或者干脆说,这是无意义的轮回。虽然时光不会倒流,但它会漏掉,和它的“历史意义”一同,从某个没人注意的历史缝隙或者虫洞——比如“团结隧道”——漏掉。结果是,逝去的时光就像白过了,几乎没发生。人们又开始,白痴一样地开始一个新的但同样愚蠢的回合。
富有意味的是,这些意义深远的结构方式,在2001年的《无主之地》里再也找不到了。《无主之地》是一部小品,一出小剧场闹剧,它不再需要宏大的结构。某种意义上,它比此前的所有“南斯拉夫”电影都要悲观,因为它已经没有了讲述历史、探究意义的渴望。像《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样,它只想通过最微小的切口,虚构一种处境,展示荒诞。经过了整整十年饱含创痛的丰收期,“南斯拉夫”导演们的火山能量在渐渐冷却,流出的熔岩已经不再有席卷、熔化一切的热力和气势。他们的“史诗冲动”面临耗尽。即使是库斯图里卡和曼切夫斯基这样的大师和天才,他们后来的作品《黑猫白猫》、《尘土》,也已经没有了那种大气磅礴,只留下奇思妙想的小聪明。这又是另一种意义上令人无奈的轮回了。
本文提及的“南斯拉夫”电影一览
《暴雨将至》
出品:马其顿/英国/阿尔巴尼亚,1994
导演:米尔科·曼切夫斯基
主演:瑞德·瑟贝德兹娅/卡特琳·卡特丽德瑟/格雷高里·柯林/拉比娜·米特尔斯卡
奖项: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大奖/国际影评人协会费比西大奖/独立精神大奖最佳外语片(1996)/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1995)
《惊变世界》
出品:南联盟/塞浦路斯/意大利,1994
导演:博洛·德拉斯科维奇
主演:鲍里斯·伊萨科维奇/莫尼卡·罗米奇/尼波萨·格罗戈瓦奇/米拉·班热奇/米热娜·约科维奇
奖项:维罗纳爱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银玫瑰奖(1996)
《地下》
出品:法国/南联盟/德国/匈牙利,1995
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主演:米奇·马诺伊洛维奇/拉萨尔·里斯托夫斯基/瑟尔丹·托多洛维奇/米热娜·约科维奇
奖项: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大奖
《战火硝烟》
出品:南联盟/希腊,1996
导演:瑟尔丹·德拉戈热维奇
主演:德拉甘·布热洛戈尔里奇/佐兰·克维亚诺维奇/尼古拉·科约/德拉甘·马克西莫维奇/米洛拉德·曼迪奇/德拉甘·佩特洛维奇
奖项:1996年圣保罗电影节国际大奖/斯德哥尔摩电影节铜马奖/鹿特丹电影节最佳外语片。
《无主之地》
出品:波黑/斯洛文尼亚/意大利/法国/英国/比利时,2001
导演:丹尼斯·塔诺维奇
主演:布兰科·德约里奇/雷尼·彼托拉亚奇/菲利普·索瓦戈维奇
奖项:戛纳电影节最佳剧本/欧洲电影奖最佳欧洲电影/恺撒奖最佳处女作(2002)/金球奖最佳外语片(2002)/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