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6年10月6日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这一紧要历史关头,耿飚和邱巍高奉命进驻中央广播事业局,夺回了多年被“四人帮”把持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及其所属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领导权(以上简称“中央三台”),控制了重要的新闻宣传舆论阵地。这一重大举措,是粉碎“四人帮”行动的一部分,在人民广播事业和“中央三台”的历史上,想是不可忘记的重大事件。
对于这一重大行动,近年来有一些当事人和亲历者发表谈话或写回忆文章,披露了当时的内幕,也有人依据史料或运用推理编写了一些有关故事,其中对耿飚等人进驻广播局的时间,以及进驻后发生的一些事众说纷纭,甚至自身前后矛盾。粉碎“四人帮”时耿飚“进局”,其主要活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时我任中央台副台长,分管宣传工作,目睹和参与了其中的某些活动,并即时作了记载。1994年我发表了《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一文,1997年收入《我与广播》一书。后来,一些读者和朋友不断向我打听有关的情况,印证和核对某些说法;北京广播学院原副院长赵玉明教授,他几十年专门研究广播、电视史,多次希望我能“澄清”一下,对历史有个交代,不然后人更难以弄清楚。我感到从对历史对读者负责来说,也应该弄清楚、弄准确,但我翻阅了一些有关文章和史料,访问了一些当事人以后,仍然感到很难把疑点说清楚,甚至头绪越来越多,只是把几个主要问题的分歧点摆出来,供读者鉴别。
耿飚是在什么时间进驻广播局的?
对此,耿飚本人有过3次、两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次是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以后,1977年10月18日,新华社召开国内工作会议,借用广播局的广播剧场,请当时主管中央宣传口工作的耿飚作报告,我列席听报告。根据我的记录,他一开始就说:“今天开会,选择电台的地方,使我回想起去年我到过这个地方。今天是几号?(去年)10月6日抓起来‘四人帮’,是下午8点零5分抓完,我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同志到电台来是晚上7点多,不到8点。一进门,就闯到了邓岗同志办公室。”这是我听到的他的第一次回忆,也是距离粉碎“四人帮”后最近的一次回忆。因为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也就特别在意。后来,有人写文章与耿飚说的抓“四人帮”和进驻广播局的时间不一致,1990年12月24日,在政协礼堂举行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台50周年联欢会”上,耿飚应邀出席,我特意向他问起这个问题。他说:“我的记忆是准确的。”
第二次是耿飚在《一场特殊的战斗》一文中说:“(10月6日)我们到广播大楼已经将近晚上10点钟了。我们直接到局长邓岗的办公室。”很显然,这与以上“进局”时间的说法差异很大。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还特意说明:“我在广播局只工作了10天时间,但那段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不少报刊文章和书籍写到粉碎‘四人帮’时,涉及到这个问题,但其中有些描述与事实有出入。常有一些同志问我当时的真实情况,现将我到广播事业局前前后后的一些事情记述如下。”可以看得出,耿飚写这篇文章是非常认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有很强的针对性。
第三次是在《耿飚回忆录》第八章《春风又绿中华》中,谈到这一事件时说:(10月)6日晚上8点来钟,华国锋把他叫到中南海怀仁堂布置任务。“我们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我们在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我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可以看出,以上3次关于“进局”时间的说法有两个版本:10月6日晚上7点多到8点;晚上将近10点。“第二”与“第三”次是一个版本,都与“第一”次说的不同,相差几个小时。对于“第二”、“第三”次的说法,还有张香山的旁证。当年,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张香山不是与耿飚同一时间“进局”的,晚了几个小时,是耿飚打电话把他召去的,他不是首次“进局”时间的亲历者。但他不仅参与了当晚的活动,而且在耿飚离开广播局后他继续留任,并在后来接替邓岗任广播局局长,在位5年多。他在《在第一线的最后五年半》的回忆文章中说,那天(10月6日)晚上他到广播局后,耿飚就把自己来后的经历告诉了他。耿飙对他说:“大约当天晚上8点过后,应华国锋的召唤,他去了怀仁堂。”随后,耿飚等人“乘上他的红旗轿车离开怀仁堂。到了广播事业局,进了大楼就到局长办公室”。这里没有具体说出耿飚等人“进局”的时间,但却印证了那天晚上8点后耿飚仍在中南海怀仁堂,那么“进局”必定是在这之后。而且,这是那天晚上耿飚告诉他的,显然有即时性,应该是事实准确、记忆清晰的。

但是,还有另外当事人和目击者的记述。
首先,最清楚的应该是局长邓岗。耿飚“进局”第二天的7日晚上10点30分,邓岗召集“中央三台”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开会,他开头就说:“昨天晚上8点30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来局,带来了华国锋总理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接着,他就宣读了这封信。
另一位当事人,是当时任广播局总编室副主任的杨兆麟。他在《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一文中说:“1976年10月6日晚上,大约7时许,我和老戴(广播局总编室副主任戴临风)正在二楼的总编室值班。忽然,办公室的门一开,耿飚同志走了进来,神情非常严肃,问我们:‘邓岗在不在?’我说:‘就在对面’。”(见《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随后,他带耿飚等人到邓岗办公室门口。广播局总编室与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是同在一个大门里的两个房间,中间有一个过间,西、东两个门相对,耿飚等找错门是完全可能的,杨与耿又是认识的,杨应该是接待耿“进局”的第一人。尽管只是说“大约7时许”,前后也不会差得太多。杨还在其文章中特意说明,他这篇文章是专门为澄清“史实真伪”而写的。他说:“事关重要史实,我感到有必要以亲历者的身份,向人们提供真实的情况,免得再以讹传讹。严肃地陈述历史的真相,是亲历者们的历史责任。”
还有我。我在《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一文中说:“1976年10月6日晚7时左右,秋天的夜幕已经降临,有几位未经打招呼的不速之客走进北京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径直走进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杨正泉《我与广播》)我这样写,来自我的直观。文革中大家养成了一种“惯性”,不分上下班的时间,每天晚上6点吃完饭,就回到办公室,有事没事一直待到很晚。我的家离电台很近,那天吃完晚饭回到电台,正在院子里散步,忽然见几个穿军装的人从北门而入。多年来有一种政治敏感,1976年发生的大事又太多,而且是毛主席的治丧宣传刚结束不久,好奇心驱使我看着他们一直走进大楼。后来看到电台岗哨增加,警卫战士不断走动,预感发生了大事,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是耿飚、邱巍高带人进局。那是在晚饭后不久,又是暮秋时节天黑不久,我推断为“7时左右”,这与杨兆麟说的晚上“大约7时许”,与邓岗说的“晚上8点30分左右”,与耿飚1977年10月18日说的“晚上7点多,不到8点”,前后相差不多,但与耿飚后来说的“将近晚上10点”,就相距较远了。
第四位见证者是中央台时政记者刘振英。2006年1月20日,我与刘振英在参观完中国电影馆回来的路上,谈起当年耿飚、邱巍高“进局”的事。他开口就说:“(1976年)10月6日晚上天黑不久,我在大楼院子里散步,就在大楼门口花坛旁边碰见了耿飚和邱巍高。过去我们很熟悉,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我有点惊讶地打招呼:‘你们来了!’他们也认出了我,说:‘你在这里。邓岗的办公室在哪里?’我说:‘在二楼。’多年养成的习惯,我不便问他们来干什么,就把他们带进大楼里,但没有跟着上楼。”我问他:“你想一想是晚上几点?”“大约7点多,不到8点。”“会不会是晚上10点左右?”我进一步问。“不会。天刚黑不久。要是晚上10点,谁还在散步?”他说得非常肯定。他不仅见证了在时间上相近,而且他直接认出了是耿飚和邱巍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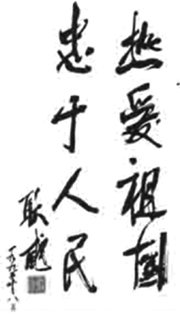
我们都是认真的,可哪个时间是准确的呢?事情还没有结果。
耿飚是在抓“四人帮”之前还是之后来广播局的?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关键情节,到底是在什么时间抓起了“四人帮”?耿飚是在抓“四人帮”之前还是之后“进局”的?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他到广播局的时间。
在我听到的耿飚1977年10月18日的回忆说,“10月6日抓起来‘四人帮’,是下午8点零5分抓完”。据当年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在《逮捕“四人帮”亲历记》中回忆,中央是在通知“四人帮”10月6日晚上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时,先后将“四人帮”逮捕的(《我的1976》)。可以看出,耿飚与邬吉成的说法基本一致。
按照耿飚这次说的“我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同志到电台来是(6日)晚上7点多,不到8点”。显然,他们是在抓“四人帮”以前最关键时刻来到广播局的。这与耿飚10月18日那次讲话的统篇内容是一致的。他说:“现在清楚了粉碎‘四人帮’时为什么去占电台?并不是对电台不信任,是怕‘四人帮’哪一个漏掉了,走漏了消息,出乱子。先把电台控制住。”他说,把广播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召集起来和控制住了中央台直播室后,他“然后打电话向华主席汇报,已控制住了,请放心吧!华主席说,一切都如意。我就理解了,‘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依此而论,明确无误地说明是在抓“四人帮”以前了。如此看来,如果按照耿飚在后来两次回忆中所说,他们是在6日“四人帮”被抓起来之后的“晚上将近10点钟”才“进局”是不确切的,高潮已经过去,那不成了明日黄花?
但推论不等于事实,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可以看出,耿飚在后来的两次回忆中,是非常认真的,而且说得非常具体。他说:“6日晚上8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听得很真切,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耿飚回忆录》)到怀仁堂后,“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叶帅也作了指示。耿飚向华国锋要了手令后,他们“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了”。
而且邬吉成在《逮捕“四人帮”亲历记》中说:“王、张、姚的事一处理完,华国锋、叶剑英指示耿飚,立即率部队接管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这印证了耿飚是在抓“四人帮”之后进局的说法。但这段回忆中有的事实与后来的实际不准确,事实上耿飚并没有“率部队”,也没有去“接管新华社”,而只是进驻“中央广播事业局”,也不是直接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当然这些事实的偏差,并不影响他对时间记忆的准确性。
另外,武建华在《中华儿女》杂志上发表长篇报告,详细记述了《粉碎“四人帮”的策划过程》。那时,武建华是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他直接参与了逮捕“四人帮”。他在回忆中有一段记录解答了这个问题。为说明起见,我详细引录如下:
武建华说,10月6日晚上7点55分,先抓了“四人帮”中王洪文,最后抓了姚文元。他说:“在我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报告,奉命完成拘押姚文元的任务时,认真地看了看手表,正好是10月6日晚8点30分。也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全部行动过程,只用了35分钟。”
他说:“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后,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并处理善后工作。”“华国锋对汪东兴说:‘你通知政治局开会,我找耿飚他们来作个交代。’”
武建华回忆说:“华国锋亲自打电话给耿飚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请他们立即到怀仁堂,有事面谈。不多一会儿,耿飚、邱巍高奉命赶到。华国锋告知他们,我们对‘四人帮’已经采取了行动,并取得了胜利,王、张、江、姚已被隔离审查。现在派你们带领精干的工作组,立即去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在那里掌握情况、把把关,不要在宣传这个口子出毛病。”
武建华说:“叶帅特别嘱咐了两点:一是防止内部混乱;二是防止对外泄密。还要预防发生异常情况。”
然后是华国锋问他们还有什么问题,耿飚提出要一个手谕,华国锋就提笔写道:“邓岗同志,为加强广播事业局的工作,特派耿飚、邱巍高来,有什么问题,你请示他们。华国锋。”

“耿、邱受命而去。”
(在此说明,根据《耿飚回忆录》第八章《春风又绿中华》中的记载,根据我在10月7日晚邓岗传达华国锋亲笔信的记录,华国锋手谕的全文是:“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我认为,这是准确的。)
至此,对耿飚等人是在什么时间进驻广播局的事应该说是清楚了,应该是在10月6日晚8点30分粉碎“四人帮”之后,“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了”。但为什么会出现耿飚几次说法的不统一?为什么广播局目击者、见证者的记忆又如此一致?彼此都是认真的,为什么误差却如此之大,版本又如此之多?依然是个难以说清的谜。
邓岗是在什么时间召集局各部门领导会议的?
耿飚等人进局后,首先向邓岗出示了华国锋的亲笔信,然后召集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开会,也包括了局的全体领导成员。我不是局核心小组成员,当然也无从知道会议的情况。当天晚上,通知“中央三台”和各局机关、单位的领导11点去开会。大家按时到会,会议室在局总编室,如前所述,与邓岗的办公室对门。晚上11点零5分,局长邓岗和第一副局长张振东、副局长顾文华神情严肃地走了进来,邓岗宣布了紧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立即清查节目,明天的广播电视中不准再出现。会议时间不长,但很重要,与会者事前已感受到局内异样的气氛,听了邓岗的布置自然会敏锐地觉察到发生了大事。为什么是晚上“11点零5分”?因为邓岗比通知开会的时间晚到了5分钟。我为什么会记得那么准确?因为我已预感到了事情的重大,而且多年养成了一种习惯。
对这次会议,耿飚在《一次特殊的战斗》和《春风又绿中华》中都有记载,而且都说是在“23点40分(注:晚上11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依据我的原始记录,耿飚的回忆肯定是记忆有误。在局里开会回来后,也正是在23点40分,我召集了中央台各部门负责人的会议,布置立即检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
什么时间是谁要去了中央台直播室的钥匙?
控制住中央台的直播室,防止意外播出事故发生,是耿飚“进局”的重要任务之一。那么是谁、在什么时候收缴的直播室钥匙?
对于当时的情景,我在《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一文中说,当我看到电台“增设了岗哨,增设了值勤人员,而且是全副武装”以后,“为了探个明白,也是责任心所驱使”,我去了节目传送间和直播室。“不一会儿,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张香山急急忙忙来到直播室,坐在直播室门前的两个沙发上寸步不离。然后把我叫去吩咐,赶快把直播室的钥匙找来,交给他们。他们坐等。”(《我与广播》)我前后找了半个小时,才交给他们,并打开门,请他们参观了尘封多年的直播室。然后,他们就向耿飚作了汇报,耿飚随即打电话向华国锋报告了平安无事。

我清楚地记得,交直播室的钥匙是由冯铉、张香山向我布置,由我找到交到他们手里的。这一事实是不会错的,对冯铉和张香山我是认识的。什么时候交的钥匙?我的记述不具体。按照时间推论,耿飚在《一场特殊的战斗》和《春风又绿中华》中的说法是,在他“进局”控制了局党的核心小组和中央台直播室的钥匙并向华国锋汇报之后,觉得人手不够,才“立即打电话到中联部,把张香山和冯铉两位副部长请来,还找了其他一些同志”。按照时间推论,耿飚“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了”,那冯、张到达广播局和交钥匙的时间怎么也要在晚上11点以后了,而且应该是在邓岗开会布置清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之后了。但耿飚说,冯、张“进局”之前,他已经控制了中央台直播室的钥匙。对此,张香山在《在第一线的最后五年半》一文中也是这样回应的:他到达广播局后,听耿飚介绍情况时说,“耿飚同志还叫邓岗把直播室门上的钥匙交给他保存”。张香山说,耿飚向他们交代的任务“就是监听录制好的节目中有无‘按既定方针’这句话,如果有,必须删除”,也就是说,并没有提到要他们到直播室拿钥匙的事。但张香山在文章中却用很长一段文字记述了他们去直播室参观的情景:“我曾抽空和冯铉一道去看过直播室,它尘封四壁,简直像间废屋一样。伴我们去的局里同志说,已有十几年不用直播室了,因为在左倾之风日盛时,广播员念错一两个字,就会被上纲到政治问题,所以大家就一律采用录音放送,而不用直播。桌上的话筒还顶用不顶用,也没有人去试过。”(《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回忆录》第二集)在这里,张香山成为交钥匙的旁观者,而不是当事人。我认为,一、交接直播室的钥匙不会、也不应该是耿飚与邓岗之间做的事;二、如果按照张香山所说,“参观”直播室的时间应该是在第二天(7日)凌晨了,因忙于审听节目,时间安排上不可能;三、张香山说的那个“伴他们”参观的“局里的同志”正是我,那番话也是我说的。在我交给他们钥匙之后,他们要打开直播室看一看,以确认钥匙和直播室的真实性,是在观看的过程中我说那番话的,香山同志精通日语,用了“放送”一词,而我用的是“播放”。
至于杨兆麟在《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一文中说,“事实上,播音区内根本没有什么专门的‘直播室’”,显然这不是事实。他还说:有一些文章中有的说当时直播室的钥匙掌握在他手里,耿飚要他把钥匙交出来;有的说杨兆麟“看了华国锋的手令以后”,“才被迫交出了莫须有的钥匙”(《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显然,这些都是编造的误传,都不是事实。至于为什么把误传安到了杨兆麟的头上,有可能是把我们“二杨”弄混淆了。
10月6日夜里有没有工作到通宵?
与以上问题相比较,这是一个不大的问题。问题的提出,是杨兆麟在《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一文中说,10月6日晚,耿飚和邓岗没有向总编室布置“检查明天要播的录音带,凡是有‘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一律剪掉”等任何任务,因为那时“有关广播电视宣传工作,局领导一直都是经过总编室,直接向‘中央三台’下达任务”的。因此,也就不存在“需要紧急动员一二百位编播人员、技术人员彻夜不眠来赶任务”的问题,“那一夜,我是目击者、亲历者,编辑部、机房和平时一样,没有任何异常”(《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显然,这一记忆与那天晚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不知北京电台(中国国际电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实际情况如何,中央台全台人员是彻夜通明地在按照邓岗的新布置,检查、审听和录制节目,准备第二天的播出。
呜呼!从1976年到2006年,事情才过去30年,有些当事人、亲历者和目击者还健在,但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件事却有着不同的记忆,同一个人对同一件事前后也有着不同的记忆,可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之难;同时期的人对同一事实有着不同的记忆,更不要说见解的分歧,那么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对同一历史事实的看法又将如何?更是千差万别、甚至是完全相反,这是常有的事,可见写历史之艰难。历史上存在许多疑案、谜团,演绎成神秘色彩的故事,但事实只有一个,也许真实的事实却非常简单。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