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
张朝阳:读清华很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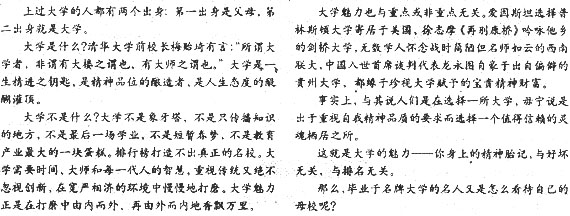
我是1981年上清华的,当时清华的文科系还不多,工科学校的特征明显。学生念书非常疯狂,也非常单纯,很少看电影、电视,与外界隔绝,一心只想攀登科学高峰,对科学有一种宗教式的狂热。“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个口号就是清华学生提出来的,还有一个口号,“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说的是工作、学习都是为了祖国。
当时挺土的,穿衣服特别单一。看到当年留下的照片,特土气,一副书呆子的样子。念书念得很苦,每天一大早跑步,早早到教室占座位,而且是坐前排;中午午休之后又上课,晚上自修室里坐满了人。清华学堂也就是最早的留美预校,都是绘图桌子,特别大,灯光也特别亮,最难占座。
但当时并不把苦当一回事,认为是去追求更高的理想。因为压力、竞争太厉害,清华出现了一些怪才,像写诗的清华文学社,还有一些其它文艺社团。而男女比例太失调,许多男生处在极不平衡的状态。枯燥的生活,精神上的苦闷,以至于转向了哲学上的追求;经历了很多痛苦、苦闷、内心的奋争之后,导致了一种自我怀疑。这不足清华一个学校的问题,而是整个教育制度的问题。
在清华的最后一年是最轻松的,因为考到了奖学金,知道自己可以出国了,那是一种中了状元般的感觉,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不需要竞争,也就不想念书了。厌学是肯定的,太苦了,没怎么享受过生活。而且,这么苦,却学不到任何东西。这么多人在一起做同样的事情,一起吃,一起睡,做一样的功课,就像一个小社会,分数就是一个人的身份。其实特没意思,学习效率极低。
清华对我来说,就是人生的一段经历,这是因人而异的。
张朝阳:搜狐CEO,1981—1986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复旦大学
王长田:我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复旦度过的
因为从小到大老师们的鼓励,高考填报志愿时我报的全是新闻系,复旦是第一志愿。都说复旦新闻系是全国最好的新闻系,复旦的生源也确实是好,我们那个年级(84级)一共有13个高考状元。
我的四年大学生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半部分也就是1984-1985年,那是复旦非常好的一段时期,学习气氛浓厚,天天晚上都有讲座,选修课达五十多门。那时我们最大的遗憾就是一个晚上只能听一个讲座,上一两门课。后半部分由于人环境的原因,人家都很迷茫,烦躁得不得了,也就开始玩。每天晚上好几个舞会,还有很多人进不去。再有就是谈恋爱。也就是在后两年,复旦那种生活的、小资的情调完全体现出来了,并且延续到以后。从复旦出来的人都能把生活安排得很好,有小情调,注意礼貌、细节。复旦好像出不了叱咤风云的人才,它出的人,精细、敬业,是职业型的人才,最适合做白领、职业经理之类。
复旦的特点与上海这座城市有关。上海籍的老师、学小多,上海人的性格也就深深影响了复旦。一方面,我队为,在对自我、个性的尊重这一方面,复旦是要高于别的学校的;另一方面,上海的同化作用非常强.令人无法抗拒。我的很多同学现在就是生活、家庭第一,事业有没有就算了。把他们放到外地会好一些。
复旦还有一个很著名的特点,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出国是他们的重要目的,孜孜不倦地追求。现在山还是。
在当时我们的心目中,它是“江南第一学府”、“南方的北大”,很多方面可与北大媲美甚至还要强,可以代表南中国。当时我们都是不服北大的。
我在复旦的生活,可谓丰富多彩:当书画协会会长,写诗(当时写诗是被人当英雄来崇拜的)。当时的状态,很单纯。也很投入,现在想来,可以这么说,我一辈子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大学度过的。同时我还要非常感激复旦的是,我刚上学时得了肺结核,校方并没有让我退学,而让我留在上海治病。否则真的可能把我给毁掉了。
王长田:北京光线电视策划研究中心总裁,1984—1988年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系
中国科技大学
蒋继宁:我真的很幸运
说起科大来,普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少年班。虽然科大值得一提的还有很多,不过创办少年班,探索超常教育规律,确是中外教育史上的创举,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少年班确实培养了不少人才,像美国IEEE学会历史上最年轻的31岁院士、微软中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业勤博士;33岁担任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副所长的计算生物学家钟扬;29岁荣获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联合授予“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学位获得者”称号的周逸峰教授。……实在不胜枚举。
我进科大读少年班时,还是个孩子,好胜心强,特别不服气,生怕不如人,每天一大早起来就和大家一起飞奔到自习室占座位,晚上还要去通宵教室开夜车。所有的通宵教室和自习室都人满为患,走进去黑压压一片人头,都在埋头苦干。五年下来,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比起其它学校,尤其是文科院校的同学,也许缺少一些浪漫的记忆,也几乎没有风花雪月的故事,但我并不后悔。我从中学到的知识,练就的坚强意志,培养的刻苦精神,是我一辈子享用不尽的财富。
科大是1970年从北京迁到合肥的,从此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少了许多热闹和关注。合肥是一个安静朴实的小城,科大也是一所安静朴实的学校,不浮躁不跟风,脚踏实地,奋发向上。在这个纷繁扰攘的世界上,质朴是一种越来越罕有的气质。而科大的质朴又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那种。这是一所有传奇传统的独特大学,她还在继续演绎着传奇。曾为科大人,我心中充满自豪。
蒋继宁:网大(中国)有限公司总裁,1984—1988年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
南开大学
姜奇平:南开的困惑是中年有产者的困惑
南开人务实,注重的是有没有根基,立得稳不稳,在做实事方面很突出。所以从南开出去的毕业生中,特别大的官儿没有,都是中层干部,业务骨干型的。南开培养的是栋梁型的人才。在这一点上,南开像清华。去年我回南开作演讲,学生们关注的是网络对人文的影响,而不是休学创业这类时髦的话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南开不能应变。当年南开率先开办心理学系、社会学系,说明她并不是因循守旧的。像中文系的叶嘉莹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可称得上是异类,但他确实是在南开作出了创新。只要能真正提出新见解,就能被南开人接受。只是,南开是属于内向型的,她倾向于渐进改革,而不是根本性的变革,可以概括为“小步快走”。今天的南开给人的感觉是,本来有一个好基础,应该有大的发展,但步子慢了。打个比方,南开像一个中年人,还没有衰老;但当她面对青年人的时代,一方面因为有家有业,不能轻装上阵,另一方面对各种新生事物不免困惑。
她希望用成熟的方式反映不成热的现实,当她面对暴发户的刺激时,她也想赚大钱,但又想用稳妥的方式去赚,于是矛盾。这种困惑,是典型的中年的困惑,有产者的困惑。
从我的角度来看,南开注重实力,认为只要有实力,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被抛弃;然后在稳定的发展中慢慢地寻求变革。南开出的不是冒尖的人才。有领导在上面指方向,他就在下面埋头苦干。像周恩来,稳重,但决不保守。其实,从广义上说,今天任何一个大学都面对变革,如果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挑战,都可以说是保守。清华属于创新型的,能适应变革,很快产生新东西;北大的步子慢一点,但一适应,前景可观。而南开,更多的是矛盾。
所以我的看法,是要打破校内外的区分,让学生自由去发展,成就“知本家”。
姜奇平:IT评论家、《互联网周刊》主编
浙江大学
李杭育:新浙大很生猛
杭州的几所好学校现在都合并了,统叫浙江大学。我在20年前就读的杭州大学中文系,现在并入了浙大的人文学院。几乎是刚一开张,这个“人文学院”就大爆新闻:他们聘请了写武侠小说的余庸当院长!有人说好。肯定浙大利用金庸的名气打人文学院乃至整个浙大的知名度是聪明之举。当然也有人很反感把办大学搞成类似“追星”的一番炒作,说堂堂浙大要靠金庸打知名度,要么是太自卑,要么是真悲哀。
但不管金庸这件事的得失如何,新浙大在吸引人才、壮大师资实力上,倒是真肯花血本的。不久前我和几十位朋友在杭州的三联书店参加了一个欢迎北京学者汪丁丁的酒会。汪丁丁受聘于浙大经济学院,同时仍兼任北大教授。浙大的“开价”之一是花几十万给他一套房子。在那个酒会上,汪丁丁说他来杭州是打前站的,接下来还将有好几位北京学者来浙大任教——譬如汪晖。他不愿透露得太早太多,只说在他后边还有“一大坨”。新浙大有这番新气象,此等“生猛”,该当我的晚辈校友们有幸。
李杭育:作家
南京大学
叶兆言:南大不可能咄咄逼人
要我评价南大,挺难;尽管我在南大中文系上了7年学,而她也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也许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吧。
印象比较深的是,南大的学生读书用功、实在,这是她的一个好传统。但现在很多学生毕业出去之后往往要改行,他们是不是会有学了也白学的感觉?
据我所知,南大的理科很棒,这恐怕就是她的排名靠前的原因吧?但要说到挑战北大清华,恐怕还不太可能;至于说南大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那更是不可能的事。南大还是南京人的传统,而南京人一直是谦和的。
我的看法,上不上大学很关键,但上哪一个大学不重要。如果你真的有本事,在任何一所学校都可能会非常好。自学最重要。
南大的校园在市中心,这是她不利的一面,限制了发展。
叶兆言:作家
中山大学
陈平原:同志仍需努力
我不只一次碰到如此知根知底的提问:“希望比较一下北京大学与中山大学这南北两大学的异同。”“比较”不敢轻言,感受还是有的。
求学燕园,须有定力,把持得住自己,方能闹中取静,走自己的路。虚荣之心,人特有之,拒绝成为“闻人”,其实不容易。生活上甘于淡泊者,未见得就能抵御得住“多快好省”迅速出名的诱惑。相对来说,生活在远离政治及文化“中心”的康乐园,寂寞些,却容易保持独立思考。假如不考虑一时一地之得失,照毛泽东所说,“风物长宜放眼量”,我真的不敢指定燕园的读书环境就一定比康乐园好。
我写过一则短文,提及中山大学小礼堂上镌刻的中山先生题词“学生们要做大事,不要当大官”不翼而飞,中大的朋友很不以为然;因题词并未永远消失,只是整修时暂时被覆盖。那是中大的精灵所在,师生们借此保存一方纯洁的精神领地,没想到竟被我无端“抹杀”了。对此,我一方面深表歉意,一方面为母校之不曾随波逐流而大感欣慰。
近年,广东的新闻业发展神速,继饮食、服饰以及流行歌曲之后,发起第X波“文化北伐”。大喜过望的京城读书人,于是有了“岭南文化崛起”的惊叹。如此称誉,虽则大快人心,却非我所敢贸然认同。在岭南,只要真正肩负“文化复兴”重任的“思想学术”羽翼未丰,“崛起”一说,便有待时间的检验。这也是我对母校寄予厚望、因而也就略有怨言的原因。
陈平原:北大教授,1977—1984年就读于中山大学中文系
武汉大学
窦文涛:武大是全国风景最漂亮的学校
我对武大最深的印象,是她的风景;跟人提起武大时,我说得最多的就是:武大是全国风景最漂亮的学校。这样的地方,每一天都有不同的风景,每一天都有不同的颜色和味道,太适合年轻人,我惟一的遗憾就是读大学时太傻,笨笨地,不会玩。
现在想来,当时来招生的那个漂亮的武大女老师对我就有一定的吸引力,她说武大是全国风景最漂亮的地方,这几乎已决定了武大是我惟一的选择。也许当时我还会考虑到武大是一所重点大学,图书馆很大,有许多名人像闻一多、徐志摩都在那里呆过等等;上武大时也在琢磨同学间怎么相处、考试怎么作弊等现实问题,但时隔10年,我对武大剩下的回忆,就只有风景。就像电影残留的胶片,主角淡出,影像剥落,只留下了背景:湖、山、树、樱花、那一场雪、看电影的地方、小酒馆……至于是跟谁看的电影、跟谁喝的酒,或者是跟某个女生似是而非的恋爱,都不重要了。
在我看来,读大学在本质上是选择一个地方生活4年,有人选择好教授,有人选择好传统,有人选择好的毕业分配机会,而我的守护神为我选择了风景。像我这样的性格,就应该选择一所风景最漂亮的大学。谁也不能教别人怎么上大学,每一个人不同的大学故事,其实都由自己的性格所决定。
至于师资力量、校风、学风这些东西,我不感兴趣,传统是别人做成的,校风是别人总结的,跟自己没关系。有千千万万的人上过这所大学,我不认为能形成一个统一的看法。一万个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大学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精彩万分。我觉得大学应该是这样一个地方,让一个学生如何拥有——段精彩生活的回忆;而说起大学,是听几个大学生讲他们的大学故事,独特的环境、人、故事,这才具有审美的价值。
窦文涛:凤凰卫视主持人,1985—1989年就读于武汉大学新闻系
兰州大学
水均益:兰大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
我是1980年上兰大的,当时只有16岁。本来我是报考北大、上外的,因为年纪小,母亲动用了一点特殊关系把我留在了兰大。但我不后悔上兰大。
因为父亲、伯父都在兰大任教,我对兰大有特别亲切的感觉,像半个家似的。70、80年代的时候,因为支援大西北,也因为“文革”时期不少优秀教师滞留在兰大,兰大的师资力量相当雄厚。而且兰大也注重改革,像我上的外语系在我上大一时就请了外教,算是比较早的。这对开拓眼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毕业分配到新华社,同时分进去三十多个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北外、上外、北大这些名牌大学出来的不少,大家互相交流,我自己感觉不错,没觉得水平比别人差多少。
因为地处西北,兰大的名气相对来说较小。我跟人家说我来自兰大,总有人觉得我念错了字,应该足“南大”。这时候我就会很认真地跟别人说明,而且要列举数据、事实。可以说很好胜,很捍卫兰大的名誉。这是兰大人的一种心态,不愿意别人瞧不起他们。
兰大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历史,出了不少人,像《读者》就是兰大的一帮人创办的。兰大在冰川冻土、沙漠治理、现代物理、量子力学等领域有着独特的贡献。从名声、资源、经费等方面来看,兰大力量相对单薄,不可能有很大的手笔,但兰大一直孜孜不倦地想尽一切办法靠近国家的前沿。今天的兰大在师资力量上有所流失,生源也不像原先那样广泛,局限在西北地区,多多少少会影响质量、实力。可以说,实力是有的,但对外形象的包装、宣传不够。实际上西部高校都面对同样的问题。
兰大的校园环境不错,在西北这种飞沙走石的环境中是很少见的,是兰州老百姓的一个景点。而兰大的存在在西北绝对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如果没有兰大,很多学生就会失去成长的机会。
水均益:中央电视台主持人,1980—1984年就读于兰州大学外语系
(赵平摘自《新周刊》2000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