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谈》是鲁迅1927年7月16日在广州一所中学的演说词。八十年后我们在中学课堂上来读和讲这篇演说,自然是别有兴味的。我们不但关心鲁迅讲了什么,更关注他是怎么讲的,也即演说的姿态、内容、讲法、演讲者与听众的关系,等等。
一、“随便谈谈”

鲁迅在演说一开始,就点明自己是来“随便谈谈读书”。这大概有两层意思。首先是并无特别的设计,也无深意,不过是“忽而想到”就“随便谈谈”。下面谈到读书时,鲁迅也说要抱“随随便便”的态度,不要一本正经地摆出一个读书的样子:“我在读书了!”鲁迅还有一篇文章,也是谈读书的,题目就叫《随便翻翻》,这都是在强调,无论演说,还是读书,都不要端架子,要自自然然地,兴之所至地讲和读。其次,还要强调,因为是“随便谈谈”,所以讲的都是“个人的意见,姑且供诸君的参考”,就是说,不是来作“指导”,也不是来作“指示”,而是发表一己之见,不过是“姑且”讲之,听众也就不妨“姑且”听之。
这样讲,不仅是为了缩短和听众的距离,更是一种演说者的自我定位,这就是鲁迅在另一篇演说《关于知识阶级》里所说的:“我并不是站在引导者的地位”。鲁迅一再说,自己绝不是“导师”,当然更不是“国师”,道理也很简单:自己并不掌握真理,只是一个探索者,连路都不知道该怎么走,如何给别人(包括中学生听众)指路?他因此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告诫年轻人,千万不要轻信那些“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不过能说话”,“不过能弄笔”,“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要他们当导师,是绝对不可以的,甚至是有害、危险的(《导师》)。
二、“杂谈”与漫说
“随便谈谈”不仅是一种演说的姿态,也决定了演说的内容、方式、结构:“杂谈”与漫说。不仅“杂”,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而且“漫”,东拉西扯,漫无边际。忽而“职业的读书,嗜好的读书”,忽而“文章和文学”的区别,忽而“弄文学,看什么书”,忽而“如何看待批评”,忽而“读世间这一本大书”:就这么不断地转换着话题。在具体展开时,就更是随意举证,枝蔓旁出。又是“木匠磨斧头”,又是赌徒“打牌”;又是“在抽屉里暗看《
红楼梦》”,又是“到广东吃荔枝”;又是创作家脑子“发热”,又是教授摆“架子”,等等,等等。真可谓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思想无羁地漫游,话语也随意地流动,整篇演说,舒展、从容,有一种说不出的自由感。
但却又是“杂”而不乱,“漫”而有序,放得开,收得拢。从总体而言,无论话题拉得多开,也始终不离“读书”这个中心。可能是考虑到听众多为中学生,因此,在结构上,也作了一些条理化处理。例如,在谈到自己对文学的看法时,就明确列为三点。文章结尾处,也用“总之”一语把演说的宗旨作了明确的概括:一是提倡“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二是强调“和现实社会的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这也是演说的中心和重心所在,是我们在读与教中应紧紧把握的。
三、“别人说不出的话”
鲁迅曾说过,他或许能够说出一些“别人说不出的话”。同样是“随便谈谈”,鲁迅谈起来,就会别开生面,给听众以意外的启发和惊喜。
前面提到的文章的那两个主要观点,就很有见地,我们八十年后听起来也仍有耳目一新之感。而他在展开论述中,更是处处显出思想的锋芒。不妨举几个例子。
比如,“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千百年来,人们总是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今天,应试教育这么盛行,也是因为应试可以致仕(升官发财),也自然以读书为高。这背后其实还隐含着一个读书人(知识分子)比木匠、裁缝(普通劳动者)高尚的理念。现在,鲁迅将“读书”与“磨斧头”、“理针线”,将知识分子和劳动者置于同样地位,这自然是对传统和世俗的读书观的一个挑战。
还有,“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是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读到这一段话,人们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因为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学理工的瞧不起学文科的,做学问的人瞧不起经商、当官的,或者反过来,重文轻理,重管商而轻治学教书,等等,人们见怪不怪,鲁迅却偏要质疑,而且还挖掘出其根子:这背后,有一个将知识与职业划分等级的观念,实际是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级化。这自然还会涉及社会体制的问题。这样的开掘,自会引出更深的思考。
再看这一句:“往往有人误以为批评家对于创作是操生杀之权,占文坛最高位的,就忽而变成批评家;他的灵魂上挂了刀”。——这里所谈已不只是批评家的问题,而触及到“文坛”(思想文化界)中占据“最高位”,也即权力的掌握者,同时拥有了创作的“生杀之权”的问题:这正是对历史与现实中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揭露。“灵魂上挂了刀”也就成了一切实行文化专制的“精神刽子手”的一个写照。
这就谈到了鲁迅演说中的现实针对性。他经常“附带”说到现实中的某个问题,点到即是,并不展开;如果不了解演说的时代背景,就很可能忽略过去。比如这一句:“我附带说一句,近来听说连俄国的小说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见‘俄’字就吃惊”。说是“附带”,其实是特意说的,因为正是演说前三个月,即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大屠杀,演说的前一天7月15日武汉政府也开始了大屠杀,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抓捕、枪杀,其中一个“罪名”就是“亲俄”,是所谓“赤色份子”。显然,鲁迅正是要通过这“附带”一句,旁敲侧击地对国民党的屠杀提出他的抗议,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这样说是需要勇气的。我们也因此懂得了他这篇演说的深意:反复告诫青年不要“躲进研究室”,“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正是暗示和提醒听众要敢于正视现实的黑暗和血腥,不要逃避。这些话,真的是别人说不出的。
记得老舍说过,鲁迅的语言“永远软中透硬”。我们前面说,鲁迅这篇“随便谈谈”,自有一种舒缓而从容的风致;现在,我们又感受了其内蕴着的批判锋芒。他的演说的魅力正体现在这软、硬两面的张力中。

四、“很普通的比喻”及其他
老舍对鲁迅的语言特点,还有一个概括:“他会把最简单的言语(中国话)调动得(极难调动)跌宕多姿,永远新鲜,永远清晰”。
本篇因为是演说词,而且听众是中学生,就更要求通俗、明白、清晰,但又必须吸引人,做到“多姿”而“新鲜”。
鲁迅告诉我们,他的秘诀是多用“很普通的比喻”。前面提到的“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还有“游公园”,到广东“吃荔枝”,这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去取喻,既来自听众熟悉的身边人和事,自然通俗易懂,但又赋予习以为常的生活经验以另一种意义,自然就构成了一个新鲜的发现。
当然,最为叫绝的,还是“打牌”的比喻。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鲁迅的一个“神来之笔”。我们甚至可以设想,他是在讲完了“读书”并不是特别“高尚的事情”这个意思以后,突发异想,就把“读书”的“嗜好”和“打牌”的“嗜好”联系起来,发了一通妙论:“读书”要和“真打牌”一样,“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即“离开了利害关系”,只为“在(书的)每一页每一页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本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读书”和“打牌”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并且似乎是处在“高雅”和“低俗”的两极,因此,这样的联想实属“荒谬的联想”。但鲁迅却巧妙地发现了其中的联结点:都是一种“嗜好”,都充满了“趣味”,而且都是“自愿”的。这样的妙语牵连,不仅让人喜出望外而眼睛一亮,更含有打破“读书高尚、神圣”的迷信的作用。
鲁迅自称“很普通的比喻”的,是他所说的“印度故事”。这样的用一个故事,而且是异国故事,来比喻一个道理,自然十分新鲜,而且这样的别一种风采,也可以产生“摇曳多姿”的效果。
除了比喻之外,鲁迅这一篇演说,在语言上还有两个特点。一是既然讲“读书”,就自然用了一些有关读书的词语,如“博览”、“泛览”、“专读”、“手不释卷”等,是应该引导学生在阅读时注意的。
另一个特点,是有许多警语、警句。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演讲者讲了许多话,真正让人们记住的,往往是一些警语、警句,或因其表达的奇警,或因其含意的新而深,让人时时回想,有时甚至因此在社会上流传开来。这也是中学生最感兴趣的。本文这样的警语很多,如“灵魂上挂了刀”,“脑子里给别人跑马”之类。更应引导学生抄录的,还有下面这些警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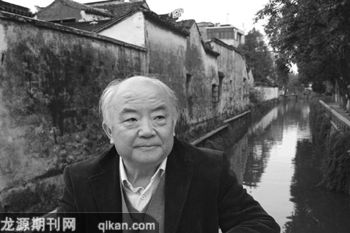
“嗜好的读书——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
“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
“自己思索,自己做主”,“自己观察”,“倘只看书,便成了书橱”。
“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
“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
“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而且这都不是有意炮制,而是读书和人生经验的自然凝结。
五、“到这里和诸君相见”
在演说一开始,鲁迅还说了一句话:“今天到这里和诸君相见”,也很值得琢磨。
于是,我们注意到,在演说中,时时提到“诸君”。“诸君”这个词,今天已经不常用,但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四十年代,却是一个普通的称呼,相当于今天所说“诸位先生”,用来称中学生听众,自然也含有尊重对方的意思。这里不仅显示了演说者与听众的平等关系,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而且,也说明演说者有着明确的“听众意识”:这正是演说的特点,它是主讲者与听众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所以叫“相见”。
所谓“听众意识”,首先是指“心中有听众”,演说者要理解、揣摩听众的心理,说出他想说而说不清楚的话,这样才能打动他,说服他。比如,如前所说,鲁迅本意要提倡“嗜好的读书”,但他却首先要大谈特谈“职业的读书”,因为这正是中学生听众更为实际的经验,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谈话——
“我想,在座的诸君之中一定有些这样的经验,有的不喜欢算学,有的不喜欢博物,然而不得不学,否则,不能毕业,不能升学,和将来的生计便有妨碍了。我自己也这样,因为做教员,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要不这样,怕不久便会于饭碗有妨。——其实这样的读书,——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你爱做的事,偏不给你做,你不爱做的,倒非做不可。这是由于职业和嗜好不能合而为一而来的。倘能够大家去做爱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饭吃,那是多么地幸福。但现在的社会上还做不到,所以读书的人们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
听(读)了这番话,我想,每个听众(读者)都会被打动,因为说到我们心里去了。
它揭示了人们(包括中学生们)真实的读书状态,以至生存状态:我们被“升学、生计”所困,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在“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不仅1927年的中学生是如此,而且八十年后2008年的中学生也还是如此,说不定更变本加厉了。揭示这一点,会让我们感到苦恼,也会引起我们的反思。而且演说者鲁迅并没有置身其外,他也深陷于这样的苦恼中,也和我们一起追寻“职业和嗜好合而为一”的理想的读书状态,理想的生活状态。这样,尽管他没有用更多的话谈“嗜好的读书”,但经过这一番逼视和反思,已经作为一种理想的,应该努力去实践的读书、生存状态,而深扎在我们心中了。

“听众意识”的另一个意义,还在于听众在听演说过程中,并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倾听者,它的存在本身,也会对演说者的讲话内容、方式,直接、间接,或显或隐地产生影响。我们在前面一再讲到在广州知用中学的这次演讲的听众主要是中学生,当然还有中学老师,这在鲁迅的演说中,是并不多见的。于是,就有了其他演说中并不多见的“请不要误解”这一类的申明和相应的补充说明。这是因为鲁迅深知:中学生作为一个成长中的生命,他们的思维相对比较简单、直线,也就容易对演说者的意思产生误解,而这样的误解有时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演说者面对中学生这样的特殊听众,说话就必须慎之又慎,要尽量避免片面性,防止发生误解,有时就需要多说几句话。
比如,鲁迅在讲了“嗜好的读书”的种种必要与魅力之后,紧接着就说:“不过我的意思并非说诸君都应该退了学,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去,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也许终于不会到,至多,将来可以设法使人们对于非做不可的事发生较多的兴味罢了”。——这样的多说几句当然是必要的。又如鲁迅在提出要多读“课外书”的建议以后,又赶紧声明:“但请不要误解,我并非说,譬如在国文讲堂上,应该在抽屉里暗看《
红楼梦》之类,乃是说,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从这样的申明、补充里,我们不仅看到鲁迅论说的全面、周密,更可以感到,他对中学生、对自己的言说的负责态度。
或许,这样的责任感,这样的真诚心,是鲁迅这篇对中学生的演说最令我们感动、最让我们深思之处。